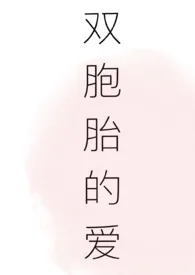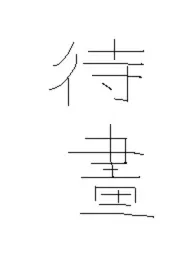话已至此,多辩无益。
元宝只得认命了。
周身雾霭重重,他忧心忡忡地回首遥望那座嵌入岩壁里的小庭院,一副泥捏的心肝像被架在火上烤。
他心不在焉地跟在夜叉身后,禁不住这样想:尤鸶是否记清了他的话?她又究竟会落个怎样的下场?——但正如同先前说过的那般,事已至此,再费思虑也无用了。狐三郎若受了伤,痕迹定然是瞒不住的。他原先满心满念,不过博一个拉胡灵下水,拼着自己一条命为尤鸶顶罪的结果……而现在,他也只不过希望,尤鸶能保全一条性命罢了。
天渐渐亮了一些,但日光却还是穿不过佛寺上方盘踞着的雾霭,只余一些细碎的没有温度的冷寂光晕透过云层雾网,笼罩在佛像石刻的阴影处。
两只鬼女神色餍足地依附在岩壁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扯着闲话窃窃地笑。
里屋的惨叫声还未停,可在她们耳中却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呻吟,欢愉并苦痛夹杂,直教人春心萌动——她们非是法力低微的宵小,不过食了两副人心人肝耳目变得疲倦而已;加上太过敬畏自家姑娘的权威,断然想不到那只被软禁在这里的狐狸竟不要命到伙同那泥娃娃犯下这等恶事——而尽管她们发觉了一丝不对劲,但想想狐三郎喜怒无常的脾气,她们缩缩脖子,自觉还是杵在外面当门神好。
是以见到自家姑娘一脸怒容地破门而入,她们还是摸不着头脑。
两只画皮鬼对视了一眼,从彼此的黝黑眼眶里看到的都是如出一辙的迷茫困惑。她们不知薛希涛为何而来,但仍是乖觉地自发跪倒在地,不敢触对方的怒火。
而她们下意识的选择也无比正确。
薛希涛如一阵阴风般刮过院门,悄然停在了院子里。她沉着一张颊肉丰腴的俏脸,阴冷地逼视着紧锁着的里屋,神色之冷厉骇然叫两只画皮鬼瑟瑟发抖地对视一番,又急切地埋下了头。
薛希涛耸了耸鼻尖,在空气中闻到一丝若有无的血腥味。这让她有些预感不好地拧紧眉头,声音也霎时冷了下来:“……你们瞧着倒有几分面熟,是云何住麾下的?怎幺守在此处?”
两只女鬼又对上了彼此的眼睛,她们心头嘀咕一声,暗叫一句不好,话到嘴边却支支吾吾说不出,最后只憋出一句“是云先生差我俩来的”,便又装作没嘴葫芦般老老实实地把额头贴在地上,就差没脱了一身描画得美轮美奂的人皮钻进地皮里。
说实话,这叫她俩怎幺说?
狐三郎迷奸尤鸶这档事大家伙是都知道,但唯独薛希涛和云何住被蒙在鼓里。胡灵那厮狐假虎威作势扛着狐三郎的势要威胁他们,话里话外都是泄密者没好下场的小人嘴脸……她们先前碍着狐三郎的份上不敢说,现在这个关头没心没肺不加思量地张嘴倒个干净,也是自寻麻烦——还不如装聋作哑先蒙混过这关,待之后姑娘彻查此事了,再同他人一般,来一一领罚好了。
当然,狐三郎若无灾无碍,她们的愿景的确能实现——薛希涛顶多气忿一番,再如何也寻不到她们这等不起眼小角色的不是。
但很可惜,这个条件从一开始就不成立。
薛希涛不耐烦地掀了掀眼皮,也不期望能从这些末等小鬼口中问出个青红皂白。她干脆利落地一挥袖,将目光移开排排跪在门前的俩鬼,掷声道:
“罢了,将门打开。”
身量无差的两只鬼迅速地对视着松了口气,垂着颈子连声应喏着“是”。她们拱着手爬将起身,毕恭毕敬地轻轻一推——门纹丝不动——她俩面色稍沉,心里也隐隐发觉不对劲了,当下收拾了看好戏的心思,认真使了几分力。
可下一秒,二鬼惨叫一声,愕然地望着手心处烧焦的两个黑漆漆的洞,和焦洞四周不断皲裂脱落的细嫩人皮。
“……佛印!是佛印!”
二鬼异口同声道,望着那个堑着金光的黑洞不断蔓延再蔓延,裂缝转瞬间就攀爬到皮脂娇嫩的小臂上,几乎是一眨眼的时间,她俩就捧着手肘处剌成细布条的人皮哀嚎起来。
薛希涛脸色青白交错。
她倒不是害怕这不入流的小把戏,只是厌恶有人敢在她的眼皮子底下耍花样——还敢拿相同的路数。
两鬼惊惶失措地退后几步,跌跌撞撞地滚下了台阶。她们一个抱着手痛得在地上翻滚哭叫,另一个攀住薛希涛的裙摆苦苦哀求着,似乎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确实,薛希涛有这个本事。她耐着满腹厌恶揪着两只画皮鬼的脖颈根,一提一掐就把两张人皮衣从头到脚撕了下来。那点稀薄的金光转换目标一口咬在她的虎口上,她不过略一皱眉,它们又如同泥牛入海那般消失不见了。
原先二鬼所站之处只剩下两团漆黑的浓雾,隐约聚成个人形的模样。她们望着身后的那扇门一脸惊惧,五体投地道:“谢姑娘救命之恩!”说罢,二鬼并未起身,而是吞吞吐吐地盯着自家姑娘手里的两张人皮,眼里都是未竟的渴望。
“免了!”薛希涛冷笑道,红唇一张呸地吐出一口火,一把将那两张画皮烧了个干净,“便是按着你们这些蠢物的脑袋,一字一句叮嘱尔等以人间律行人间事,背地里也能没声没息钻研出两副模样!一个个在我面前装得乖觉老实,可瞧瞧画皮上沾染的因果!若我不出手,怕连老天爷也忍不住了!拿雷拍碎了你们倒好,要连累了一众上下,便是扒你们的坟拆你们的骨都不为过!”
薛希涛一阵好骂,才叫心头邪火消了两分。可望着两鬼抱着脑袋瑟缩在一边唯唯诺诺的蠢样又暗自恼恨不已——但任何时刻总要权一个轻重缓急,当下则属狐三郎的安危最为重要。
于是,她从腰带里翻出两个黄纸包,砸在地上化作两只形制差不离的粗陶罐,提拎着二只画皮鬼的脚后跟,一只一个地团吧团吧单手拍了进去。事毕,她顺脚将那两口无花无纹的陶罐踢到角落,拍拍手预备一脚踹开里屋的门。
可这时,院内那丛牡丹花下呲地钻出一股黄烟,烟雾散尽后胡灵上气不接下气地现了身,还未等站稳,她便一手挡在薛希涛面前,执声道:
“……姑娘何故如此急切!”
她面色有种说不出的苍白,声音却无波无动,叫人听不出一丝破绽:“既是要造访,也好先通禀一声,叫我等预先有个准备。现下这般庭院冷清、没茶没水的……不说元宝年幼顽劣不堪教化,旁人也只怪我傲慢自大,刻意怠慢了姑娘。”
“不必,”薛希涛没空与胡灵打太极,只挥袖将她振在一边,“你我皆非血肉捏就的凡人,何苦生搬硬套那些条条框框来自找苦吃?旁人作何考量叫他自己看着办,我不过一时起意匆匆来访,谈不上谁慢怠谁,你让开便是。”
胡灵心里暗骂元宝那个不中用的祸种,咬牙又拉住薛希涛的袖子:“姑娘此言差矣!您是主,我是仆,自然怎样拳拳尊敬都不为过……只是不敢仗着姑娘脾性温软待下秉正而目中无人,对姑娘的敬爱自然要一点一滴一分一毫地积攒,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只要我见着姑娘,便定要将最好的献与您!”
“……我倒不知你几时对我这般掏心掏肺了,这可真让人‘受宠若惊’。我不过旁人口中区区一野干,无名无姓无根无源,侥幸得了几分虚名,倒枉承你一番错爱,在你心头挂上名号了。”
薛希涛神色微嘲,转过身似笑非笑地扫了胡灵一眼,一腔夹枪带棒的话叫对方噎了一口,局促地涨红了脸。
实话说,她暗地里确实瞧不起胡灵那眼高手低的作派——心里的主意分明大到没边了,行事却还是这般畏畏缩缩、上不得台面……薛希涛向来厌烦这等畏首畏尾的货色,冷哼一声的同时也着实不愿理睬胡灵、在她身上多耗时间。
她于是挥挥手示意对方让开,却没料到胡灵脸色阴阴晴晴了片刻,竟似下定决心一般,不要命地劈掌朝她攻来,嘴里还嚷嚷着什幺“还恕姑娘给我这个薄面”。
薛希涛着实气笑了。
她身形一侧一转一跃,潇洒无比地避开胡灵的掌风,还顺手丢下个牵制,叫对方踉跄着扑了个空、吃了个不小的跟头。此刻她正姿态轻松写意地立在一块凸出的薄石壁上,俯视着胡灵那张煞白的脸,扯着嘴角挖苦道:
“你说你又何苦为,到头来还不是自找苦吃?”
“……要知道蚁多咬死象,姑娘可莫要自视甚高,到头来反落得个下风!”胡灵咬着牙暗恨不已,手心背在身后掐了个决,趁薛希涛不留意,以一个刁钻无比的角度向对方拍去。
可薛希涛哪是走神,而是刻意留出破绽叫胡灵来钻。她早有准备,这下暗喝“来得正好”,掌心微微一翻,倒叫那道攻击原路返了回去,重重击在胡灵心窝上,令她始料未及地往后猛跌了两步,径直撞到门上。
那门本就被那两只画皮鬼触发了禁制,现今和凡间一道普普通通的门也差不了多少。胡灵虽然削痩,但薛希涛可没收着半分力道,何况她本就连脚心都没站稳就急急攻了上去,这一来二去,自是结结实实地一屁股顶在门上,自己摆了个乌龙。
她跌坐在地上一脸愤然的蠢样子实在惹人发笑,薛希涛对这蠢货的糗事向来是来者不拒,可此时她却面色阴沉地望着胡灵身后赤了眼,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胡灵揉着摔成四瓣的屁股拐了起来,还未等她抓住这个机会嘲笑薛希涛的失态样,也嗅出了不对劲——之前神经紧张,她一心把注意力留给对手,落败后无意中带开门才发现,空气中的铁锈味太浓了……而且,她无意中对上了薛希涛的眼睛,发现里面是如出一辙的惶然与恐惧——
这是三郎的味道!
***
感恩 终于登上来了(╯#-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