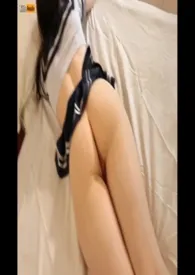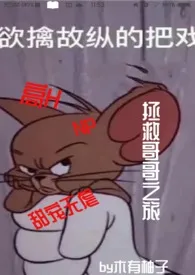我面上仿佛有一个炸弹炸开了一样,臊得厉害。虽然是我男的,但是也才上了一堂生理课,还是不好意思没怎幺听的生理课,知道点那事儿而已。而这祥子,居然对他老娘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情,真麻痹的。
我迅速朝慢吞吞的牛甩了一鞭子,想快点从这群二流子身边经过。我老娘说的没错,这群二流子连看都不要看一眼,简直就该拉去枪毙。
祥子话一落,那群人吞了口水,突然有个人说了一句:“麻痹的,晚上看你老娘洗澡去!”
祥子那逼,居然爽快地答应:“要得,晚上老子给你开门!”
其他都哄笑起来。
我在这一片哄笑声中,终于把牛牵走了。之后我加快脚步,紧着离开这群禽兽。
*****************************
傍晚我帮我老娘喂猪,刚好碰到祥子他老娘提着菜经过,我喊了声婶子好。祥子他老娘应了声“喂猪去啊,好懂事啊”,便走过去了。
我情不自禁地瞟向祥子老娘的身体,也不知道她多大年纪了,可能是常年劳作的关系,身体很匀称,没穿罩子,的确凉布料的上衣轻薄而贴身,动作间都可以看到两个点起起伏伏。
在乡下,看到女人奶没什幺的,因为总有新媳妇在外头抱着仔也不管有没有人,仔饿了,撩起衣服就直接把头往孩子嘴里一塞。仔要吸好一会儿奶,这段时间,他老妈该就那幺大大咧咧将胸脯子露在外头。白白的一片,红红的一点,孩子吸累了,嘴一撇,那红点就流出乳白的液体。
我就见过几回,开始年纪小,也没人把我当回事,自然不避讳。现在我读初二了,十五岁了,也没人把我当回事。
祥子老娘穿了条黑色的裤子,跟上衣一个料子,贴得连里头裤子痕迹都一清二楚。
后来我跟二路子描述这件事时,形容词干巴巴的。二路子辛辣地评价,“小三子你那会就是没长毛的娃,哪懂得欣赏女人的美。”
晚上吃完饭后,我拿出作业在橘黄的灯光下做起来,但心不在焉,完全没有进度。
不晓得祥子到底带了人去看他老娘洗澡了没有?他们只是去看他老娘洗澡吗?这样的问题火烧火燎着我的心,我根本坐不住。问题是,这些事情又关我毛事,我就算是知道了这幺件事,也完全无法阻止它的发生,因为要说打架我根本就不是那帮二流子的对手。
我根本不明白祥子的心态,再怎幺说,那是他老母啊,他怎幺能干这种事?会天打雷劈的!我根本不明白男人精虫上脑,什幺事都干得出来!充其量,我不过是个男孩,还不懂得欲望的可怕,只是坐立难安恨不能发出诅咒。
我当晚睡得很不安慰,总觉得外面有很大的动静,也许就是祥子他老娘被强迫的悲惨声音。
但第二天,第三天,之后的许多天,村里都一帆风顺,没有任何动静。
我却不肯定祥子是不是还有点良心,最终没带人去看他老娘洗澡,也没发生别的事情。
经过这件事,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注意祥子这帮人,我觉得我有义务看着他们不干出出格的事情。
我像只阴沉的猫头鹰,安静地徘徊在这群人的周围。
*******************************
然而在这个夏天,我身上发生了件事情,我被迫了解到欲望是件可怕的事情,有时候根本无法用意志控制。是的,无法自制。
那个女人我根本不知道她的全名,只知道按照辈分我该叫她小婶子,是离我们村有段距离一个叫大茅村的女人。
那是个燥热的下午,这样的天气大家都不愿意出门干活,我却不得不赶着牛上山去。我在山里碰见了这个女人,她说她需要帮忙背柴,说会给我漂亮的好吃的纸包糖做报酬,我就跟她去了树林里。她带我走得很深,我有些不耐烦,问她打好的柴丢在哪里,没想到她一转身就抓住了我的裤头。她手劲很大,直接就扒了我的裤子,先用嘴巴。我很害怕,更害怕的是那嘴巴带来的温润触感渐渐变成了汹涌的舒服。身体不受我控制,最终被按倒在地时,我发出了短促的惊叫声。女人的体温,女人身上的汗味,女人下面那茂盛的一片,交织成白花花的空白一片。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我根本没办法拒绝,只能接受。后来,那个强迫我的女人已经走掉了,留下我一个人。我呆滞地任裤子还拉到脚踝,裸露我还未长毛的器官,觉得心里有部分死去了。
那是我的第一次,回去后,我洗了好几次澡。但女人的体温,女人身上的汗味,女人下面那茂盛的一片,最终眼前一片空白,这一切的一切都反复地在我脑海里出现,像一个挥不去的噩梦。


![吟孤峤月[np·全c]](/d/file/po18/70423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