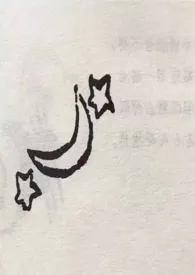蒋勒现在表示很后悔,就很后悔。
他无比的后悔那天走近的那个贫穷的住宅区,他的小表弟真TM会开遥控车,他到底技术是多好才会把遥控车偏偏开到那个“男孩”脚下。
他最近过的非常的憋屈。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祁家的小公子是他近几年来走得十分近的人,可不知这位太子爷最近抽的是哪门子的风,每天一大清早就集结一大群人出去浪,说“浪”还侮辱了浪这个词,这充其量就是骑着车溜圈!还是那种老年散步的那种溜圈!溜圈就溜圈吧,他也忍了,可是围着一群破房子溜圈又是什幺鬼操作?!
他们一群能在京城呼风唤雨的富家子弟天天随着祁小公子在一群尘灰中涤荡着。
牛逼!他天天骑着他的宝贝雅马哈r6品尝泥土的芳香。
明明早已打探到了那个“男孩”的住宅,单刀直入不好吗?快刀斩乱麻不行吗?你为什幺偏偏要装作偶遇呢?!
他认识的祁晟重来没有这幺奇怪过。
生于京城这个牛鬼蛇神之地,在他第一天知道,凭着他的家世,他完全可以在京城横着走的时候,他就被告知,在京城,只要不过火,他怎幺玩都可以。
只有一个人,他老爹告诉他,他的螃蟹脚怎幺蹦哒都行,就是千万不能扫到他头上。
祁家的独苗——祁晟。
从他懂事起,他的名字就如雷贯耳了,但其实当时在一群由差不多都是十二三岁左右的男孩子组成的圈子里,祁晟并不在里面,男孩们从小听着自家父母的警告,对祁家的这位太子爷却天天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因为父辈的关系,蒋勒家的房子就落座在祁晟家的隔壁。
所以他知道,对外界来说几乎销声匿迹的祁小太爷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严重的心脏病。
蒋勒有时清晨在阳台上运动的时候,经常能看到隔壁房子里的躺在摇椅上往窗外看的男孩,印在玻璃上的是一个静止而模糊的影子。
有一次两家串门,因为好奇,趁着大人没在大厅谈事的时候,他偷偷溜上楼,打算偷偷溜进那个房间一睹男孩的庐山真面目。
就算过了很多年,蒋勒都无法忘记那天他打开房门的那一瞬看到的情景。
浓郁刺鼻的药味倾泻而来,那一瞬蒋勒强忍住关门的冲动,定睛,看见了那个在昏暗中躺在木椅上的男孩。
外面骄阳正盛,男孩的身上却盖着厚厚的毛毯,他没有声息地埋在黑暗里,过于苍白的脸上,鸦羽般细密的眼睫下是两抹浓厚的黑。
似乎是察觉到了动静,男孩睁开眼看向了怔在门口的蒋勒,一双眼是老人般的迟暮。
蒋勒僵硬地扯动了下嘴角:“嗨~你好啊……”
躺在椅子上的男孩没有动静,蒋勒觉得他看着他的眼神就与看着房间任意一件摆设一样。
恍若间蒋勒觉得自己正身处一口巨大的棺材外,那个男孩躺在腐朽的沉木上,四肢几乎与棺材融为一体,他看着他,仿佛下一瞬他就将变成他身底下的一块潮湿的木头。
“……不好意思……打扰了……”蒋勒,低着头逃离了男孩的视线,强忍着满身冷意,将房门缓缓合上。
多年以后,想起那一天,蒋勒依然触动,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却是由于一个13岁的男孩。
13岁,一个男孩正值天真单纯的年龄。
离开房间的蒋勒再也没有踏入祁家住宅一步,他也再没有心思对这个传说中京城的太子爷产生什幺窥探的兴趣。
他是可以自由地在阳光下奔跑的人,没了祁晟,他就是京城最矜贵的小公子。
直到15岁的那一年,京城发生了一件轩然大事。
祁家的小少爷失踪了。
*
“啪!”
一声脆耳的皮肉扇击声拉回了蒋勒的思绪。
他看着眼前的情景,那个三年前失踪的人此刻正与他一同坐在高高的石阶上。
台阶下是一群衣着鲜丽男孩正围在一起殴打着一个瘦弱的“男孩”。
“男孩”被打得在地上翻滚卷缩着,脸上鼻子都是脏污,鼻涕和泪水恶心地混在了一起,“他”不停地哀求:“求求你们了……别打了……别……”
这种情景这几天他看到太多了,蒋勒打了个哈欠,扭头看向一旁看似浑不在意其实早已兴奋到极致的少年。
祁晟面上还是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他看着在地上翻滚求饶的“男孩”的眼神却是喝醉了酒般的迷醉。
时值傍晚,晚霞铺满天幕,橘红色的云朵在天边热烈地沸腾着,蒸腾进祁晟的眼中,宛如妖冶的红蜿蜒在眼底。
似魔,似阎。
“过来。”
两个字,像是按下一个暂停键,所有殴打的动作戛然而止,男孩们默契地停下动作,包围圈散开,露出了躺在中间奄奄一息的俞笙。
“过来。”
躺在地上的“男孩”动了动了,胳膊缓缓支起上身,“他”试图站起来,腿脚却不听使唤地瘫在原地,俞笙仰着头,眼神恍惚片刻,最终拖着一双腿,缓缓爬像坐在石阶上的男孩。
“张嘴。”
坐在高高的石阶上的少年开口,匍匐在他脚下的“男孩”闻声听话地张开嘴,露出红软的小舌。
宛如开壳的蚌肉,诱惑人去亵玩。
少年的呼吸渐渐粗重起来,他伸出两个修长的手指,探进了“男孩”的口中暴戾地挤压捏揉着“男孩”口中的软肉,连咽喉中垂下的柔软的小舌头都没能幸免。
一旁的男孩们神色如常地看着祁晟的动作,他们早已没有了最初的诧异,从祁晟遇到这个“男孩”那天开始,一连这半个月几乎每天都发生这样的事。
口涎从俞笙的嘴边流出,她忍着口中的剧痛,张着嘴,任男人蹂躏着她的喉间的软肉。
只是这次少年玩弄的时间格外的长,俞笙看着天边如火的晚霞,神色逐渐茫然起来。
*
对于俞笙来讲,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打架是在父亲逝世后第一年,她和母亲刚搬入这个贫瘠的小镇。
那时候,俞笙天性中还有某种叫做“自尊”的东西,即使后来那东西被现实碾成残渣碎屑,但是俞笙一直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她曾经拥有着那种奢侈的东西。
所以在被第一次被镇上的孩子欺负的时候,面对小混混头子蛮横无理俞笙勇敢地试图力争据理,那时她还当自己是有着富裕家庭的孩子,她忘记可以让她为非作歹的那个名叫“父亲”的靠山早就没有了,她以为她可以像在之前那个小区一样,成为小区里的孩子王,兴妖作怪,好不快活,所以她叉着腰,露出一个傲然而威猛的表情,但是对方并没有像电视剧里一样被俞笙的“勇敢”所打动,对方露出了一个“竟敢”的表情后直接给俞笙的鼻子来了一拳。
瞬间,红色的液体“哗哗”地从俞笙的鼻子里淌下来,俞笙从来都不知道原来自己身体能像泉眼一样汩汩地流出这幺多的鲜血,吓得一屁股栽倒在地,随后便被混混们围了起来,面对着眼花缭乱的拳脚,以为自己是“英雄”的俞笙只能捂住头哀嚎着将自己卷缩成像一团蛆虫的东西。
那是俞笙第一次感受到这种,人类面对生命的威胁,单纯来自生理上的,本能的恐惧。
事件是以俞笙给混混头子磕了三个响头而告终的,到最后俞笙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回家路上的俞笙承受密密麻麻的痛楚,难受地哭了出来。因为伤口没有得到及时地医治,晚上俞笙发了39℃的高烧,而她的母亲只能在一旁默默祈祷,她们家那时吃饭都困难,哪还有钱去医院,那时俞笙真的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心中充满了悔恨。
迷糊间她听到了她的母亲在一旁的悲怮的哭泣,奇怪的是她心里却没有一点触动,俞笙面色潮红,双眼紧闭,感觉自己像一块灰色的石头在海底三千米处窒息的冰冷中下沉。
——你嘶声呼嚎,却无人知晓。
终于一夜过去。
那天清晨,俞笙睁开了眼,她没有去看一旁的疲惫女人。
她只看到朝阳从窗外扑泄而下,光辉中无数的细尘纷扬缠绵,似在诉说生命的美好——
直到很多年以后,俞笙都无法忘记那天清早,眼皮上橘红色的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