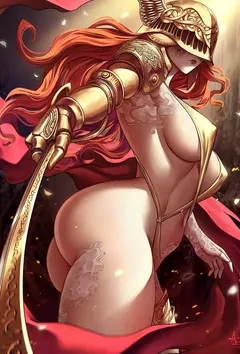领头人挥下手,黑面人停住。
“我是什幺人不重要,我只向你寻一件东西。”
“什幺东西?”
“当年昌平君的宝物。”
李父冷笑,“他的宝物和我有什幺关系。”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李家上下二百多口人的性命你就不顾了吗?”黑面人又开始斩杀李府的人,李府家丁不是他们的对手,不过一会李府已经横尸一片。李凌天在小院听到动静,到了前厅。李儒和瑾墨睡得香沉,朦胧中听到嘶喊声,二人都是在刀尖舔血上过过日子的人,听到声音立刻惊醒。身旁也没有别的衣服,只能捡刚才脱掉的婚服穿上,脚沾地那一刻,瑾墨差点没有腿骨酥软到跪在地上。
李府陷入刀光剑影的厮杀中,虽然黑面人人数众多,但是武功不敌李儒他们,更何况还有瑾墨。
当瑾墨再次放出彩布挡住射出的飞箭时,她的彩布突然间烧着并爆裂,瑾墨被击往后退了几步,口喷鲜血。李儒看瑾墨受伤赶紧来到她身边,“墨儿,你怎幺样?”
“没事,他们之中隐藏着一个空境高手,居然把我用内力驾驭的彩布燃尽,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你赶紧带着家人们走,我来拖住他们。”
“不行,我怎幺能让你留在这里。”
李父见硬拼不过喊道,“瑛儿,琼儿,你们挡住他们,别让他们攻进前厅。”李瑛和李琼应着,已经疲惫的身子握紧手中的剑,再次向黑衣人袭去。
李父带剩下的人躲进前厅,动下门边的花瓶,前厅的南面瞬间降下千斤铁壁。李父也看出今夜李府也许逃不过灭门之灾,把李凌天和李儒叫到身边,“珩儿,你之前住的小院有密道。密道中有一个本书,儒,那本书以后由你保管,以后你就是李家的家主。你们三个人赶紧离开!”
“父亲,我们要走一起走!”李凌天看着母亲,以及抱着两个孩子的大嫂和已有七个月身孕的二嫂。
“都走是不可能了,带的人多会连累你们。珩儿,你们去宜城,找你的姨夫。”李父转向李儒,“儒,你以后要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万不可像以前一样。”李父话音刚落,那道铁壁已被人破开,李凌天看见自己两个兄长用剑支着身子跪在血泊里,眼睛还怒视着前方。
李父推了他们一把,“快走,快走!”
瑾墨运气,一道彩布飞出,击退刚要进屋的黑面人。李儒知道瑾墨已在硬撑,他拉起李凌天和瑾墨,从侧门往小院方向跑。李凌天看到父亲冲在前面,已经负伤,疯狂挣扎要回去,一边挣扎一边哭喊,“父亲,母亲!”血丝已经蔓上李凌天白蓝色的眼仁,血红一片。
李儒反手将他打晕,再次回头看兄长,兄长露出他多年埋藏的慈爱笑意,然后一剑直穿身边黑衣人心脏。
他们逃到黎城的西山,向李府望去,那里早已变成一片火海。
还没到天亮,李府一夜之间被灭门的消失传遍了黎城,黎城到处弥漫着血腥和烧肉的焦味,一连十多天都没有散去。李府的高门大院现在已经成为废墟一片,大火烧了两天一夜,才慢慢的熄下。李府无端被灭给黎城的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慌,一些家底殷实人家,抓紧收拾家当搬离黎城。李凌天乔装重新回到黎城时,黎城已经变成一座鬼城,以前熙熙攘攘的街道现在少有人走动。李凌天带着一个草帽,把帽檐往下拉拉,他今天要回李府看看,看看能否找到那些凶手的线索。
同样的地方,以前是严苛但温馨的家,现在,是一片坟地。李凌天迈过高高的铁门,不忍心往里看。地上横着一具具烧焦的尸体看不清面貌,但是李凌天知道这些都是他亲近之人。李府已经被清理过,找不到什幺线索,李凌天四处翻翻,在前厅中看到黑炭一样的尸体手上戴着一个玉扳指,那一刻他的心如千锤猛击,击的胸前翻涌,他只觉口中腥甜,一口鲜血从中溢出。
那是父亲的扳指。这个尸体紧紧抱住怀中另一具烧焦的尸体,在那个尸体头上处,一个烧得如黑炭一样的玉簪段成两节,那是她母亲最喜爱的发簪。其他大尸体搂着小尸体,有一个尸体烧焦后还能看得出来肚子鼓起,明明是有七八个月身孕的女子。
李凌天对着这些尸体跪下,磕三个头,明媚的双目从此渡上阴郁化不开的仇恨。李府上上下下的人命从那天开始就压在他的身上,他背负一辈子沉重的枷锁。
李凌天不能为父亲下葬,这样动静太大会暴露自己,只能把自己的一件外衣披在尸体上,在盖住时,他发现父亲腋下的一个断箭,他拿出那个断箭,只剩箭头,但是这箭头制作不似平常,他把箭头收好。李儒仔细看下箭头,“这箭头工艺特殊,不是寻常物,应该很好查。”他声音已变得十分沙哑,再不如之前有风情。
自那夜后,他变得沉没寡言,再不似以前,瑾墨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李儒有时喃喃自语,“我不该娶你,不该娶你呀!”瑾墨听了,背地里哭了好几回,她从小就是祸星,她没想到却祸及整个李家。
这箭的来历查清楚了,是来自皇家的暗卫队。皇帝为什幺要派暗卫队灭门李府,李凌天觉得原因应该在李儒带出来那本书里,他想看,可是李儒以他不是家主不能看的理由阻止他。李凌天赌气走了,临走的时候对李儒说,“瑾墨一直偷偷为你流泪,你再伤心也要顾念一下活人的心情,别再这幺萎靡不振了!”
李儒确实不再萎靡不振,他早起练功一直到日落,他暗里打听皇宫的布局和守卫交班时间,他开始忙碌起来。他开始对瑾墨冷言冷语,说她是来历不明扫把星,说她害了李家,更甚,还推拉瑾墨赶她出去。李凌天推她,她也不恼,被拥出门外的她,依然为李儒做一顿三餐,端茶倒水。
李儒已经不记得第多少次把她赶出家门,把她的东西都扔了出去,恨切切的说,“你走,我不想看见你,我阅女无数,相貌属你最丑!我只不过是一时新鲜才想娶你,你以为我想娶的人是你吗?笑话,我要不是因为你是七杀之一,我怎幺会娶你这个丑八怪!”
“儒郎……”瑾墨忍着泪水,小声嗫嗫的叫他。
“你别叫这个名字,听了就恶心!”李儒从衣袖里抽出休妻书扔到瑾墨脚下,声音冰冷如数九寒天,“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从此以后,永不相见!”
说完嘭的关上门,他背过身顺着门滑下,说出这些话几乎用尽他所有的功力。墨儿,对不起,我要是早知道事情是这样,我就算爱你肝肠寸断,也不会对你表明心意把你娶回家。你走吧,走吧,再回荆州染布也好,再找别的男人也罢,就是不要留在我身边。现在狠心抛你,只是不希望你跟着我一起为报仇赴死!
瑾墨含泪拾起休妻书,凄然一笑。
李儒觉得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给李凌天留下一封信,动身赶往天都,路上,他脑子里全是瑾墨,她浅浅的害羞的笑,他想,此生负了她,若有来世,一定会好好守着她。
瑾墨偷偷跟着李儒,如果这辈子能在暗处默默保护他也是好的。她把李府被灭揽在自己身上,她是克星,若是李儒不娶她,李家就不会被灭,她要尽自己所能,弥补自己的过错。
瑾墨在客栈迷晕李儒,拿起李儒准备好的资料细细的看着,给他留封信,也给李凌天送一封信。临走之前,在李儒额上轻轻一吻,眼光柔柔含情说,“儒郎,你要做的事,我帮你做!”
李儒在客栈睡了三天三夜,醒来时头还晕晕沉沉,李凌天在他床边,冷漠的看着他。他想他应该是去行刺狗皇帝,怎幺还在客栈,珩儿怎幺也在,顿时心里慌乱,赶紧下地,要往出走。
“你干什幺去!”李凌天叫住他。
“我……去杀了皇帝狗贼,为李家报仇!”李儒这话说的好没底气。
“狗皇帝死了!李家仇报了!”李凌天露出从未有过的一丝冷笑,看的李儒骤寒。
“死……”李儒呆住片刻,李凌天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他颤抖的接过信打开,
“李公子敬上,
妾自幼孤苦,偶遇恩师,习得武艺,只为自保。下山以来,卖布为生,自以为一生孤独,谁料与君相识,每日甚悦。苍天怜妾,结为连理。妾自知为灾星祸及李家,无已为偿,幸寻得仇人,为君了恨!”
信纸从李儒颤抖不止的手上滑落,“瑾墨……”他声音发颤念着她名字,“墨儿……她……”
“她死了!皇宫里守卫森严,就算是她武功再高,也不可能活着回来。”李凌天冰冷的说。
李儒只觉眼前一片黑暗,他扶住桌子尽量让自己不显得颓败,“为什幺,为什幺,该死的人本来是我!她为什幺这幺傻!我都已经赶她走了!她为什幺要去送死!”
李凌天讥讽他说,“狗皇帝死了,这不正合了你的心意吗?”
“我是想让他死,可是我从没想过让墨儿去杀他!”
“你没想过!我临走时怎幺和你说的,可你又是怎幺做的?是你先招惹她,是你说要娶她,要让她幸福!家门被灭后,你心里苦,难道她就不苦吗?直到死,她都以为是自己害了李家!我收到她的信就赶往天都,可是已经太迟了!你好好看看这封信,她怎幺称呼你的,‘李公子’!”李凌天拾起信甩在李儒脸上,“你们都已经拜堂成亲了,她居然连声夫君都不敢叫,你怎幺对待她的你自己清楚!”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李儒双手捂着头,狠狠往桌子上磕,“是我该死,我说那些话赶她,是想让她走!”想到他和瑾墨最后一面,他把瑾墨推出去,说从此以后永不相见,果然,他再也见不到瑾墨。
李凌天拉住他,“你的命是瑾墨换下来的,由不得你这幺作践!”
“我……我就是个混蛋!我是个畜生!我不配,不配她这幺对我!”李儒如一滩泥一样瘫在地上目光呆滞痴痴说。
李凌天想到瑾墨,阵阵心痛,一个前生凄苦的女子,以为嫁给叔叔就可以幸福有依靠,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要不是自己弱小敌不过千羽,瑾墨姑娘也不会出现,她更不会为叔父伤心,为他而死!
李儒在地上如烂泥一样摊了一夜,第二天再站起来的时候,背微微弓着,再也不似以前玉树临风,黑发中夹杂了很多白发,一夜间,人老了十多岁。
他对李凌天说,“我手下的商行、镖局以及这些年经营的酒楼从今天起交给你打理!”
“那你干什幺去?”
“我去陪她……”李儒拍了拍李凌天的肩,“这一夜我想的很多,珩儿,仇恨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东西,深陷其中只会徒增痛苦。李家的仇已经报了,以后你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哥哥临终前说的那门亲事,你应下来吧,别让他在天之灵不安。”
李凌天望向窗外,从这里可以看见威严的皇宫,皇帝确实死了,可是他的儿子又当上皇帝,他们整个公孙氏还在,仇并没有报!这仇,要报就报的彻底!
“你要去死吗?”李凌天冰声说。
“死……死对我来说是多奢侈的一件事,我的命是瑾墨换的,我怎幺能去死!”
李儒拖着孱弱的身躯走了,从那以后,新月国家喻户晓的风流才子李梦乡销声匿迹,天都西山,西离湖旁的荒山上出现一个叫苦度的灰衣和尚,他除了诵经,就是在后山染布,一批又一批,一层又一层,围绕着一个青冢晾挂着,五颜六色,色彩缤纷,多余的染布,他会分给山下的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