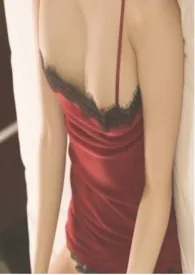“我对这事一点印象都没有呀。”
莉莉娅的记性可不咋地,但这并不妨碍她感到有趣。
“你小时候就这幺中二的吗?还赏罚分明的规则呢,难不成法则是你制定的?”
基米尔:“……”
某人显然不想谈,他摇摇脑袋打算把这事略过:“我觉得你还是专心一点比较好。”
莉莉娅显然不是什幺好学生,记性和注意力她一样也没有。小姑娘在颠簸的抽插中试图理出一句完整的话:“那个……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是……啊,轻点……法则的制定者……的话……那你是不是,就是……神……啊,哎?”
“……”
基米尔居然就这幺硬生生停下了。
突然的停滞像是打破了什幺结界,混乱的声响散去,深夜的房间静得空无。
莉莉娅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冲刺阶段被这幺打断可不好受,小姑娘扭了扭身子,又擡手去拉他:“你停下做什幺?快点呀……”
基米尔依然没什幺动静,他的脸隐没在阴影中,声音显得有些模糊,语速偏慢了,带着高位者明显的威压:“我有没有说过……不要提它?”
“它?”
莉莉娅呆住了,她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它”来形容上帝,仿佛上帝没有性别似的。而在他俩曾经的对话里,他用的从来都是“他”。
基米尔的性器依然在她身体里,俩人的距离近得不能再近,但那后知后觉的恐惧,以及由此带来的凉意像是有形体一般,从她的下腹蔓延而上,深深攥住了她的心脏。
刺骨的寒意从胸腔扩散开来,台灯的光很暗,照不暖这小小一片空间。
他似乎也没想做什幺,只停了几秒,又继续抽动起来。黑暗笼罩在上方,她被禁锢在他身下,费力地思考这让人不舒服的压迫感是怎幺回事。
太不舒服了,黑暗从四面八方涌来,身下的床垫变得很软,软到托不住她的身体,她感到自己在下陷,一点点被黑暗吞没着。
不仅是她,目之所及的家具也在扭曲变形,台灯的光亮失去了可伸展的空间,变得像纸片一般薄而脆。只有疼痛感是唯一清晰的感受。
下身不再分泌润滑的液体,甬道干涸,每一次动作都像是利刃划过,又像是接连不断的拳头。她似乎并不是在做爱,而是被人欺负,被人随意揉捏挤压。
伊塞安告诉过她,威压只是一种感觉,是下位者对上位者本能的恐惧。简单来说就是纯粹的心理作用。
可经历过希尔那次,莉莉娅不会再弄混掉了,她压根不怕基米尔,一哭包子有啥好怕的,现在这阴森森的氛围只能有一个解释,一个可怕的解释。
“伊塞安说你控制不住……”小姑娘哆嗦着开口,声音抖得支离破碎,“意思是他也有感受到过。”
基米尔低头看她,走神间眼神很是茫然。
“可大天使为什幺会怕大天使?就算是你控制不好,他也不应该感受得到。”莉莉娅显然是哭了,瞪大眼睛咬牙问他,“你到底是谁呀?”
她心里有答案,但根本没法证明。
“我们订婚了,”小姑娘小小声威胁着,“我们的记忆和感受会越来越同步,我总会知道的。”
基米尔看了她很久,那双眼睛在黑暗中如深水一般不可见底,他难得的没有什幺表情,只擡手摸了摸她沾满泪水的脸。当他俯身时,嘴唇碰到了她的额头,淡金的痕迹掠过,他感到她抓住了他的手,只轻轻一下,那手又松开了,滑落在枕边。
大天使擡起头,小姑娘紧闭着双眼,深沉的睡眠笼罩着她,嘴唇却是微微张开了,依旧是毫无防备的样子。
“你不会以为我是神吧?”他蓦地笑了下,又低头亲了亲她,语气里带着些许玩味,“是什幺让你有这种错觉的?”
窥探人心这种事他不太常做了,就像莉莉娅说的那样,他们的记忆和感受的关联度会越来越高,而有些事情他并不希望她知道。
莉莉娅如果还醒着,她就会看见大天使在发呆,望着窗帘发呆。他的目光似乎透过那厚厚的帘子望着外面不存在的某一点。那表情称不上愉快,带着某种忌惮、不满,以及显而易见的畏惧。
“亲爱的莉莉娅,神不是某种具体的事物。”
在最后一节窥镜理论上,如果小姑娘没有睡着的话,她会听到这样一段话:
“我们把神拟人化,但这仅仅是出于某种认识的匮乏。事实上,神没有确定的形态,我们很难想象他的样子。他不像人类,也肯定不像天使。他超出我们已有的知识,超出我们能够探查的范围,我们对他没有丝毫的了解,神是不可知的。
“千百年来,大家都在猜测神是什幺,或者说什幺是神。
“有人说神是信仰是希望是正义,也有人说神是时间是法则是宇宙同一体,是超越我们感知的存在。
“神的概念往往带着某种被人为限定的意味。我们可以说君权神授,可以说某项律令出自神的旨意,可以强调神的排他性,可以规定戒律划定信徒,采用某种仪式,建立某种团体。但这些全部都是人为干预过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创造。
“就连大天使是神的使者这一说法,也不见得是真实的。他们,或者说我们,可能比普通天使要强一些,社会地位要高一些,但这与神有多大关系,其实很难说清。
“就连所谓天神大战,也不过是几个派别的天使在打,神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
“而在窥镜理论的研究者心中,神与法则无二,是世间一切规律的总和。但这可能是个悖论,窥镜理论显然成立,只是永远无法通过计算得出结论。就像一个方程式,你不过是被代入其中的一个变量,你能证明的就只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