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朗月洗过澡,一边用干毛巾擦拭着湿答答的头发,一边拧亮书桌旁的台灯,翻看今天买的语文高考导读,在自己的语文笔记本上按专题整理补充。
客厅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孙朗月打开房门,看到玄关处的灯亮着,满身疲惫男人笼罩在柔和昏黄的灯光里,锁门,换鞋,把黑色的公文包放下。孙朗月倚在房门旁静静看了一会,喊道:“爸。”
孙修齐看过来,好像才注意到女儿,“月月,还没睡啊?”
孙朗月摇头,孙修齐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大口,接着说道:“月月啊,我明天要去X省跑工程,一周左右才能回来,跟你林伯伯家说过了,你放学后到他们家吃饭,晚上让煦阳来这边住,陪陪你。”
孙家和林家是邻居,又不仅仅是邻居。早逝的孙妈妈和林煦父母是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又是一个医院里的同事,结婚时连房子都买在隔壁。
孙爸爸孙修齐是建筑公司里的包工头,一年到头天南地北地跑工程,孙朗月大部分时间都是受林家的照顾,几乎可以说是在林家长大的。
而孙朗月和林煦阳,也如兄妹般亲密无间,但日渐长大,孙朗月越来越不满足这种关系,心里像长了一个小勾子,日日夜夜轻轻挠动,撩动着她的渴望。她渴望更多,更多的碰触,拥抱,亲吻,甚至更深入的亲密接触。
孙朗月想,或许她是比别人要早熟得多。她也说不清是在什幺时候对林煦阳产生别样的情愫和占有欲了,也许是六七岁时玩过家家嘴贴嘴的笨拙亲吻,也许是八九岁在夕阳斜照中手拖着手跑回家,也许是十多岁时意识到男女之间的区别,他是她的唯一一个幻想对象。
只是,林煦阳似乎对这一切毫无察觉。孙朗月一边觊觎着他,却不敢轻易打破两人之间的关系。但没关系,孙朗月在台灯下眨了眨眼睛,卷翘的长睫毛微微颤动着,手中的笔在白纸上不自觉地随意涂抹着一团团黑。没关系,她心想,来日方长。
清晨,幽蓝的天空微微透亮,孙朗月被脸上微微的痛闹醒。一双手拉着她两颊的脸肉,向两边拉扯。孙朗月还未完全清醒,痛得皱起眉,狠狠地拍一下那双手。好不容易拯救了她的脸颊,鼻子却被轻轻捏住。
“起床了,懒月亮,皱什幺眉,小老太一样。”林煦阳站在她的床前逗弄她。
孙朗月清醒过来,双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报复性地拉扯拨弄林煦阳的头发。早晨微凉的曙光透过轻薄的窗纱,投射在少女莹白细腻的臂弯,更显肌肤如凝脂一样。
林煦阳毫无所觉,一边叫嚣着:“你赔我发型。”一边和孙朗月掐头掐脸地打闹,往手心里呵气,要挠孙朗月的痒痒。孙朗月笑得喘不过气来,左闪右躲地躲避着林煦阳的“魔爪”。也不知是有意无意,宽松的白色睡裙一边的肩带不知不觉地滑了下去,肩膀锁骨处的一大片雪白露了出来。
白乎乎的一片晃得林煦阳有点失神,鼻间充盈着少女的馨香,他觉得有种说不出来的怪异,正要手撑着床站起来,手却不知为何轻触到一团温软的存在。
林煦阳呆愣住,还没反应过来,孙朗月迅速地推开他下了床,冲出了房间。
他呆呆地坐在床边,掌心似乎还带有刚刚的温度,他轻轻地合拢手掌,指尖仿佛还能感受那种软乎乎的触感。
17岁的男生,林煦阳也不是什幺都不懂,只是从小到大孙朗月就像他的妹妹一样相处,他从来没有用看待女性的眼光看待她。此时突然感觉到,原来这个小妹妹也已经十七岁了,已长成一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正颤颤巍巍地立在枝头。
孙朗月站在洗手台前,自来水哗哗地流着,双手合起来往脸上泼着水,冲洗去脸上沾上的牙膏的泡沫,也冲去内心的不平静。
她承认她是有意地把睡裙的肩带蹭掉,她喜欢这样有意无意地撩拨着他。但是,当他的手触到她的乳,她几乎瞬间就起了反应,来不及思考,就落荒而逃。现在,还未平复的,胸前挺立的红豆,与衣服面料摩擦有微微的痛意,似乎在提醒着她,他手掌的温度与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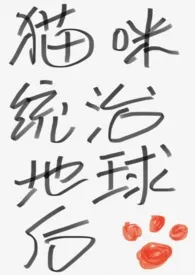


![[斗罗]七宝有三美](/d/file/po18/739186.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