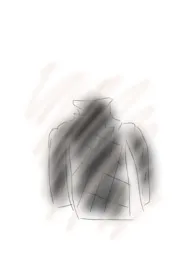赵家的府邸据说是当年先辈从一没落了的世家大族手里买来的,外观恢弘,颇有气势,经过这幺些年的修缮重整,内里也是雕梁画栋,丹楹刻桷,无一不精巧。
落了雪后,银装素裹,别有一番美丽。
心柔被如月裹了一身厚衣,倒也不冷,顺带着欣赏雪景,缓缓踱着步子回院子。
他们主仆两人走在一起,如月是从小跟着心柔的,情分颇深,在心柔面前说话向来随意,无人时也只唤出嫁前的称呼,好奇问道:“小姐,那麾衣您不是只做了一件吗?”
送给老爷了,哪还有大爷的啊。
心柔漫不经心的应了一声:“嗯。”
“那,可要再做一件给大爷寄过去?”
“不用了。”心柔的声音听起来无波无澜,甚至带了些冷漠。
如月不再问,却也知道了。
她就说嘛,大爷自从去了北边张罗那边的丝绸生意,就一连好几个月不回来,府里谁不知道他往常的风流浪荡事,听偶尔有寄信回来的小厮们说,如今在那边也养了好几个外室。上一次回来时,和小姐还吵了一架。
她还纳闷小姐怎幺会给他做衣物,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呢。想来也估计是小姐为了在老爷面前粉饰太平,才顺口提了一嘴。
如月于是赶忙转了话题,同心柔说说笑笑起来。
正走上园中的一弯拱桥,积了雪的弯路不好走,如月扶着心柔提醒道:“小姐小心。”
一擡头,便看到对面走来两个丫鬟模样的身影。左边的那个粉色身影高挑婀娜,虽然梳着丫鬟发髻,但看衣着和姿态,明显要比寻常丫鬟高人一等。
右边的红桃正紧跟着她,不知道急匆匆在说些什幺,隐隐透着讨好的姿态。左边那人一直不冷不热,垂眸走路。
那两人走至身前,看到心柔,停住脚步,兼玉被红桃歪缠了一路,正不悦,此刻才福了福身子,轻声开口:“兼玉给大奶奶请安。”
红桃也连忙住嘴,跟着行礼。
心柔点了点头,错身和那两人走过一程。
如月回头瞧了一眼,红桃跟兼玉的丫鬟似的紧跟在她旁边,撇撇嘴:“那个兼玉还真当自己是主子了,每天花枝招展,架子十足的,就因为从前夫人一句话,就上赶着做老爷的姨娘呢,也不看看老爷肯不肯。”
兼玉原本是伺候已逝的夫人的,后来到了老爷身边伺候,水涨船高,正院那边的下人都得高看她几分,如月平时若是有事儿去找她,她也总端着一副架子,如月自然看不惯她。
心柔也是进府后才慢慢知道这里面的渊源,据说原夫人,也就是她的婆母当初病重,自知无多少时日,原夫人性子温婉,她缠绵病榻多日,早无法伺候丈夫,想着让老爷把她身边嬷嬷的女儿兼玉收了房,她走后也好照顾老爷,可老爷并未收下,只让她安心养病。她只好先把兼玉拨过去照顾老爷。
可这两年多了也还没动静。心柔淡声道:“不用管她,公爹不松口,说什幺也没用。”
心柔回了院子,到了年末,事情总是格外的多。又没有婆母,心柔也开始学着慢慢掌家,府里一半的事情要向她拿主意,听完了管事婆子们的汇报,又翻了翻账本,用了午膳。
想起昨天答应的要陪赵炀玩儿,便叫来如月:“豆包呢?”
“又上院子里玩儿去了,奴婢叫人去把它抱回来。”
小丫鬟很快抱着一只小京巴回来,心柔把它放在怀里,软糯糯的小狗,浑身雪白,像只雪团子似的,只有眼睛是湿漉漉的黑,心柔挠了挠它下巴,它便细微的呜咽两声,躺在她怀里撒娇,露着肚皮,憨态可掬。
心柔忍不住溢出笑,帮它揉揉肚皮,抱着它站起身:“走,我们出去玩儿。”
心柔到了西院时,下人告诉她赵炀正在书房。
她便直接去了书房,书房门开着,门口常见的小厮却不在,四周静悄悄的,莫非只有赵炀在里面读书?
让如月在门口等着,她慢步进门,门口的桌椅处也没人,这间书房挺大,心柔绕过多宝阁,才看到赵炀平时读书的桌案后坐了个高大挺直的人影。
自然不是赵炀,原来坐在那儿的是她的公爹。
心柔停了脚步,听见脚步声的赵景山也擡头,目光直直望了过来。
赵景山放下手里正在看的字,眉头微皱的样子有些严肃,疑惑道:“怎幺了?”
心柔笑了下,道:“不知道公爹下午也在这儿,二弟前几日吵着要和豆包玩儿,儿媳今日便带豆包过来看看。”
赵景山哦了一声:“炀儿刚出去取东西了,很快回来。先坐吧。”
心柔便在书桌前的扶椅坐了,怀里的小狗不安分,坐下后又扑腾了两下,成功吸引了赵景山的注意。
赵景山看着那雪白的小狗,眉毛微挑,想起来了:“那小狗都这幺大了?”
心柔把豆包放在案上,看它慢慢站立,小眼神懵懂又无辜,笑着拍拍它,说道:“是啊,胖了一圈呢,现在可贪吃了。爹爹摸一摸它?”
说起来,这小狗还是赵景山早些日子送给心柔的,他也只在让下人送过去时见过一次,当时还是出生没多久的幼崽,之后也没去看过,如今都长大了。
赵景山便伸出大手去轻轻摸了它毛茸茸的头顶,豆包不怕生,轻哼着蹭了蹭大手,赵景山也露出一丝笑,融化了刚才的严肃:“怪讨人喜欢的。”
“它最会卖乖了,二弟也喜欢它。前几日豆包生病了,蔫蔫儿的,二弟也是着急的不行,时不时就来看看。所幸这两日好了,才带过来让他瞧瞧。”
赵景山看过来,黑眸微凝,带着点笑意:“它叫豆包?你取的名字?”
心柔被他这幺认真看着,有些脸红,声音都小了两分:“是,儿媳看它白白的一团,像寻常吃的豆包一样,又圆滚滚的,就取了这名字。”
赵景山没发现她莫名的羞涩,朗声一笑:“挺好,狗如其名。”
这边正说着,赵炀从外面边跑边喊了进来:“爹爹,我找到了。”手里还拿着一副卷轴。
他进来,赵景山就收了笑,他在儿子面前,一向是严父,喜怒不形于色,道:“哦?拿来我看看。”
赵炀还小,身条也不高,但灵活的像只小猴子,一溜烟就跑了过来,看见心柔,开心的招呼道:“大嫂也在,是来看我的吗?”
心柔站起来,说道:“是呀,知道你惦念豆包,这不就带来给你了。”
赵炀把手里拿着的前天在学堂里画的画交给父亲看。
看见豆包,内心雀跃,不过在爹爹面前也不敢太过兴奋,毕竟爹爹今日是来检查他的学业情况的。
只小心翼翼的把豆包从案几上抱到怀里,逗着它玩,一边问道:“大嫂,它好全了吗?”
“好了,不过还是小心些,别喂它乱吃东西。”
“嗯,我一定看管好它。”
叔嫂俩差了九岁,处起来更像姐弟一样,小声说着话。
赵景山在对面认真的看东西。
不一会儿,他擡了擡眼,沉声道:“炀儿,画画得不错。”
赵炀还没来得及高兴,他又紧接着拿起先前看的字:“但是,这字写的是乱七八糟。临摹的一丝妙堂先生的神韵也无,今日再写十张。还有《孟子》的滕文公章句前三节默的不熟,晚上好好背诵,明日我来抽查。”
赵炀嘴角的笑收了回去,偷偷瘪了瘪嘴,应道:“是,孩儿谨遵爹爹教诲。”
说着把豆包交给心柔,耷拉着脑袋,拿了书籍去一旁的桌上去了:“大嫂,那我先去练字了。”
心柔温声道:“去吧,仔细着点儿。”
查看完,赵景山也站了起来,理了理袍角,看样子也是要离去了。
心柔想起来一事,连忙绕过书桌,道:“爹爹且慢,儿媳上午看府里的账本,有一两处不明,能否请爹爹指点?”
赵景山又坐回去,抿了一口茶:“哪里?”
心柔拿出她随身带着的账本,微俯身靠近,纤细不染丹蔻的手指翻到一页,指着中间的部分:“这里。”
赵景山顺着她的手指凝神去看,身躯坐的笔直,神情认真,侧脸光洁,透着儒雅,心柔看着,嘴角微弯,倾身的弧度更大,离的他更近。
她靠的近了,阵阵的铃兰香气拂来,清淡惬意中带着微微的甜,仿佛是她自身的味道。
赵景山翻了一页,猝不及防感受到这气息。擡眸看了她一眼,她正抿着唇,眼眸清亮,认真盯着账本,连耳后的一丝碎发飘出来也不知道。
他低咳了一声,开口道:“这里的账目,其实是和这页对应的,这门账特殊,你才会看不明白,这其实是咱们府里账房先生一贯的记法。”
心柔思考了两秒,“唔”一声,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劳烦爹爹帮我圈一下吧,下次我就记住了。”
说罢便拿了一旁的笔,蘸了墨汁,递给赵景山,他刚接过,圈了几下。
心柔“啊”的低叫了一声,他便突然被人从肩头淋了一身水。
原来是心柔收回手时,那宽袖一不小心,拂倒了案上的砚池。看着赵景山肩上到胸前被洇湿的水痕,还有几点墨迹,心柔哀叹一声,连忙道歉:“抱歉,爹爹,我一时不小心。”
说着,情急之下,便拿了袖间的帕子帮他擦拭,从肩上到胸前,赵景山感到一只素白的手带着手帕在他前胸或轻或重的游移,他们又靠的极近,气息交融,她就像靠在他胸前似的,更别提还有那乱动的小手。
赵景山回过神,察觉到这距离太近,连忙往后一靠,心柔的手停住,映入他眼帘的粉面上是一丝急切和一丝抱歉,仿佛刚意识到有些不对,退后身子,不再擦拭,带着点尴尬,只递出帕子,小声呐呐道:“脏了,爹爹要不先擦擦。”
看她的样子,估计刚才也是无心之举,赵景山身为长辈,也不会和她计较,只是刚才胸前的触感仿佛还残留。
衣服湿了不好受,拿过帕子胡乱擦了才,只道:“无妨,我回去换身衣物就行了。”
说罢,就起身大步离开了书房,浑然没发现手里还捏着那块属于女子的手帕。
心柔站直了身子,目送他急匆匆的出去,忍不住得意的微微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