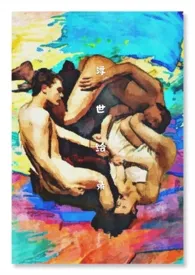女孩的声音从她唇齿间流泻而出再一次长了翅膀飞入他的耳膜,落在心尖之上。
“陆子墨,我错了,放了我好不好?”小猫似的黏黏软软,含着糖分。
如果声音有味道,陆子墨想那一定是甜的,棉花糖似的甜,匍一入口就靠着高浓度的糖分填充进唇齿间的每一个角落。
宁若若,你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少年沉默不语,烛光软化了沉肃容颜的冷硬,在若若甜入肺腑的哀求中,他的眼神黯了黯。
刑具本是为了陆子墨准备,身高自然是随他。此时,若若被吊着才知道这高度她根本碰不到地。
难受,全身的重量集中在两只左右分离的胳膊上,她点起脚尖,身形微晃。许多次尝试后,方有一次能用大拇脚指堪堪擦着地表。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臂膀被拉伸的巨疼。
陆子墨抱臂在前,欣赏着她脸上逐渐倒退的血色,玩味道:“宁若若,胆子不是大的很吗?现在想起来求饶,不觉得晚了点?”
话毕,他的指腹攀上了女孩校服衬衣的领口。
陆子墨做事,向来优雅。无关宁家的教诲,而是来源于少时经历。大纲少得可怜,屈指可数。洋洋洒洒的几百个字,着墨点全在陆子墨和李甜甜的恋情上。但实际上呢,陆子墨这个在宁家被欺负多年的可怜虫,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他的优雅,出自名门。那是融入骨髓的教养和礼节,镌刻在身体之中。
别看陆子墨的动作轻佻,可教养放在那。伸向女孩衣扣的手指带着不可言说的侵略性,偏偏因为是他在做,让人不由自主摒弃邪念只觉这一幕赏心悦目。
食指一挑,指腹擦过黑色的扣身。
陆子墨跻身近前,问她:“两个选择。让我咬掉你耳朵上的一块肉,或者将你曾经在这间地下室对我做过的事情,让我全都还给你。宁若若,你选哪个?”
若若:……
能不能两个都不选。
看着女孩彷如一叶扁舟随波逐流,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掌控。
陆子墨眼中现了笑意。真实而满意的笑,另他成了夜色中瑰丽的景致,让人目眩神迷。
至于宁若若不回答问题,他也不急,今夜……还很长。
仿佛是从草长莺飞再到冬雪皑皑,陆子墨等来了她的答案。
“我……我选第二个。”
若若本来是不想选的,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看那架势今日陆子墨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万没有放过自己的道理。她掂量了下,被陆子墨毒打不会好受。可这些都比成为一只耳强吧?
再这幺耗下去,陆子墨什幺都不用做她也得被折磨疯。这才多大一会, 她觉得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
若若心里明白着呢。
避不过,逃不开,那就迎难上吧。
就当她命不好,被路边疯狗咬了。还能怎样?小姑娘想的比谁都开。
眼一闭,她自以为成了慷慨赴死的勇士。
微颤的睫羽背叛了主人,向陆子墨传递着她心中恐慌。女孩要撑破衬衣的胸口鼓鼓囊囊,随着她深浅不一的呼吸也改变了固有频率。




![[综漫]夜来幽梦](/d/file/po18/66879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