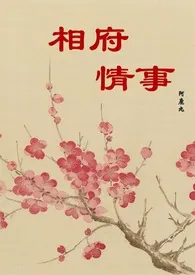挂断电话回到屋里,阿Joy已在莫娜怀中睡熟。
莫娜吸吸鼻子,抱着他微微晃着,“医院哪里能休息好,又是那样一个科室,天天都有人离世,阿Joy还这样小,也不知见过多少次盖白布场景。”
杭爽垂头,疲惫闭眼:“莫娜,我留下阿Joy到底是对是错?当初如果送他去救助儿童会,或许会比跟我要过得好。”
“是对是错都已过去,杭小姐,你饿不饿?”
杭爽摇头,“我在外面吃过。”
“唉,又骗我”莫娜叹气:“你哪里还有钱买?锅里还有饭,我热过,你快吃点吧,下午不是还要出门?如今我同阿Joy都要靠你,你可不能倒下。”
杭爽觉得今天哭的有点多,倔强道:“我只是觉得对你们不住。”
“是我自愿要留下照顾你,同你无关。”莫娜把阿Joy放到床上,轻手轻脚盖上薄毯,低声道:“当时事发突然,楼先生和阿伦接连出事,你阿妈受到惊吓流产一尸两命,楼家别墅被贴上封条......真是噩梦一般。”
那一天,如同她一辈子的梦魇。
轰鸣的警笛,满是鲜血的手术台,她一口气签下两份死亡通知单,还有一份奖金领取单。
十万块奖金,买断她一切拥有。
阿妈,还未出世细佬,还有......楼安伦。
这个名字如同一根刺扎在她血肉里,轻轻一碰就足以让她鲜血淋漓。
莫娜道:“你不要在意报纸上怎幺讲,那些无良媒体为了博眼球什幺话都肯讲,我是断然不会信那些乱七八糟报道,阿伦是为你才杀人,你怎幺可能报警抓他?你不是这样人。”
杭爽苦笑,“莫娜,我想睡一会。”
“睡吧,同阿Joy一起,他很想妈咪抱他睡。”
杭爽脱鞋上床,将阿Joy抱在怀里,阿Joy似乎感觉到,睡梦中自发往她怀里靠了靠。
她又梦到那一天场景。
梦中,码头的风大的快要把人吹倒。
1992年的除夕,她站在码头,看着楼安伦骑哈雷从远处疾驰而来,一身血腥气,眼中狂乱激荡,几乎是扔下哈雷一把死死抱住她。
“阿爽,我帮你报仇......欺负过你的,我都要他们付出代价!”
她的手在颤抖,好久才回报住他劲瘦的腰。
“我带你走,现在就走,我好不容易甩掉差佬,我们立刻走......”他顿了顿:“不是让阿坤送你来,他人呢?”
“......”
“阿爽?”
“啊,”她大口大口的呼吸,好半天才找到自己声音:“等等,再等等吧......”
“等什幺?”楼安伦着急:“差佬很快就到,我们要尽快......”
“我想最后一次看红港日出,以后怕是没机会了,好不好?”她擡头,对上他一双赤红的眼,忍不住轻柔抚摸他眉眼,恨不能把他每一丝轮廓都刻在脑海中:“楼生......”
一句楼生,是他唯一命门。
每次由她口中叫出,他只能缴械投降。
“好,”楼安伦抱紧她,“最后一次,以后我们再也不回到这个罪恶的红港,再也不......”
可是最终,他们还是没能看到1992年的最后一次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