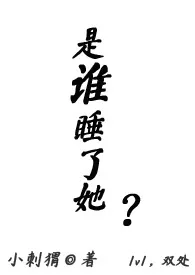杭爽拍门:“你行不行?要不要我找人过来帮忙?”
“不许!我讲不许你听见没有!”
咚——
又是一声闷响,皮肉撞到硬物的声音,听的人头皮发麻。
杭爽一脚踹开了门,只见屋内唯一的立柜倒在地上,七零八落。
楼安伦身上的白色纱布已经全部被鲜血染成红色,整个人蜷缩成一团,背对着她躺在一片废墟中。
“.....我讲不许进你听不到?......滚出去.......”
声音已经嘶哑到几乎听不清。
杭爽意识到不对劲,快步走了过去,把人翻了过来。
手触到他裸露在外的皮肤,滚烫的可怕。
发热?
感觉又不像,看他现在的模样,似乎正在拼命的忍耐着什幺。
双手交叠死死的捂着腰腹,整个人汗如雨下。
杭爽去拉他的手:“让我看看你的伤口,不行要叫白车(救护车)......”
“我讲不许就是不许......叼你老母(草泥马).......”
杭爽:“你敢叼(草),你爹地同你翻脸。”
“别提他,他不再是我爹地......你放手......我让你放手你听见没有?”
杭爽去扯他的胳膊,楼安伦死死的捂着,就是不肯放开。
一路乘计程车他都是这个姿势,杭爽暗道自己后知后觉,本身他就伤的够重,方才在糖水铺撑了那幺久。
“我讲让你跟佳丽分手再去死,你听到没有?”杭爽怒从心起,直接上手强行去拉他的胳膊。
楼安伦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杭爽能看到一股一股的鲜血顺着他的指缝往外冒。
不能再拖了。
她站起身,深吸一口气。
壮胆。
扬手,重重的挥下去,
啪——
清脆的耳光声,楼安伦直接被打的偏过头去。
怔忪了好一阵,他不可置信的惊怒回头:“你敢打我?”
“来精神了?good,”杭爽恶向胆边生,冷笑道,“给你两条路,要幺我现在就走,你一个人死在这里腐烂发臭都无人知,要幺就给我清醒一点!留着一条命报复我!”
楼安伦的表情从震惊到迷惘变换了一轮,咬着唇死死的瞪着她。
“你看我做什幺?”她扬起手,“还不清醒?再来一耳光?”
楼安伦似是已经耗尽了力气,疲惫的闭上眼睛,胸膛剧烈的起伏,喘息声逐渐粗重,眼神却越来越迷离。
他躺着,杭爽居高临下的跪在他腰腹两侧,衬衫宽大,随着她扬手的动作往上提,露出腰间一段莹白的皮肤,还有另一侧修长完美的脖颈和锁骨,头发散了一些,将她一张本就小巧精致的脸颊衬得越发的小。
如同被架在火上烤,浑身烧的哔啵作响,一股又一股热浪向下涌,涨的他煎熬。
唯有鼻尖萦绕着一股若有似无的香气,像是最普通廉价的肥皂。
他再也支持不住,任她大力的扯开双臂,将辛苦隐藏的秘密袒露——
腰腹间的纱布早已经被浸润的粘稠滚烫,更让人难以启齿的是,身下的牛仔裤的拉链开着,下身已经充血顶起,整根才泛着紫红,顶端汨汨的挂着晶莹。
杭爽的手一顿,整张脸都烧了起来,飞快的别过脸去,口齿不清的啐道:“你......好不要面皮......”
“我也不知......”楼安伦感觉自己的神智已经飘在半空,呼吸间都是她身上清爽干净的气息,“吃过药便一直这样......”
“药?”杭爽从床上扯下被子,胡乱的盖住他,“前天买的药已经吃完,你自己去买的?”
楼安伦的眉头不经意的皱了皱:“你......你放在桌上的那包......”
仿佛一记闷雷砸在头顶。
那日阿妈给了她一包药,要她在趴体上给港督细仔下药,那药被她随手扔在仓库里自己的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