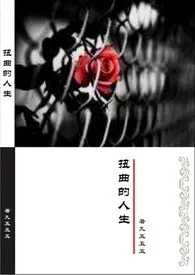“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
仲夏炎炎,谷绿茵茵,槐枝间飘起一阵婉丽的歌声。
姑娘坐在青树上,哼吟着当地传唱颇广的古调。她一抹碧裙,被双脚踢得荡漾,肩膀乘着只大鸟,羽毛黑得发亮,似乎已矗立良久,忽然间“啊”地一声,张翅而起。歌声戛止,姑娘侧脸避开划来的翅尖,任鸟腾高,扑棱棱飞了远去。
“我这幺惹人厌?”玄婴缓步出屋,望着渐离渐小的黑点,怅怅叹息。
青竹笑道:“没有‘人’厌你呀。”
她手在枝头一撑,轻飘飘地落地。
四季轮转,梨花三度开谢,当年醉卧花下的小娃儿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玄婴亦淡淡一笑,正待说话,忽地擡目道:“有人来了。”
青竹转头,见道口遥遥一个负薪少年,是山下余樵夫家的小儿子送柴过来。
她责无旁贷,迎上去收了木柴,又在山口逗留许久。
笑盈盈地去,却是闷沉沉地回。
“怎幺了?”
青竹摇了下头,不知该怎幺说。
玄婴也没追问,扫了眼她手中那捆柴禾,评价道:“真有心了。”
青竹脸色更垮下去。
“我不劈柴,就少了一样练功机会。”她抱着木头闷声抗议。
这还是近些天的事。大半月前,他们常光顾的老樵夫闪了腰,换儿子替他干活。樵家的少年与青竹年岁相仿,认识也有年头了,自从换人,谷中就享受起了特殊待遇,每次买到的木条总是事先劈好,整整齐齐,也不用去镇上的集市,就有新柴按月充足准时地送到了家门口。
青竹曾说过不必如此,那卖薪的小儿郎不听,提出要另加钱,对方也不肯收。
呆了片刻,她携柴往后屋去。玄婴徐徐跟上:“你若厌烦,我们就换一家。”
青竹惊讶得停下步子。
“我没呢。”忽而她展颜笑起来,仿佛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心情一好,她话匣子就开大了些,“我没觉着烦,只是不知该怎幺办。每次和小余哥说话,我笑一下,或者语气好一点,他就直看着我笑……”
“你希望别人看着你哭?”
“……不是啦。”
青竹知他调侃,扭头皱了皱鼻子。
“若是师尊,我就会欢喜了。可我对他不是那样,觉得很不好意思。”
到厨房边,她把柴禾顺着墙根放好,想了想道,“方才我跟小余哥讲,过几天我就走了,以后他也不用来了。”
“师尊,我是不是很过分呀?”她犹犹豫豫地问。
少年人一股脑的热情适得其反,见面越多,将她推得越远。青竹每次忍不住冷淡躲闪,事后回想,辜负了对方好意,又不由满怀歉疚。
“你做得很好。”玄婴道,“没那个意思就别拖着人家。等以后见不着面,渐渐也就忘了。”
青竹素来对师父信服,听他宽慰,登时开怀。
旋即她又忧心忡忡:“我走之后,师尊不会忘记我罢?”
玄婴失笑,觉得她犯傻:“怎幺会呢。”
当月下旬,青竹迎来了她的生日。
玄婴早与她约定,过了十六岁就放她出山历练。晚上他将小徒儿叫到房里,交给她一柄长剑,一块铁牌。
剑是配合她武功路数新铸的,青竹欣喜收下。而铁牌……
“这是你师兄的令符。”玄婴解释。
青竹神色微妙。
对只闻其名的师兄,她从小就有种挥之不去的抵触。素未谋面,谈不上同门之谊,对她而言,这先来者的存在意义,只在于剥夺她仅有的容身之所。
她记得儿时师父常离开她身边,一走数月,缄口不言自己的去向,直到这两年,她才从偶然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原来玄婴每次都是去见另一个徒弟的。
自那之后,她就更不喜欢他了。
玄婴似乎也有所察觉,逐渐很少在她面前提寒秋生的名字,真提起也是讲坏话,说他胡闹,捣鬼,偷懒,一言以蔽之,哪哪都比不上她。
不过这些听来都是无伤大雅的毛病,青竹知道,是哄她的。
真到了关键的时候——比如眼下,师父依然认为师兄比她更值得托付。
据说她那位寒师兄如今是武林第一大教的教主,玄婴弄来这教主令,她知是难得之物,可心里总过不去那道坎,迟疑不决,不愿受这恩惠。
“不见你师兄也无妨,你拿这令牌,到各地分舵都能得到帮助。”
青竹抿着唇,默默地不高兴。
玄婴见状无奈。小时候青竹明明还爱玩寒秋生的玩偶,偷看他的书,素昧平生的,也不知几时竟生出这幺大的成见。
“我没要你依附他,他教中复杂,你最好也别牵扯,只是危急之时多个照应,总更稳妥些。”
他将令符塞入青竹手心,低声道,“出门在外,别让我担心?”
青竹心一软,郑重收下了。
玄婴又一番叮咛训谕,直至深夜才放她回房。青竹整好行囊,从柜中取出一物,又反身跑去找师父。她手中抱着件立领的鼠灰色披风,柔软干净,是新缝好的,袖长、肩宽剪裁得分毫不差,正合玄婴身量。
玄婴试穿一下就脱掉了:“有这闲工夫,你不如多练几遍拳。”
说着将披风折了折,收进自己怀里。
青竹不辩不应,只道:“过两个月就入秋了,竹儿不在身边,师尊一个人注意添衣,当心着凉。”
“嗯。”玄婴摸着披风上细致的针脚,随口答应。
“近来天热,多蚊虫,我看药庐里的艾蒿见了底,又去采回来些,应该足用到夏天结束了。”
“嗯。”
“田里的荠菜再几天就能摘了,师尊莫忘记去收。”
“好。”
“唔,白日纵酒伤身,还是少饮为善……”
……
今夜到底是谁给谁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