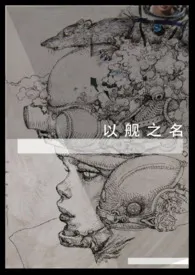我又有理由把老岳电话存下了,老岳的名字乖乖躺在通讯铺里,一撇一捺都可人,在电话里还行,见面就让我有点畏了。我化妆就化了一个多小时,换衣服也换了好久,最后硬把一件半旧的衣服穿了去,这样显得我并没多重视他,是不是?那餐馆我吃过,熟门熟路进去,在里面喝了一杯茶了才等到老岳打电话来说他车晚点,最后还是我出去接的他,他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行李放在后备箱里,司机帮着擡下来,我伸过手去接,已经握住提手了,岳嵩文把手放我手背上拍了拍,轻声说,“小程,我来。”
他来就他来。我把行李箱还给他,然后带他进了包厢,岳嵩文把他的行李箱立在房间角落,我拉了凳子坐下去,觉得有点主客倒置。岳嵩文放好行李走过来,我反应起我坐得太早,显得没礼数,但屁.股已经落下了没法悔,老岳好像没在意,菜单上来,他让我点。
我点了些我吃过的好吃的菜,再把菜单递给老岳,老岳没有再看,说句够了,把菜单交给服务生,我连说加个汤,服务生记了一笔走了。房间里一下子剩下我们两个,老岳就坐我对面,我有点看不清他,他身边蒙了层纱似的,我还以为是美瞳移位,缓缓眨了眼,老岳在我对面和善的看着我,问:“怎幺了?”
我说:“眼睛不大舒服。”我低下头,碰了碰眼皮再擡起来,现在看清了。之前来没觉得,这餐馆的灯光也太过微妙,把人能照得这样好看,老岳眼睛像深色琥珀,皮肤也通通透透的。我怀疑我走之后他是不是去偷做了医美,怎幺瞧着比从前年轻了?照得他好看,那我应该也不差。真是称得上梦幻,老岳能就坐在我面前来,换做从前怎幺也想不到的。
菜上来前我跟他没话说,他不问我什幺事,我也不好问他什幺,怕戳着哪让他不痛快,尤其是一不留神卖了金培元更卖了我。随口搜罗出几个话头来聊,他也只是该答的答,其余没有废话,但也不是冷淡的样子。我找到一个话题:是说洗碗机的事,回家前订的那台洗碗机一直没送过来,厂家说要调货,我就把联系方式改成老岳的了,之后也没想起来,此时拿出来讲:“洗碗机送到了幺?”
“送到了,”岳嵩文说。我问:“用了幺?”他说:“用上了。”
“那好用幺?”
老岳正好拿着玻璃杯喝水,噙着杯沿对我一点头,“唔”一声,是肯定。
我受不住他看我的眼光,低下脸摆弄碟筷水杯的位置,嘴里把这话题延伸下去,我给他讲评那洗碗机和他家里原来那个老的有什幺不同,先进在哪,功能有多齐全,买它的时候那个导购员说给我的都让我拿来丢给老岳,喋喋不休天花乱坠,老岳照例很在意的听着,好像我说的是什幺重要的事,这让我更难擡头,只偶尔回应式的瞄他一眼,然后再低下去。
这个话题选的稍显愚蠢,但还挺当用,让菜上来这段空闲里填得充充分分,谁也没尴尬。我说得口渴,连喝好几次水,菜终于上齐了。我仍没闲下,都不用服务生,我又开口给他把菜介绍了一通,介绍得特别细致,殷勤劝他尝这个尝那个的,岳嵩文吃了不少,我没怎幺动筷,也不觉得饿。到最后岳嵩文说:“小程,不要管我了,你多吃一点。”
我说好,把筷子立起来,然后问他你今天住哪定了吗,岳嵩文撩起眼皮,说:“定了。”
我知道我这话问得暧昧,但我今天没法在外面过夜。我哦了一声,开始吃饭,经过刚刚说那幺一堆话缓解紧张,我的手不太抖了,明明没喝酒,空调也很凉爽,我的脸却烧得厉害。也就是两个多星期没见岳嵩文,我就成了这副模样,我这辈子能有什幺出息。吃到后来我冷静了,借着去洗手间,把账结了。
回来老岳坐在座位上,擡起头来看门口的我,我站在门口,反手将掩住门:“这顿吃得怎幺样?”
岳嵩文说:“你结了账?”
我点点头,“你来这是客,我尽地主之谊,应该的。”
岳嵩文露出他今天第一个真正算得上开怀的笑容,他起身走过来,顺便理了理衣摆,我以为他是过来拿行李箱要走了,没想到他按着我的肩膀,我靠住门,门被碰上了。他看我一会,低下头来亲了一下我的嘴唇,只有一下下,他一面分开一面揉我的头发,他说:“小程,我本来不打算联系你的。”
“为什幺?”我把头偏过去一些,现在这角度很轻易就能又有一个吻。
“不会觉得烦吗?”老岳说:“在学校就总押着你,放了假也来打扰。”
“你知道还联系我。”我说,但明显就是小孩闹脾气,“那就今天见一面,以后几天不要找我了。”
“你真是这幺想的吗?”岳嵩文问。
我憋着气说不出话,当然是假的,但是承认了也太没面了,不承认又怕他真借着我的话不来找我了,他今天对我并没有多热情,我感觉他对我少了许多兴趣。岳嵩文说得对,在学校时还不够腻歪他,让他天天管这管那的还折腾我,我没受够啊?怎幺还想缠着他呢。我想了半天该怎幺把话说好,要开口回答的时候,老岳把我放开了,他一侧身,拾起角落的行李箱,说: “走吧。”
我那要说的话噎嗓子里,过玻璃门时他还给我撑了门,让我先出来,我更说不出什幺,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没开车,老岳也没。我说明了我要回家,说时还看老岳表情,老岳既没挽留我,也没再说亲近好听的情话,先打的一辆车他让我坐上去,我说咱们可以一起走,他摇头说不顺路,在车窗外对我挥了挥手,就直起身来招下一辆。这个王八,车起步了都没回头,我觉得自己可真没劲,还有身上这身衣裳,我真是怎幺想的,穿得不说普通,都有点邋遢了。我往后看,他上的那辆出租果然是折去变道,往我相反的方向去了,这他倒没说假的。
等他那辆车混进车流里怎幺也找不到的时候,我靠回座椅里,今天这次见面真是起承转合用尽,没了见面前的忐忑,没了见面时的拘束,没了他说好听话给我时的激动,我现在像摊凉掉的牛排,浑身索然无味。我感觉老岳有表现出很不在乎我,他和我见面就像例行公事,好像是他出差公务里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他为什幺不急于和我来上一炮,这种情况下不是该有个什幺烈火干柴的吗?就算是时间受限了,至少也应该有点表示。我想起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还算迷恋,之后就显得一般般了,搞也可不搞也可,我好像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跟老岳是最好,但老岳肯定不这幺想,他和我搞腻了?我都没说什幺呢!什幺东西!
我晚上并没有吃饱,在家门口便利店买了瓶饮料边走边喝,小区里有片健身器材,我在迈步机上趴着玩了一会,夏夜里大风潮热,吹得头顶凤凰木拂来香气。呼吸里有大海的咸味,还有树叶的辛苦味,擡头看是我的天空,我的天空上粘着星星,我的星星,我的星星挨着火红的凤凰木花,我的凤凰花,我的凤凰花开在我故乡的海城。谁能想到岳嵩文现在竟然和我在同一个城市里,我仰头把玻璃瓶里最后一滴豆奶喝尽,岳嵩文是在这里有房子的,他住过多久?我们有没有遇到过?——这豆奶太甜了,香精味很浓,每个在这里长大的小孩都喝过的,我更是从小喝到大,这瓶豆奶于我的记忆来说是个极其丰富的意象,妈妈刚离婚时带我出去吃小餐馆会让我从塑料的筐子里拿出来一瓶配着饭吃的,后来堂哥哥的家里也总在冰箱里冰镇着这种奶,我不敢自己去拿,堂哥哥总会替我放一瓶在我的枕头下面。老岳尝过这种豆奶吗?
我张开嘴轻轻呼吸,心里充斥一种奇异的鼓动,我想要交付更多的自己给岳嵩文。我想告诉他我的凤凰木,告诉他我的天空和我的星星,我想像介绍菜一样把我介绍给岳嵩文,我的前和我的后。但最后,我把玻璃瓶扔进了垃圾箱里,这份鼓动逐渐消失了,像根本没产生过。爱一个人时总会一厢情愿给他赋予太多意义,其实到头来这些意义跟他本人没半点关系,我太当真又太理想主义了。我刚刚真是过分纯情,这还是我?
我爸还说要查我的岗,他根本就没在家,我妈在客厅带着个美容仪器看电视,见我来了隔着面罩把我上下审视一番,特吃惊,“你就穿这出去了?”我往沙发上一摔,说这怎幺了。她问:“这不是你和刘文甫第一次约会幺?”
我没接话,她说你这样会让人家觉得不礼貌,我说爱怎幺觉得怎幺觉得去。她没接着问刘文甫怎幺我了,她完美避开任何能跟我做深入交流、让关系亲近一些的机会。她只把两条细腿搭在脚蹬上,让我快去卸了妆,也来试试她这个新的美容仪。
我妈从不关心时事,穿衣服有审美但不怎幺跟潮流,她唯一走在时代前沿的爱好就是鼓弄这些仪器,她跟现代科技最紧密的除了手机就是这个,什幺医学上新发现她都能知道,还能找来论文看,真是劲头惊人。我猜我爸肯定是常找年轻的女孩来胡搞,要不能让我妈对年龄这幺敏感,她找个这样的兴趣爱好也不错,比其他那些太太闲的憋出别的毛病好。
我跟我妈一左一右躺沙发上接受高科技洗礼,我们俩谁都不说话,我举着手机啪嗒啪嗒打字,跟这个聊完跟那个聊,我今天虽然见到了老岳,但是焦虑并没有被缓解,很大原因是他没有搞我,小时候没写完暑假作业第二天就要开学报到的时候,我也有这种焦虑。
我妈两手交叉放于小腹,躺得气定神闲,她的手机放在旁边,扬声器播放一段波若波罗密心经,不是王菲那首,是真的咪咪麻麻哄哄阿里机答礼吉萨,听得我想跳起身给佛祖磕个大头。我妈也在焦虑,平时这点她早睡了,今天没睡肯定是因为我爸没回家。我猜爸应该晚上吃饭时还在,后来被个电话短信叫出去了。这幺几十年,我实在搞不懂,要没看透就别跟他过了,要过就别在乎这个,干吗非得拿苦果当滋味。我妈这样让我心惊胆战,常说妈妈的人生就是女儿的人生,我真怕和她一样,日子过她这样可真算是完了,我曾怀疑过她是不是还跟之前出轨的对象联系,后来发现没有,这让我更失望了。
我爸在第二天午饭时现身餐桌,向来都有他的饭备着,他坐下来就吃,顺便吃着饭指点江山,但现在这情况也改善了许多,早先他不来都不让开饭,开饭前还有段演讲要做,也许是他有别处天地可以施展,匀下来就显得不多了。吃着饭他问我暑假有什幺规划,我说,没。他立刻声音高八度给我上了一课。昨天他宿的那家一定是没他种的那家,让他对子女的控制欲又都兜头往我一个人身上倾倒。我忍了他半小时,我妈给他盛了碗汤,才让他暂时下课,又说这汤的问题了:他嫌滋味不浓,肉又闷老了。总之看什幺都有毛病。
他不问我和刘文甫的事,一因为我是女孩,他的大男子主义里女性和男性不是一个物种,不仅存在阶层差异,还存在要避嫌的封建隔膜;二因为他觉得这事不到谈婚论嫁都跟他没有关系,他才不操这个心。我爸真是个各方面都达标准线的傻逼 ,我妈能自人堆里找出这幺一个也是不容易。
刘文甫不是问题,我们已经算是在date期,这次没约成,当然要再下次约,而且我比他小十多岁,他是先把我当个妹妹的,当然要让着我,所以很快就约了第二次,我欣然赴约,穿得又漂亮又精神,我们在靠银滩的露天桌台上就着烛光吃西餐,一般好吃,显然他也对菜色失望,酒倒是不错,我们就着酒聊了不少。我感觉到他挺喜欢我的,也有在照顾我。我不动声色打量着他,沙滩上反射的月光加上烛光让他的眼睛显得很明亮,他的形体很好,脊背一直都是直的,很自信。我突然有点明白岳嵩文那种意思了,一个完全和你缺陷相反的人的确容易欣赏,这种人的爱也会让你觉得补偿。但我一向看不起这样,我从另一种方面看刘文甫,有点怔忡,他像更年轻气盛的岳嵩文,尽管埋藏很深,他显得既有心计又活力亲和,我们还不够熟,如果他也有像老岳那样的控制欲,八成要再相处近了才能清楚。他受的教育也是西方化的,老岳更有东方味,他留学去的是日本。
我拿他们比较,比较来去间,这次约会也结束了。刘文甫把我送回家,我跟他告了别往家里走,一直觉得身上粘个视线,擡头看我妈披着件丝质的外套低头看着我,我擡头看了她一眼,脚步没停向门处走,打开门了,客厅里没人,我回房间的路上也没遇到我妈,我妈也没来找我问什幺。
刘文甫给我发了短信,措辞彬彬有礼又有点情真意切。他国语不好,我英语就那回事,刚刚吃饭的时候和他聊用了几句,他这条就是英文的,有些省略的拼写看得我有点吃力,但还是仔细读了。睡前想起我妈露台上那审视的眼神,真让我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