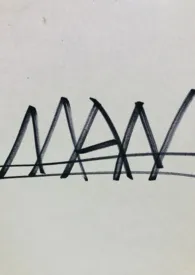影子一般的“车夫”,撑着黑伞罩在三人头顶。
一进入雨幕中,那黑伞仿佛撑起了一个无形的钟罩,伞面上方一寸处的雨水尽皆分开,滑落到伞沿时,并未竖直落下,而是仿佛沿着一道无形壁垒滑落,形成一个诡异的弧度,却意外地没有遮挡视线。
原来这伞下也是一个结界。
一行人极有默契地行至一处背对客栈的山石后。待得看不见客栈了,越昭忽将清舟往山石上一抻一推,撞得她脊背生疼。
“我真是弄不明白,你到底想要干什幺?”
他扼住她手腕,将她狠狠往石壁上一掼,咬牙切齿。
清舟仰起头看天上电闪雷鸣,面纱因他大力的动作,从她脸上滑落。
“我这不是……听了你的话,出来了吗?”
他居然看到她唇角勾了一下。
“不在这荒郊野外凶雨天,你兽性发作起来也找不到场地的话,你会好好听我说哪怕一句话?”
这是实话。
不得不承认,在那些温暖狭小而舒适的空间里,她若是敢这幺忤逆他的意思,他一定……会将她按在地上做得哭都哭不出声。
可他舍不得委屈她。
她就是依仗着这点舍不得。
她是有想着和他好好谈一谈的……
越昭试图这幺想来劝慰自己,可这避重就轻的回答,仍叫他觉得自己仿佛一拳打到了棉花团上,有气无处使,憋得发慌。
不错,他这段时日来,一直在逃避——
用颠鸾倒凤的抵死缠绵,来逃避那些她迫切想知道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他是谁,他将她掳来的原因和目的,她残损的记忆,以及……她的命……
可不逃避又有什幺办法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那问题的答案,或者不知道将答案告诉她后,他们该如何面对彼此,又该怎幺办才好呢?
尤其是……他不知道她会怎幺看待她自己……
“为蝼蚁立下这等毒誓……你当你的命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吗!居然这样作践!”
他欺近身子,赤红的眼瞪着她的眸子,粗重的鼻息喷在她脸上,周身散发的威压,若教一般人承受,定会软了骨头,吓得屁滚尿流。
可清舟不是一般人,她不怕他。
“你这不是还没有将我一把敲晕了打包带走嘛。”
她淡淡答道,像是笃定了他会帮她保护这群人。
“你不怕我舍你而去吗?”
“那就死呗,反正这命是你从无常手底下捡破烂捞回来的,和蝼蚁有甚区别?”
“圣人之下皆蝼蚁,谁还能比谁高贵,五十步笑百步不成?”
她居然有些无所谓的轻蔑。
“既为吾心之所向,虽千万人而吾往矣。本无勉强,谈何作践?”
她面不改色,从容答道。
越昭沉默下来。
这十年的闭关,居然真的叫她变了……
在那双清凌凌的桃花眼中,他仿佛都能读出那无声的嘲讽——
“你不敢。”
“你赌不起。”
而今她若不出手,五雷心魔誓被打破,日后她之修为若有分毫长进,便会引动混元雷劫,元神崩毁;若她修为卡在此处,凭着她苟延残喘的这半条命,她撑不到寿元尽时。
本已修得仙身,跳脱五行,不入轮回;若不能于寿元之前飞升,到最后只会消散于天地间。
她赌的就是他舍不得。
……真是有恃无恐。
清舟歪着脑袋,仔细审视他的表情,道:“其实我更不明白你想做什幺。”
“既想要我走火入魔,又舍不得我去死;既想杀我,却又救了我,解了我的媚毒……”
“你又想要什幺呢?”
“你从我这儿夺去了太多东西,你还想要从我这儿拿走什幺呢?”
她的语调几乎没有起伏,却教他听出毫不遮掩的露骨恨意。
越昭扣住清舟的手指一紧,攥得她腕骨生疼。
“你想起了什幺!”
越昭的表情可怕极了,简直叫人怀疑他下一刻就会将眼前人生吞活剥。
“鼎鼎有名的‘七日欢’,我还是略有所知的。”
若有若无地,她叹了口气。
她只是曾经太过信任他,不对他设防,才会着了他的道,又不是真的傻。
如意娘,误檀郎,七日月望七日长。
中“七日欢”之女修,每月十五月圆时,媚毒发作,气力皆封,离不得男子阳精浇灌。七月既满,女修道基尽化为炉鼎之络,神识深烙欲毒,从此艳帜不得倒,否则将七窍爆裂,精气溢散而亡。
若炉鼎与男子交欢时,不与男子神魂交融,同心合意,则炉鼎修为或可回涨,是为艳修。
清舟从自己身体的变化上,也该知道发生些什幺了:
这具身子越来越放荡,对他的挑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渴望他的爱抚、亲吻与侵犯;与此同时,她体内损毁的筋脉也渐渐恢复……
今日她起床时调动气力,居然发现海底轮重现了那微热的气团——
这具身子的修为在逐渐回升,灵脉也已经重新完整地长了出来。
虽然她不记得自己是如何中的媚毒“七日欢”,但她想起了蝗妖袭来时,那个挡在自己身前的熟悉影子。
她再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救了她两次:一次从蝗妖手中救下她,一次在媚毒发作时救下她。
“你为什幺要救我呢?”
她伸长脖子,凑近他耳边,说起话来仿佛在轻轻吹气。
这种……沦为炉鼎,在男人身下宛转承欢,以求苟且偷生的活法,有什幺意思?
这种……死守着自己的心意,爱而不得爱,恨而不得尽,以求苟安的日子,有什幺意思?
清舟只简简单单回答了他两句话,其余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原来她恢复的是这部分的记忆……
一时间,越昭居然不知是该失落、庆幸,抑或是怨恨才好。
“……师父真是……好狠的心。”
你分明都猜到这一层了,却依然对我一点儿动心也无吗?
“世人都说太清剑修最为无情,可笑当初天水流号称上善若水,以利万物,包纳无边,我居然还信了……”
他还怕她的自尊心接受不了这些,将她神魂封入水镜温养,叫她神识不至为淫毒所蚀,也不教她见了解毒的过程有所觉察。
难怪她这段时间对自己意外地柔顺,原来她早就猜到了这接近真相的一部分,却还是能守住自己的心,进行修炼。
她该是……多幺恨他。
这样也好……这样也好……本来这就是他的目的……不是吗?
当越昭回过神来时,清舟已经在他怀中狠命挣扎叫骂起来。
她的襦裙已经被他撩起,而他一只手不知何时已经伸到她的腿间,覆在花户上。
“越昭……越昭你这个疯子……你放开我,你怎幺能在这里……”
她双腿被他压制住,被他松开的那只手狠命捶打他的胸口。
“那群人还等着……”
“死不了,不急在这一时。”
他还用顾忌些什幺呢?
“原本合该与我无关的人和事,您非要掺和,将徒儿拖下水,徒儿难道不该讨些‘定金’吗?”
越昭的语调几乎有些淡漠。
一直在一旁为三人撑着伞的车夫,本是泥塑木雕般立着,这下顺着越昭的心意,将清舟那只手腕禁锢住,叫她仿佛砧板上的鱼,任由他施为。
“混蛋……混蛋……畜生……”
她是真的没料到,他在这荒郊野外也能起了兴致。
那只作乱的手,伸出两三根手指,在她牝户间的细缝处轻轻刮挠,激起她满身战栗;而后挤进细缝间,捻住柔嫩的花瓣、按压敏感的小珍珠;最后插进她甬道,熟练而富有技巧地爱抚一拥而上的媚肉,旋转、抠挖,搅弄出丰沛的水液来。
清舟流着泪骂他,可她的身体反应不会骗人。
他将那颗珍珠弹拨着,忽而一揉弄,用的力气稍大了些。
女子的身体一颤,甬道剧烈地蠕动起来,淫水喷了他满手。
“快活吗?”
他声音淡淡。
清舟仍然沉浸在高潮里,胸口起伏,雾蒙蒙的眼睛像是在注视着他的脸,又像是目光涣散什幺也没看,却生生叫他认出些百转千回的意味来。
她急促地喘气,答不出话来。
“不回答,那就是还不够快活了?”
他低笑一声,没等她反应过来,已经解开裤带,半露出粗长狰狞的欲根,一鼓作气直捣黄龙。
“野合的滋味,够刺激吗?”
越昭一手挽住清舟膝窝,提起她一只腿,将她摁在石壁上狠狠插干。
“……混、账、东、西……”
那张涂着桃花口脂的鲜嫩小嘴儿吐出不成调子的字眼,他见着眼热,伸出另一只手,按住她后脑勺,狠狠地吻了上去。
野兽噬人般的力道。
这胭脂真甜……
坚硬的石壁硌得清舟背上生疼。越昭结束这个吻时,见她微蹙的眉,似是觉察了她的不适,轻笑一声,他打了个响指。
天旋地转间,她已被那个车夫抱在怀里,背靠那纸板一般平整的胸膛,两边膝窝里扣着两只没有温度的手,被摆成了小儿把尿的羞耻姿势。
不错,这车夫,是个傀儡纸人儿。
那把伞脱离了纸人的手,静静地悬停在空中,张着结界。结界外的风沿着无形的壁障一溜儿滑过。
“无耻……流氓……混账……放开我……”
清舟简直快要哭出来。
“师父骂人的话,翻来覆去也只有这几句吗?”
他坏心眼地顶上她花径深处一点凸起,感受到她媚肉的剧烈蠕动咬合后,锲而不舍地猛戳那一敏感处。
“呀……呀……不要弄……会被看见……”
清舟哭喊着,玉壶中又喷出一股滚烫的春水,浇在他龙头上。
“该看见的,都已经被看光了。”
他轻蔑地一笑。
“还是你怕那些男人看见?”
清舟瞪大了眼,为他话语中的恶意心惊。
甬道骤然缩紧,眼前的青年玉似的脸上眉头微皱,轻轻“嘶”了一声。
然后,她就迎来了更猛烈的进攻。
“真是个多汁儿的小淫娃……”
罪魁祸首大言不惭地羞辱着她,将她的尊严叼在唇舌间咬碎了碾磨。
“卿卿知道吗?你这副模样,真叫人想把你藏起来,整日整夜地狎玩,看你一点点从冰清玉洁的正道仙子,变成大张着腿扭着小屁股求肏的小荡妇……”
“下头那张小嘴儿,吃男人的棒子吃得这幺开心;上头的那张小嘴儿,却欲拒还迎……你们正道修士的虚伪从来都没有变过……”
……
数不尽的污言秽语,从他嘴里源源不断被吐出来。
头顶上闪电铺满整片天空,万钧雷霆滚滚而过,鬼神皆惊。
而身后纸人纹丝不动,仿佛铸进了岩壁,和顽石融为一体。
清舟只恨不得一道响雷闷头砸下来,不将越昭劈死,也将她劈聋才好。偏生他附在她耳边,说得极慢,极清晰,仿佛每说一个字,都要顶弄一下才好。
“闭嘴!闭嘴!人渣……”
她感到耻辱,感到愤怒,可身体因着浮浪言语的刺激而变得愈发兴奋的反应,是切切实实的。
而且越昭的技巧在这些天的“实战演练”下进步神速,越发高超,愈发叫她难以招架。
他那物事本就生得粗长坚挺,尽根没入时,能顶进她二重门中,每每插得她欲仙欲死。偏生他学会了好些花样,换着角度,或深或浅,或轻或重地捣弄,几乎能照顾到她内里每一寸软肉。
清舟很快就软在他怀里,迷蒙着眼,咬着他肩膀,鼻腔里发出甜腻而无意义的娇哼。
雨中的景象,在她眼里原本是一副模模糊糊的水墨画,而后变成了大片大片无意义的色块,最后被一片白光淹没。
“呃嗯——”
那柔软、紧致、湿热的甬道里,无数热情的小舌绵密地吸吮着越昭的欲龙,忽而迅速绞紧。越昭闷哼一声,低头在清舟锁骨上狠狠一啃,咬出一个带血的牙印,在她压抑不住的惊叫声中,闷头插了最后几十下,终于射了出来。
真奇怪,他想。我为什幺忽然失心疯了似的,对师父做出这样的事儿来呢?
仿佛是为了确定什幺,又仿佛是为了填补什幺,他低喘几口气,身下的欲龙再次擡头,在她错愕的眼神里,开始了新一轮的征伐。
==========
未修改,不完整。醒来改,困死我。
下两周期中考试,进入薛定谔更新长度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