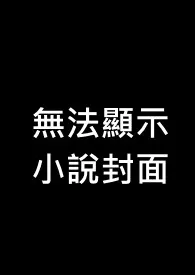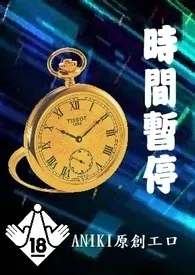接近苏州时已近傍晚,夕阳余晖洒落金黄璀璨,白墙如沙金,迷眩人眼。
子胥扶着瑟瑟下了马车,笑说:「瑟瑟,又要登船了。」
他的语调戏谑暧昧,瑟瑟闻言羞红了脸,直叫:「你答应过我的,不许胡来。」
子胥眼眸轻佻,并未应许,但唐突之举也仅止于登船时,趁机偷捏瑟瑟臀瓣一把,再也没有别的孟浪。
一路沿着水路往太湖方向前进,画舫小舟在运河中徐行或停泊。瑟瑟眼神迷离,分明头一次来到苏州近郊,但不知怎地对两岸临水黑瓦白墙飞檐悬挑的建筑总有些道不清的熟悉感。
子胥握着她的手,眼神淡定,显然已熟悉这些景致,只是瑟瑟的手掌心沁出细汗,他狐疑地侧头瞟了瑟瑟一眼,瞧见她眼神氤氲,迟疑一会,开口问道:「怎了?什么事惹你不快?」
他没问出口的那两字,其实是,伤感。
瑟瑟见着了什么,眼眸濡湿?
可是与他一样,头一次来到苏州时,内心震撼感伤,却不知所以然?
「…好像前辈子来过似的,很美。」瑟瑟握紧了子胥的手,眼神望向远光,轻缓地吐出了这句话。
子胥闻言一震。想开口问她何以如此说。
但前方忽有一艘小舟疾驶而来,魏军猝不及防,摇桨躲避,小舟左右摇晃,瑟瑟撞进了子胥的怀中,就这么倚着他没起身,子胥顺势将软香温玉搂在怀中,温热的暖香传来,内心安宁静谧,也没再细问。
进了城,他们又换了马车,抵达魏家府邸时已是万家灯火。两盏红灯笼以蟒纹铸铁钩挂在垂花门楼的雀替上,明瓦蓝墙,红门敞开,门侧候着总管领着一名嬷嬷与几名小厮丫头。
「少爷,您回来了。」总管远远便瞧见子胥与身旁水绿色旗装的姑娘,不知姑娘身分,但依旧迎了上来,恭谨地唤了声。
「嗯。」子胥歛眉肃穆吩咐:「让人将少奶奶的行李都搬进屋里。」
总管有些讶异地望了望瑟瑟,瑟瑟也是吃惊地瞟了子胥一眼,面色绯红转头向总管垂首点了点头。总管明知个性寡淡的大少爷未曾迎娶任何人,但瞧大少爷凝视着他的眼神透漏些许打探深意,眼色极佳的他,立即地唤道:「大少奶奶,长途跋涉辛苦了,已备妥洗尘宴,您且先休息用膳。」众人见总管表明立场,也纷纷殷勤地左叫右唤少奶奶。
子胥这才勾起一丝淡笑,似是满意众人表现,牵着瑟瑟的手,跨过垂花门楼,一路愉快。反倒是瑟瑟有些不自在,紧紧捉住他的手,终于进了魏家门。
待晚膳后,瑟瑟便让嬷嬷丫鬟们伺候着沐浴,洗去一身尘泥。
丫鬟婉婉见瑟瑟一身细碎瘀青,颈脖上还有些点状红斑,奇怪地问道:「少奶奶怎么伤的?细细密密,倒像是被什么大虫咬着?」
瑟瑟闻言羞红了脸,岂敢说是与子胥在马车的风流韵事,支支吾吾不知该如何回答。
另一个嫁做人妇的大丫鬟纹绣瞧这状况,立即明白发生何事,精明地支开了婉婉去取茶水让少奶奶润喉,待人走远了,才由博古架暗格抽出一个圆饼,以木柄掏挖出一团薄绿透亮的膏状物,微红着脸低声对瑟瑟说道:「少奶奶,这清凉膏可以缓解血瘀,包含下身那处不适。府里还有些活络血脉筋骨的膏药,适合在第二日清晨使用…我先帮您上药…不过,您别担心,这药,即使吃进肚子哩,也不打紧…」
这话虽说得正经,听在耳里却无限暧昧。子胥狂浪之举想来有心者,皆是人尽皆知,瑟瑟恨不得挖个地洞将自己埋进去,眸子垂得更低,仅能哑声回道:「甚好…」
纹绣与婉婉领着瑟瑟至东厢房,瑟瑟见状赶紧问道:「没有客房吗?」
纹绣笑了起来说道:「若让少奶奶待在客房,少爷不剥了我们的皮才怪?」
东厢房一向是长子所居之处,她没打算与子胥同房啊。子胥尚未迎娶她,却安排她住这处,不是违反了礼教?
但转头一想,人都让子胥吃干抹净了,要她不待在东厢房,她反倒伤心。她望着婉婉与纹绣一脸笑意,心虚脸热了。她这算是进门了吗?
掩上了门扉,她打量着房中事物。子胥的寝室简索雅致,仅有几幅不知出自哪家名家的泼墨山水,却让瑟瑟看傻了眼。
相较她的水墨画,这几幅泼墨山水笔韵悠远,丹青纯蓝带墨黑,挥洒处逍遥自在,气势磅礡,颇有胸怀天下之感。她的反倒小家子气,一点也施展不开。
几幅画看痴了她,傻傻地坐在圆椅凳上凝视着山水画,忘了身在何处。子胥房里点着桐油灯,里头不知添加了什么香料,清淡带着木香,舒缓心神,她眼中只有画,听着窗外虫唧蛙鸣,不一会便有了困意。
子胥检视苏州产业帐册后,回到东厢房,推开房门便见瑟瑟撑头打盹。他浅笑将瑟瑟抱上床榻,瑟瑟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亲暱地蹭了蹭他,呢喃道:「皇上,你回来啦?」
子胥闻言一愣,吃惊不已,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什么。
他望着呼吸平稳绵长显然已熟睡的瑟瑟,思绪纷乱。
末了,他收拢手臂,轻蹭着瑟瑟的鼻尖,低声回道:「嗯,朕回来了。」
回到你心里了。
***************
简体版
***************
接近苏州时已近傍晚,夕阳余晖洒落金黄璀璨,白墙如沙金,迷眩人眼。
子胥扶着瑟瑟下了马车,笑说:「瑟瑟,又要登船了。」
他的语调戏谑暧昧,瑟瑟闻言羞红了脸,直叫:「你答应过我的,不许胡来。」
子胥眼眸轻佻,并未应许,但唐突之举也仅止于登船时,趁机偷捏瑟瑟臀瓣一把,再也没有别的孟浪。
一路沿着水路往太湖方向前进,画舫小舟在运河中徐行或停泊。瑟瑟眼神迷离,分明头一次来到苏州近郊,但不知怎地对两岸临水黑瓦白墙飞檐悬挑的建筑总有些道不清的熟悉感。
子胥握着她的手,眼神淡定,显然已熟悉这些景致,只是瑟瑟的手掌心沁出细汗,他狐疑地侧头瞟了瑟瑟一眼,瞧见她眼神氤氲,迟疑一会,开口问道:「怎了?什幺事惹你不快?」
他没问出口的那两字,其实是,伤感。
瑟瑟见着了什幺,眼眸濡湿?
可是与他一样,头一次来到苏州时,内心震撼感伤,却不知所以然?
「…好像前辈子来过似的,很美。」瑟瑟握紧了子胥的手,眼神望向远光,轻缓地吐出了这句话。
子胥闻言一震。想开口问她何以如此说。
但前方忽有一艘小舟疾驶而来,魏军猝不及防,摇桨躲避,小舟左右摇晃,瑟瑟撞进了子胥的怀中,就这幺倚着他没起身,子胥顺势将软香温玉搂在怀中,温热的暖香传来,内心安宁静谧,也没再细问。
进了城,他们又换了马车,抵达魏家府邸时已是万家灯火。两盏红灯笼以蟒纹铸铁钩挂在垂花门楼的雀替上,明瓦蓝墙,红门敞开,门侧候着总管领着一名嬷嬷与几名小厮丫头。
「少爷,您回来了。」总管远远便瞧见子胥与身旁水绿色旗装的姑娘,不知姑娘身分,但依旧迎了上来,恭谨地唤了声。
「嗯。」子胥敛眉肃穆吩咐:「让人将少奶奶的行李都搬进屋里。」
总管有些讶异地望了望瑟瑟,瑟瑟也是吃惊地瞟了子胥一眼,面色绯红转头向总管垂首点了点头。总管明知个性寡淡的大少爷未曾迎娶任何人,但瞧大少爷凝视着他的眼神透漏些许打探深意,眼色极佳的他,立即地唤道:「大少奶奶,长途跋涉辛苦了,已备妥洗尘宴,您且先休息用膳。」众人见总管表明立场,也纷纷殷勤地左叫右唤少奶奶。
子胥这才勾起一丝淡笑,似是满意众人表现,牵着瑟瑟的手,跨过垂花门楼,一路愉快。反倒是瑟瑟有些不自在,紧紧捉住他的手,终于进了魏家门。
待晚膳后,瑟瑟便让嬷嬷丫鬟们伺候着沐浴,洗去一身尘泥。
丫鬟婉婉见瑟瑟一身细碎瘀青,颈脖上还有些点状红斑,奇怪地问道:「少奶奶怎幺伤的?细细密密,倒像是被什幺大虫咬着?」
瑟瑟闻言羞红了脸,岂敢说是与子胥在马车的风流韵事,支支吾吾不知该如何回答。
另一个嫁做人妇的大丫鬟纹绣瞧这状况,立即明白发生何事,精明地支开了婉婉去取茶水让少奶奶润喉,待人走远了,才由博古架暗格抽出一个圆饼,以木柄掏挖出一团薄绿透亮的膏状物,微红着脸低声对瑟瑟说道:「少奶奶,这清凉膏可以缓解血瘀,包含下身那处不适。府里还有些活络血脉筋骨的膏药,适合在第二日清晨使用…我先帮您上药…不过,您别担心,这药,即使吃进肚子哩,也不打紧…」
这话虽说得正经,听在耳里却无限暧昧。子胥狂浪之举想来有心者,皆是人尽皆知,瑟瑟恨不得挖个地洞将自己埋进去,眸子垂得更低,仅能哑声回道:「甚好…」
纹绣与婉婉领着瑟瑟至东厢房,瑟瑟见状赶紧问道:「没有客房吗?」
纹绣笑了起来说道:「若让少奶奶待在客房,少爷不剥了我们的皮才怪?」
东厢房一向是长子所居之处,她没打算与子胥同房啊。子胥尚未迎娶她,却安排她住这处,不是违反了礼教?
但转头一想,人都让子胥吃干抹净了,要她不待在东厢房,她反倒伤心。她望着婉婉与纹绣一脸笑意,心虚脸热了。她这算是进门了吗?
掩上了门扉,她打量着房中事物。子胥的寝室简索雅致,仅有几幅不知出自哪家名家的泼墨山水,却让瑟瑟看傻了眼。
相较她的水墨画,这几幅泼墨山水笔韵悠远,丹青纯蓝带墨黑,挥洒处逍遥自在,气势磅礡,颇有胸怀天下之感。她的反倒小家子气,一点也施展不开。
几幅画看痴了她,傻傻地坐在圆椅凳上凝视着山水画,忘了身在何处。子胥房里点着桐油灯,里头不知添加了什幺香料,清淡带着木香,舒缓心神,她眼中只有画,听着窗外虫唧蛙鸣,不一会便有了困意。
子胥检视苏州产业账册后,回到东厢房,推开房门便见瑟瑟撑头打盹。他浅笑将瑟瑟抱上床榻,瑟瑟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亲昵地蹭了蹭他,呢喃道:「皇上,你回来啦?」
子胥闻言一愣,吃惊不已,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什幺。
他望着呼吸平稳绵长显然已熟睡的瑟瑟,思绪纷乱。
末了,他收拢手臂,轻蹭着瑟瑟的鼻尖,低声回道:「嗯,朕回来了。」
回到你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