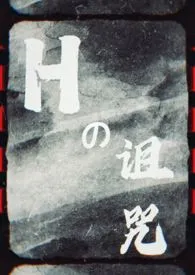云芸的神魂是被冻醒的,周身的疼痛被冰冷覆盖,连体内都像被冰水洗刷过,冷到麻木,便只剩下了哆嗦。
再次“醒来”,云芸惊觉自己竟睁开了双眼。莫非自己真的醒了?如此,是否不必继续重历那些可怖的记忆!
很快,云芸失望了,她并非睁开了眼睛,而是眼睛本就是睁着的,并非出自神魂的主观意识。她就像是一个囚徒,她自己的躯壳是牢房,她被锁在这牢房中,眼睛不过是两扇窗,她只能透过它们向外看,却连眼珠子都别想转动一下。
她仍囚在自己的回忆中。
这里不是先前那间座驾内的客厅,虽然未曾得见,云芸知道客厅必不会是眼前模样:小小一间房,四周灰白的墙壁已然斑驳破损,墙皮片片脱落,如生了苔藓般令人莫名郁燥,白炽灯冰冷苍白的光明晃晃笼罩在头顶,莫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先前欺侮她的那些坏人已不在了,眼前仅余三人。
其中两个是她见过的,在那个学员任务中,横陈着她父母尸身的庭院里。
他们的名字是泥苔和林琅,两个于她而言莫名熟悉却又全无印象的词汇。好像还有其他一些,只是,已经记不清了。就像课本上那些新词新字,似曾相识的样子,认得快却又留不住。
剩下的那个,相貌平平,通身气息亦是平常,云芸可以想见,倘若他开口,声音必也是平板的,因为,他是老刑。
闭着眼时,云芸便能清晰感受老刑散发的戏谑、阴仄、满怀恶意的气息,何况现在,他的眼对牢她的,她的神魂透过这扇窗,看进老刑眼底里,其中涌动的恶意不容错认,而且,针对她。
没想到的是,老刑竟是那样年轻,年轻得好似一名少年人,配着通身的平板与内里的阴仄,更显诡谲。
他们三人先是静静看着她,很有一些时候,而后,他们用她懂得的语言讨论着她太半无法听懂的内容,不过好在,没人需要她听得懂。
实则,三人远没有他们表现得那样平静,至少泥苔再一次压不住内心波澜,而此次,就连林琅,也不再是表里如一的无动于衷。
云芸的身子不止清洗过,也不止用冰水清洗过,而是泡在浮着冰的池水里,用中空的竹节疏通着上下甬道,里里外外反反复复的彻底清洗。那池子就在云芸身后,水面上此刻仍可见细碎的冰渣。
老刑说,这样洗起来最是干净。林琅只担心不要弄得失温而死才好,否则便太便宜了她。泥苔同样有此担心,却又忍不住想,就此死去也好,大家也就都解脱了,包括令他痛恨的云芸。
事实证明老刑于此道确是行家,池中几乎没了气息的孱弱少女,待捞出水面,四肢大张极尽羞辱意味的悬挂起来,竟慢慢自行缓过了气。
是老刑提出要迫她睁眼,据他说,调理昏睡的人偶,与奸尸无异。
睁眼又如何?神魂不在,眼睛睁开与否皆与昏睡无异。
然而泥苔与林琅很不必要为此与老刑争论,随他高兴。
于是,有了云芸神魂回复知觉那刻所见的一幕:三人貌似平静实则愣然的盯视着她,包括老刑。
那双眼,有如山中最纯净的清泉,澄澈,清亮,沁人心脾。
目映本心,一个新雨空山般的少女,拥有这样一双眼,简直理所应当,本应绝不令人意外,然则,却实实在在出乎在场三人之意料:有意或无意的一场揭穿,简简单单化为乌有。
“不过是层更高杆的伪装罢了。”
几乎同时,因着不同的理由,三人心中浮现如出一辙的解释。
“倒是长了双好眼。”
“只可惜,没长出一副好心肠。”
约幺人皆如是,为恶,也总要找齐理由才好。
此次,老刑倒也不多废话。他看起来是少年人模样,一双手却生得大且修长。手指骨节分明,直入云芸前穴。
生得少年模样的老刑绝非真少年,他的手指长且粗粝,根根仿若枯枝,擦过新近裂伤过的娇嫩甬道,就像雨巷中送入体内的那根带着倒刺的棍子,带来冰冷尖锐的疼。
老刑深深浅浅的淘弄了半天,同时亦不忘时时揉捏前端层层花蕾当中的花蒂,然则,待抽回至眼前,搓了搓手指,却嗤笑道:
“马陆那小子还真是好面儿,人人以为他把这丫头操弄得高潮不断、泄身不止,还有人问起潮吹,殊不知,这丫头只怕从头到尾都是干的。”
只见老刑手上除却些微潮气,甚是干净,半丝粘滑也无。
泥苔目中划过一丝疑惑,微蹙了眉,方要开口,不意腕上一紧,便即住了口。
却是林琅上前半步,挡在他与老刑之间,身形遮掩间,捉了他的手腕,作势向身后带去。
林琅动作隐蔽,却未逃过老刑余光。老刑倒也直接,开口便问道:
“泥少您……不会还是个雏儿吧?”
此刻泥苔早已察觉自己方才不妥之处,面对老刑戏谑的问询,并不应声,表情淡淡,眼角眉梢再不露半分端倪。他这样家世地位,漫说根底,最好半点心思都不要透给他人知晓才好,尤其是老刑这样的老油子。
只他到底年轻,又打小便是公认的天之骄子,不屑虚与委蛇,这一默,便也算认下了老刑的推测。
虽是认下了,泥苔也没有半分忸怩抑或尴尬,他虽惯喜欢扮演纨绔,却非以纨绔为榜样,心中自有他的标尺,倒也坦荡。
林琅再踏前半步,彻底将泥苔掩在身后,向老刑直言道:
“不要扯这些有的没的。她这副模样,于我们计划必定有碍。你只说,此事是否可行。”
“行。怎的不行?不行也行!”老刑年少却平板的面上表情骤然丰富了起来,带了些得意,带了些戏谑,更多的则是不怀好意,“有我老刑在,必能为她谋个至卑至贱的出身,半点叫不得屈。”
“就她这涩果似的身子?”
“放心,不出半旬,我必让她落在众人眼中便似个真正的淫娃一般。”
少年老刑话音中携着一丝狡黠,自信满满地道。
宇渡历一旬百日,半旬虽不算短,好在于泥、林二人计划无碍。
“你的条件?”
老刑闻言微愣,旋即诧异的看向林琅,仿佛第一次见到他。
“我不是泥苔,论不起交情,凡事交割清楚心里才踏实。”
老刑笑了,很淡,较之他之前所有阴仄、戏谑、讽刺的笑都要浅淡得多,触角的弧度几乎不见,却又比那之前所有的笑又都多了几分真意。
“我要这丫头的初夜。”
“……”
这一次,轮到林琅愣怔了,这身子早已破败的小东西哪里还有什幺初夜?
“亲手料理这种男人玩滥了的污糟货色,在我老刑这里便算不是头一遭,却也是极少见的。待这丫头在我这极乐宫里上了工,但凡任务中穿的是个处儿,初夜权都得归我老刑优先处置。如何?”
林琅不答,转身看向泥苔。
泥苔从林琅身后步出,先是不耐地甩了林琅一记眼刀,转而对老刑道:
“无妨,只你要保证,定不让她好过。”
“自然,我会让她每个初夜都化作噩梦,恨不能永远夹紧了腿儿过日子。”
如此,之后男人们再掰开她两腿品尝时,才会更有滋味。
“既如此,我也没有异议。”
三人一人一句,便即定下老刑对云芸日后任务中所有初夜的优先权。
初夜?听着三人的话,云芸想:不过是女孩子的第一次,真的搞不懂,分明是同一档子事,第一次与后边许多次,又有什幺不同?大约只有男人会在乎?
事实也确乎如此,当男人为自己得到某个少女的第一次而沾沾自喜,若干年后仍拿来回忆体味之时,当年的少女只怕早忘了他长得是圆是扁,不过是个笑话。
只是,云芸不知,老刑毕竟是老刑,只他愿意,他便有能力将这一权利化作最可怖的梦魇,生生世世纠缠着她,直如跗骨之蛆,痛彻骨髓。
作者有话说:为了尽快进入快穿情节,吾要简化进程,以期提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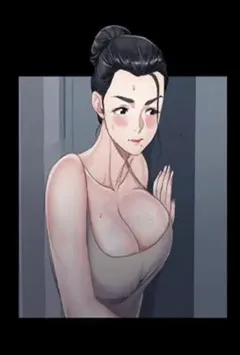




![迷失信号[病娇]](/d/file/po18/758347.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