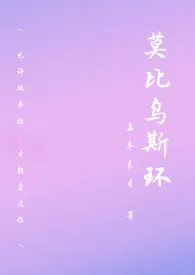阳光照在脸上,有些微微的痒意,至臻醒来,自己睡在兰芷院的床上,身边空无一人,恍惚以为昨天那场伤心事发生在梦里。
严嬷嬷与花容进来伺候梳洗,消失了月余的人熟练的在屋里忙忙碌碌,至臻有些疑惑,又暗嘲自己知道又如何,只安心受了,假装她们一直就在。
漱口洁面梳妆,严嬷嬷把剃刀拿进来,至臻愣了一下就从善如流地躺在塌上,任由花容分开自己双腿,严嬷嬷在腿间动作着。
虽然已经好多回了,至臻仍然有些紧张,紧咬着下唇偏着头不敢看,之前没除尽毛根,那处不到一旬就茂盛起来,留下这许多麻烦事。
至臻得知月河半夜就起程去军营了,心里竟不似昨天那样难受了。
外面有丫头回话说老爷下朝了,请二奶奶过去用早膳。
府里虽然没有正经婆婆,至臻也偷不得懒,只要苏纲在府里,两人一日三餐都是要一起用的,大伯苏堰偶尔过公主府小住,大部分时间只是在自己院子里读书作画,至臻进府至今都未曾见过。
下人呈上饭食就被遣下去,苏纲把至臻抱在腿上用饭,先是把鱼刺挑出来喂到小美人嘴里,看至臻慢慢嚼着竟还用嘴去抢,吃个早饭都能把至臻弄地气喘吁吁,淫水涟涟。至臻吃饱后就解了衣衫让苏纲吸奶,被嘬到动情苏纲就用手给她纾解,即使自己腿间都已直起帐篷,也不曾真的插弄至臻,想还是避讳着苏玉河的。
用完早膳,苏纲拿了软帕给至臻擦洗身子,先是细细抹干净胸前的乳汁,来到腿间发现耻毛被剃了个精光,阴核水嫩嫩的俏立着。
至臻有些羞怯:“严嬷嬷……啊……”,那处被唇舌亲吻,至臻娇吟了一声。
苏纲擡起头,在至臻耳边说:“很漂亮,我很喜欢。”
至臻看着苏纲带笑的眉眼,鼓足勇气说:“我想看看孩子……”
苏堰在二弟的新婚之夜被塞了个孩子,震惊之外对这新妇就存了一丝轻视。后来听公主说起“娇娇”这个昏名儿的来历,更是对至臻厌弃至极,原先只以为二弟孟浪,现在看来倒是二弟着了这淫妇的道儿。所以月余来才对至臻不闻不问,若不是今日苏纲领着,至臻怕是连凉风院的门都进不了。
苏堰躬身向父亲行礼,他自幼聪明勤奋,不需苏纲费心教导,父子俩竟有些疏离。
苏纲让出半边身子,苏堰才看见后面还缀着一个妇人,穿着轻薄的秋装,绾了简单的发髻,行动间袅袅婷婷,眉梢眼角俱是风情,她上前一步,娇声问安,之后怯怯地看了他一眼。
这一眼竟把苏堰看醉了。
他轻咳一声,回了句“弟妹安好”,遣下人领着她去侧院看孩子。
苏纲被苏堰引进书房,一时无话索性对弈一局。
苏纲棋艺精湛,陪先帝下棋仅输一子,苏堰自愧不是对手。
不一会儿,侧院传来孩子响亮的哭声,苏纲一个错子丢了一大片“江山”。
“父亲心系小辈,怕是要输。”苏堰及时给父亲找了个台阶。
孩子一直在哭,不一会儿,那妇人出了侧院,用手绢掩着小脸跑走了。
苏堰觉得父亲的棋风愈显凌厉,之后竟“自断一臂”草草结束了棋局。
苏纲回到忠勇堂,发现至臻正倚在塌上等他,眼角红红的,一看就哭过。
苏纲挤上塌,让至臻靠在自己怀里逗她:“小哭猫,一天哭三回。”
至臻情绪有些沉郁,“孩子起名字了吗?”
苏纲说昌平公主赐名“乐瑶”。
至臻委屈的小声说:“乐瑶都不吃我的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