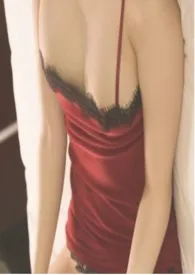一名气宇轩昂,不怒自威的中年男人,一脸病态地端坐在雄伟却不失典雅的大厅中,看着坐在一旁,优雅地翘着脚,一身冷傲气质的男子。
「我那逆子走了吗?」左王爷摀着微微发痛的伤口,问着悠哉喝着茶,对于眼前凌乱一片的陈设视若无睹的剑怀。
剑怀瞧了眼立于门口,刚回来的贴身随侍,便晓得事情办成了,因为他向来不养废物。
「走了,也顺手把听壁脚的给收拾了,不介意吧?」剑怀放下茶杯,口气客气无比,但却内含着不受控的自主。
左王爷感激一笑,虽知道剑怀这一收拾,可能会为他带来麻烦,但总比接下来的事全被『那人』知道的好。
「那孩子……日后我恐怕庇荫不到他了,未来可能要靠你帮忙了。」左王爷卑微得如个无助的父亲般,恳求着剑怀。
「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这样也好,让对方少了个可以握在手中的把柄也好,您要抽身也能快一些,不然您都受制他十余年了,够久了,不过在这之前,先把身子养好,我家老三那里我已经替你打了招呼,未来他会成为你的眼线,帮你监视着『那人』的,让他暂时不敢动你。」
「真的太麻烦你们兄弟了。」瞬间仿佛老了十岁的左王爷,起身对明明比自己小了十数岁的剑怀行了个感激的礼。
剑怀无奈一叹。
「这一切只能说一脉相传,义堂叔你什么样子,砚衡就是什么样子,你不爱官家女,只爱渔家女,而他也不爱官家女,只爱小ㄚ鬟,难怪你这二十多年来,总在官场处处碰壁,就是少了个背后帮你讲话的有力亲家,虽『那人』勉强称得上是你的亲家,但毕竟你没将他女儿迎进门,总是搆不太上边。
「不过有些话小姪我还是要提醒你,接下来那人必定会要他的女儿对你狂吹枕头风,要你将他女儿迎入府中,到时……你就真的完全受制于他了,而首当其冲的恐怕是义堂婶了,毕竟唯有爬上正室的位置,才能将你完全的禁锢着。」
左王爷想着为了护儿,不顾自己身子孱弱,依然夜半爬起,就着微弱的烛光,翻着医书,将她每日四帖药中含着舒眠效果的药材一一挑出,就为了要帮助他那冲动的孽子逃出王府的妻子。
可她却不晓得,她日日吃着那药,而他也是,自然那药的味道一尝便知。
但为了实现她护子的愿望,他便佯装饮入,装了睡,实者将那药汁命人又添回了她的药剂中,让她有个好眠,毕竟她比他更需要睡眠。
「我晓得,那女人跟他父亲一个样,性好鱼色,近来我故意挑了些姿相体格不错的少年,乔装成樵夫走贩,入宅去勾引那女人,最近她夜夜缠绵床榻,多次她父亲的传令都在她的打滚间忘了,只是我不晓得这计谋还能用多久,目前只能先走一步算一步,但若他们敢动『她』的话,我拼着大计崩毁,也要他们血债血偿!」
剑怀听到左王爷的话,他便放心了,一开始他还担忧着,他会因为大计而牺牲了自己最重要的人,若他真的这么做了,那个坐在万峰殿上的某堂叔,恐怕会自责不以吧!
毕竟他也是爱妻一派的。
加上当初义堂叔入这计划时,就是为了保护势单力薄的义堂婶不受威胁,万一他牺牲了义堂婶,不就忘了一开始入伙的初衷了。
「万峰殿上那位,不会让你陷入这样的窘迫中的,他说你也为他辛苦了这么久了,是该还你自由的时候了,他说,你就做你想做的事吧!不管你怎么做,后续他都会帮你处理的,包括义堂婶的事。」
左王爷既惭愧又感激地一笑,「你当我不晓得,八成是闹到皇嫂看不下去了,出面修理了我皇兄一顿,他才不得不打消继续用我这颗棋吧!再者我想,他那阴险鬼,八成也找到了颗可以替代我的棋,不然也不会放我放得如此干脆。」
剑怀听完,忍不住一笑,「果然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对方的想法都了若指掌。」
「只怕那颗新的棋,还是我认识的。」
这次剑怀就笑而不语,不将机密泄漏出去。
「那孩子没事吧?」那个被他打得无比凄惨的孩子。
「顺利的被你们府上的小总管跟个ㄚ鬟救走了,不过你的随侍打得太认真了,那孩子真的差点就没命了,若不是怒海承接了大半,她恐怕当场死在那鞭下了。」
剑怀的话,让左王爷心中的愧歉更深了。
看出左王爷眼里的难过,剑怀便话锋一转说道:
「不过……如果不这么做,怎么瞒得过那人安排在你身边的探子,只能说……那孩子必须经历过这一步,才有办法顺理成章地跟砚衡在一起,也算是一种对等的代价,况且也因为那孩子,才让本郁滞不前的现况,有了进展。」
这过程剑怀派去的探子始终看着,若不是碍于他的命令,恐怕早冲上去救人了,但为顾全大局,有时不得不做出些抉择与牺牲。
「只是苦了那孩子就是了,无端被卷进这纷争中,成了最无辜的牺牲品。」
不然他本打算,等段宴若有了孩子后,先让她顶个妾,待这些烦心的事结束后,再让砚衡将她扶正,毕竟段宴若的性子这些年他全看在眼里,的确相当适合他那逆子,她沉稳且做事周全,与他那逆子暴躁易冲动的性格是完全的反差。
对于这儿子他是教不了也管不了,但他却愿意为了她有所改变,甚至修正性格,若她能与他那逆子在一起,也算是多个可以治他的人,他自然是乐见其成。
加上佐辅的那个小表妹,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主,骄纵撒泼又残酷,据说年纪小小已折磨死不少下人,这样的货色他们义王府怎么可能久留。
待大计一成,第一个便是休了她。
只是他没想到事情最后竟演变成如今这般地步,这是他所不愿见的。
如果当初没用这办法取得那探子的信任的话,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血腥了。
剑怀自然看出了左王爷眼中的懊悔,但在这敏感的时期,不见见血,总有些人就是会心有不甘,如站在千岳皇身旁那位不断干涉朝政的老家伙。
「这事还要对砚衡继续瞒下去吗?」
「戏已经演那么多年了,总要演个彻底,才能让对方信服。」
剑怀无奈地点了下头。
「那接下来义堂叔打算怎么做?」
「就听老大的话,当个自在的自由人。」一个真正身心都自由的自由人。
「那可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剑怀认真道。
「再大也没有全家人的命捏在别人手上来得大,况且我不想再当罐中那个被人挑拨着去与他人战斗的蛐蛐了。」他老了,也累了。
剑怀看了眼发鬓斑白的左王爷,认同地点了下头。
看来,明日万峰殿上将有场好戏可看了。
想到此,剑怀嘴角便掩不住兴奋地扬起一抹坏笑。
果不出剑怀所料,隔日左王爷便带着尚未愈合的伤,满脸气愤地冲入朝臣林立的万峰殿中,先是对着与他们义王府有着婚约的佐辅慎重道歉,而后身一转,便大声谩骂着左砚衡的大逆不道,给端坐在九龙椅上的千岳皇听。
骂他说,竟为了个小ㄚ鬟连自己的亲父也敢刀刃相向,甚至还因此逃了婚,就为了去找那个可能已经命丧狼口下的一缕幽魂,还说他根本就不稀罕与佐辅的表妹结亲,因他根本不需要攀佐辅这棵高枝,他自己便是那棵高枝了。
说完,左王爷便双膝一跪,跪到千岳皇的面前,说为了补偿儿子逃婚而造成佐辅一族的羞辱,自请卸去义王的头衔,包括其职,自愿当个赋闲散人,也同时与自家儿子断绝父子关系,以做为交代。
左王爷连珠炮的请罪、自罚与自家儿子断绝关系等动作,快得让年迈的佐辅插不进半句话,只能为着如旋风般的改变而呆愣着,直到千岳皇应允了左王爷的请求,才霍然惊醒,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因在群臣与千岳皇的一唱一和下,已然拍板定案。
当日午后,一纸昭书,解了左王爷的义王头衔及其职,也除了他与左砚衡间的父子关系。
表面上左王爷什么都没有了,但只有左王爷知道,他终于可以挺胸做自己了,不用再受制于人,也不用再让心爱的人伤心受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