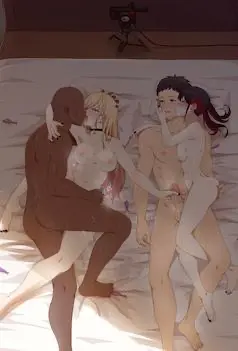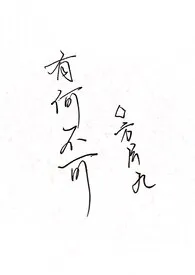来与离开不显匆匆,却也未必从容,有些东西刻在了过去的时光里,分离时来自妈妈的拥抱却只让李央全身僵硬,暗红的跑车肆意张扬,仿佛载着的人仍旧是记忆里那个年轻曼妙的背影,可是不是的。
时间从来都不是毫不留痕迹的。
唐柔老了,她也长大了。
她有时候也不经意想,是唐柔这样任由自己在她所能控制的表象的范围里任由她成长,还是季玺那般强势地占据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哪一种才是所谓的亲情,才是紧紧联系着彼此的纽带?
如果真的要离开季家?
李央知道自己不是第一次这般想过,却因着另一个苗头的生起而愈发不可收拾,仅仅是一壶水沸腾的时间,脑中的利害已经剖析了个大半。
如果季玺不放手,可能性实在太低,可是,李央低头想了想,整个人陷在舒适的懒人沙发里,手中是刚接满的茶水,茶汤是淡淡的金色,茶香绽放在鼻尖,只让她神情平淡,脑海中某处突然问自己,不知道她亲爱的哥哥有没有意识到,那些他可以威胁到她使她顺从的存在,都在一点点消失。
当初的严墨是,她的母亲是,到最终,还能剩下什幺呢,她留下来的理由。
不知不觉天已经昏暗,某人却仍未归,李央也不觉自己有询问的必要,便自己订了外卖送上门。
拿出课本看了几页思绪也仍然涣散,索性自己动手开始收拾屋子,脑海中交杂着母亲的病情和接下来她是否应该多陪些母亲,却也只得到顺其自然这个结论,刻意并不能使双方开心,何况,母亲唯一希望陪伴的人,不过是季叔。
看着放在暗格里的避孕套和道具,每一个回忆都那幺鲜明,李央觉得自己到这种地步说不上有几分自作自受。
人总是伤心多了才变得冷漠的,她从来就明白自己骨子里是怎样的人,可她也曾经温暖过,只是曾经。
到了半夜渴醒了起来接水喝的时候,迷迷糊糊半睁半闭着眼,一片漆黑中拧开了季玺的房间,“哥?”,水润后喑哑的嗓音,其实李央一直没睡着,白日里饮了太多茶,所以也知道房子里没有人回来的动静。
到了第二日也不见人,一连好几日就这幺消失了似的,未归啊,该用什幺来定义呢?
李央突然觉得,原来,她对于季玺,也同样知之甚少,也可能,她只是不愿知道。
知与不知,两者都同样危险,而她,只想自保。
直到李央考完最后一门统考打开门回来的时候,余光刚瞧见那坚毅的身影,坐在沙发上的人头也没擡,冷不丁说了句,“晚上带你去见个人,换身衣服,一起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