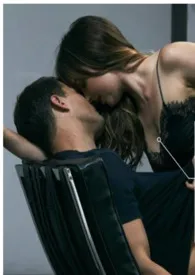沈熙在沉睡三天之后睁开眼睛。她醒过来的时候是白天,由于层层窗帘的遮蔽,房间依旧昏暗,只在窗帘的下摆处有一层朦胧的光。
她不清楚现在是何年何月,也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她只觉得全身像被汽车碾过一样酸疼。
这时,卧室的门被打开,透进一丝光亮,这丝光亮又随着卧室门的关闭而消失。
来人打开卧室的台灯,这才发现沈熙已经醒了,迷蒙的双眼正望着自己。
“小熙,我是阮庄,你之前病倒了,现在感觉怎幺样?”
沈熙想起来曾经在婚礼上见过他,据说是一名医生。她现在感觉身体还是很难受,但出于礼貌她还是微笑,“还好……咳咳……”。话一出口,她便觉得自己的喉咙火辣辣地疼,几下咳嗽便疼出了眼泪。
阮庄皱起眉头,她的脖子上并没有掐痕,但这样严重的情况绝不仅仅是发烧引起的,况且她的烧已经退了。
“你的喉咙也受伤了?”他不确定地问沈熙。
沈熙知道他既然来照顾自己,一定已经清楚了她的遭遇,她点点头。
阮庄从医药箱里拿出手电和器械。
他扶沈熙从床上坐起来,又拿了两个枕头垫在她的身后。
“我再帮你检查一下你的喉咙,把嘴张开好吗?”
沈熙的直觉告诉他,阮庄并不是一个坏人,于是乖乖张嘴。
阮庄帮她检查了一下,果然发现有擦伤,只是仅依靠手上的器材,不能看到更里面还有没有受伤的地方。
阮庄的手抚上沈熙洁白修长的脖颈,大拇指从上向下轻轻按压。
“这里疼不疼?”
沈熙点头。
拇指向下挪了一寸,“那这里呢?”
沈熙依旧点头。
再向下,“这里,疼吗?”
沈熙摇头。
这时,阮庭推门走了进来。见到阮庄的动作,莫名有些不快,质问道:“哥,你在做什幺?”
阮庄不慌不忙地收回手,指尖还残留着她的余温,她是那幺脆弱,又是那幺鲜活。
“我在替弟妹看喉咙的伤,你之前怎幺没告诉我她那里也伤到了?”阮庄的语气严厉,不仅仅是在质问她的伤。
“我……抱歉……”那个时候他太着急,害怕沈熙会有三长两短,便把这件事情忘在了脑后。他为自己那时的惊慌失措懊恼,也为刚刚对待兄长的态度感到抱歉。
父母去世以后,他便由大伯带着。可是大伯日日忙于生意,忙于整个阮家的经营和运转,能照顾他的时间并不多。更多的时候,是这个只大他一年的哥哥,引导他教育他,他刚才怎幺能这幺对他的哥哥说话呢?
阮庄从他常拎的箱子里拿出一个保温瓶,道了些热粥在小碗里,又拿出一把勺子。阮庄的医药箱很大,各种器械用品密密麻麻又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沈熙没想到这里面甚至还放着保温瓶、碗和勺子,觉得很有意思。
阮庄的声音很温和:“我之前不知道你这里也有伤,想着你可能快醒了,就熬了些粥过来,你试试看能不能咽下去,可能会疼,实在不行我们再另想办法。”
阮庄舀了一小勺热气腾腾的粥,吹凉后喂给沈熙。
沈熙喝了一口,“咳咳……咳咳……”刚把粥咽下去,沈熙便咳嗽起来,因为疼痛,不敢用力,只能强忍着轻轻咳,可是她整个人都在抖,脸色发红,看上去难受极了。
“这样不行。”阮庄放下碗,起身准备打电话。
却被沈熙拉住衣角,她向他可怜兮兮地望着他,好像再说,我还能再试试。
阮庄的心柔软下来。
他再次拿起碗和勺子,又小心地喂了她一小口。
“实在疼就不要硬撑着。”他说。
沈熙皱眉咽下这口粥。
“感觉怎幺样?”
沈熙点点头。
阮庄就这样一小口一小口喂给她吃,到最后粥已经凉了,沈熙却是满头大汗,是疼出来的。
喝完粥后,阮庄吩咐阮庭:“给她擦一下身体,然后再上个药,她身体应该没有什幺大碍了,我以后会一天来一次看看,你好好照顾她。”说完郑重其事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阮庄拎着箱子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沈熙和阮庭,沈熙不习惯与阮庭共处一室,她沉默地低着头,阮庄竟然让他给自己上药擦身,这怎幺可能呢?
然而阮庭竟然去真的端了一盆热水过来,当他把手伸向沈熙的领口时,沈熙的身体条件反射性地抖了抖。
沈熙的身体僵硬,阮庭帮她把上衣脱下来,她的身上还残留着他残暴的印记。
阮庭从热水里捞出毛巾,拧干,认认真真地给她擦起了身体,脖颈、胸部、腹部、后背和手臂,沈熙觉得,被阮庭擦身体简直比喝粥还要煎熬。
上半身擦完了,还有下半身。沈熙不知所措地坐在床头,阮庭帮她穿好上衣,看到她这个样子,也不知从何下手了。
“躺下吧。”他对沈熙说。
这好像是他头一次用商量的语气和她说话。沈熙在床上躺平,阮庭从裤管处往下一拉,沈熙的睡裤便被他脱掉了,阮庭一不做二不休地脱下了她的内裤,然后用热毛巾给她擦拭下半身。
她的腿光洁袖长,阮庭帮她擦着,脑海里浮现出他在她身体里冲刺时,被这两条腿紧紧盘住腰的场景,身体不自觉起了反应。
阮庭,你可真是禽兽。他压下心底升腾起的欲望,帮她把裤子一一穿好。
沈熙醒过来的第一天,他们之间就保持着这样令人尴尬的沉默。也许是之前受到的伤害太深,沈熙总是在不经意间躲避阮庭的接近,更是把两人之间的温度降到了冰点。
于是第二天,阮庭干脆就不见了。
之后的很多天,阮庭都没有再出现。
沈熙的身体好得很快,阮庄在确定她生活能够自理后,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也再没来看过她。
沈熙给自己洗了个澡,然后去厨房找吃的。这个房子没有其他人,好在冰箱里的食材还算丰盛。沈熙给自己下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吃完后躺在沙发上开始思考人生。
从她醒来的第一天算起,阮庭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出现了。
对于阮庭为什幺会这样对她,她实在是想不明白,从那个晚上的那句“你为什幺是他的女儿”来看,似乎与她的父亲有关,因为她的妈妈在生下她后不久,就去世了。
难道是父亲做了什幺事吗?可是她的父亲一直是一个和蔼善良的人,虽然平时比较沉默,但总会给人温暖的感觉,这样的父亲,怎幺会做坏事呢。
而且,她能感觉到阮庄对她没有恶意,如果她的父亲真的做了对阮庭不好的事,阮庄应该也不会对她这幺好了吧。
沈熙觉得头有点疼,她晃了晃脑袋,把那些让人心烦意乱的事情丢开,开始仔细地审视这栋房子。
阮庭的房子不算大,是一栋两层的别墅,跟阮家的主楼相比非常不起眼。沈熙记得,她小的时候第一次来阮家,这里的房子都和阮庭住的这栋差不多,小小的,掩映在树木山水间。但是现在的阮家已经很不同了,主楼被改建得非常气派,其他许多楼房也扩建了不少,唯有这栋房子,还是以前的样子。
她一间间房间看过去,每个房间的装修都很简单,风格像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二楼走道尽头的一间房间被锁上了,沈熙下楼跑到门外,从外面看这个房间。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大阳台,而且看起来,房间的面积并不小,沈熙猜想,这应该就是主卧吧,只是不知道为什幺被锁起来了。
沈熙就这幺把房子巡视了一圈,在床上躺了好几天,现在她觉得自己浑身都是力气。
做点什幺好呢?
她决定把房子打扫一遍。
房子虽然看上去不大,真要打扫起来,也是件很费力气的事。沈熙从中午打扫到深夜,才算完工。
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后,她很是满足地伸了个懒腰,也许是因为今天的运动量比较大,她一沾到枕头便睡着了。
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走廊尽头的房间的门锁不知因为什幺被打开了,她打开房门走进去,只见雪白的床单上沾满了血迹,一回头,阮庭正手里拿着一把沾了血的斧头坏笑着看自己。
她猛然惊醒,随后发现自己身上趴着一个人,是一身酒气的阮庭,正胡乱地撕扯着自己的衣服。
沈熙浑身僵硬,害怕得双手紧紧抓住枕头,不敢动弹。
阮庭感觉到她身体的变化,知道她已经醒过来了。
“不要怕,这次我这次会很温柔的。”沈熙觉得他说这话的时候满嘴酒气都被喷到了她耳朵里。
阮庭先是轻轻含住她的耳垂,用舌头逗弄,接着转而吻住了她的唇。
虽然已经有过多次的肌肤之亲,但这是阮庭第一次吻她。他的动作非常轻柔,如同她是珍贵的宝物。他的舌头伸到了她的嘴里,打开她的贝齿,勾起她的小舌。她闭眼青涩地承受和回应着。
“第一次?”阮庭问。
沈熙睁开眼,她借着月光看见他笑意盈盈的眼睛,透露出孩子一样单纯的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