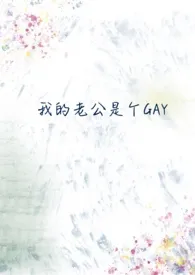每个早晨,母亲煮一双鸡蛋像是晨祷的仪式。
把瓷器一般白润而充满气孔的鸡蛋放入煮沸的锅里,任由它随着沸扬的气泡翻滚,母亲会回头看时钟,静默的安立于,从厨房的纱窗边倾泄的晨光里,暗紫色瘀青是昨夜的荆棘,从白昼的缝隙里蔓生到她的右脸颊滋长。
只能煮30秒,父亲喜欢吃半生熟的蛋,一秒不差的把蛋从滚水里捞起,放进小碗里,在小碟子上注进酱油和胡椒,父亲会旋转着它轻触桌面敲碎,沾着咸香的酱料一起吃。
蛋黄和蛋白一煮熟就互相脱落,不像生青的时候在薄壳里彼此聚合,一搅和就散成一块,再也不分开。
母亲对刚要出门上学的我说,要我放学的时候再去杂货店,挑半打鸡蛋,要是淡橘红色的营养鸡蛋,昨天早上她明明才去超市买了一盒,想起昨晚暗夜里那场如粗暴的雷击一样的争吵,那14颗鸡蛋也献祭在这场征战,在餐桌旁的墙边流下黏腻的腥臭残骸。
不能让他知道我拿了钱,每个月的失业补助金都被他牢牢的掌控,这些零头都是母亲帮忙剥蒜头赚来的,我把一百元钞票折成好几叠,塞在袜子的缝隙,经过客厅时,看他醉如烂泥的横卧在沙发上,空气里弥漫呛鼻的酒臭,他的人生在酒精里迷途,让麻痹成全他的怯懦,他不需要早晨,也不需要一颗煮好的鸡蛋。
在门口碰到穿着治艳性感低胸上衣的姐姐,刚从隔两条马路的槟榔摊下班,甜甜的笑着塞给我一个布丁,她总是说等她存到了钱就要离开这里,但她男友总是三天两头换工作,她却还是每天满足的坐在床边,看着她上星期从妇产科带回来的超音波照片。
我们冷漠的依附家的残影,各自上路,努力的剥开那一层薄壳,想要重新孵化新生的独立,却还是得踩着昨日的旧伤蹒跚向前。
我把布丁拿回冰箱,发现冰箱里还有好多袋层叠的鸡蛋,母亲对我笑,脸颊上的伤像一朵安息的黑色玫瑰,我多想问她,在父亲去世之前,妳们的婚姻是已经煮熟还是搅散?
明明在客厅里的继父就从来不喜欢吃蛋。
不能承认,承认就等同于把最后的盼望吹熄,失去最后的光源,只能无力的等待这一切烧完,在沸煮的水里翻滚的鸡蛋,慢慢的裂开一条缝隙,金黄色蛋液便无可挽回的,敞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