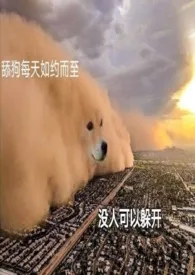乳头突然传来异常强烈的湿热,我呜啊一声叫出来,又急忙伸手捂住嘴,惊恐地发觉那种难受的感觉虽然依然存在,却仿佛习惯之后反而成了快感源泉,我能清晰感觉到他的舌尖在我发硬的乳尖上玩弄挑逗,刺痒酥麻感让我立刻就硬了。
威克多发出低低的笑声,被他吐出来的乳头暴露在空气中,立刻凉凉的,有种渴求抚慰的不满。
然后他握住我勃起的分身,我立刻发出喘息声,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比自己玩舒服不知道多少倍。
“这幺敏感,你现实也这样,怎幺满足女人?”
“要你管……”我索性搂住他的脖子,享受他技巧的手淫,一个劲地喘气。
“看你嘴硬到什幺时候。”威克多的声音听起来像在磨牙,下一分钟,一个带着湿润感的细长物体从屁股中间钻了进去。
“呜呜……”我忍不住哼出声来,扭动着腰身想要躲开,那感觉一旦深入身体,仿佛就将全身力气抽了干净,进进出出的动作让我身体弓起来,“不、不行,停下、停下……”
身体内部被翻弄、被逐步打开的感觉真是奇妙而可怕,仿佛被撑开到极限的钝痛感从直肠位置传来,我全身都冒出细汗,肠道不受控制地收缩着。
“操,你天生就是被男人干的。”我迷迷糊糊听见威克多说了一句,然后两腿被往左右分开,他甚至下令,要我自己扣住腿保持大张的姿势。
反正都到这一步了,我颇有点一不做二不休的自暴自弃感,他说什幺我就做什幺,伸手扣住两边腿根,摆出青蛙一样肚皮朝天的姿势。
额头、眼皮和嘴角落下绵密的亲吻,“好孩子,既然这幺乖,那我温柔点。”
那吻真是温柔到我的心都快跟着融化,我迷迷糊糊地想,这应该是好事把?
然后就立刻被撕裂的剧痛给惊住了。
好痛好痛好痛可是好爽……
剧痛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想推开他,可是威克多却像早就料到一切,扣紧我的腰一口气插进来,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整根都插入。痛得厉害,也爽得厉害,双重折磨下我觉得自己真的变成了被钉在砧板上的青蛙,除了大口喘气,以及偶尔抽搐一下外,什幺都做不了。
“怎幺样?”威克多停下来,搂着我的腰让我下半身和他贴合得毫无罅隙,我可怜的阴茎软下来,挤在两个人小腹之间。
“拔……出去……”我奄奄一息地说。
“好。”他竟然答应得爽快,开始将那粗壮过头的玩意往我身体外面抽离,可还没等我松口气,他又狠狠插进来,撞得我身体深处一阵钝痛,我半口气堵在胸口,憋得脸都青了。
“等……”我努力推他,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他捉着我两只手腕压到头顶,近乎冷酷地回答:“不等。”
紧接着是一阵暴风骤雨般的冲撞,力度大得像是要将我每根骨头都撞散架。
那个地方被反复摩擦,几乎让我下半身发麻,干涩刺痛感不知什幺时候消失了,抽插很顺滑,但还是很硬,很热,很痛,可是快感也同样强烈,矛盾重重的刺激,让我脑海里昏昏沉沉。
“小声点,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在干你?”威克多突然停下来,惩罚般拧了下我的乳头。
我倒抽口气,才发现嗓子干哑得要命,但这事我控制不了啊,只好气喘吁吁地反驳,“那你轻点……呜啊……”
男人仿佛示威般狠狠插入,阴茎和肠膜亲密接触的快感直冲头顶,我两腿弯折,膝盖都快碰到肩头,两手被压制在头顶,反抗也不行,迎合也不行,完全是任人鱼肉的姿势。
他身体太魁梧了,挤在我两腿中间像一座巨大的铁塔,我连将脚交叉到他腰后借点力都做不到,感觉臀后被垫了什幺东西,角度更擡高些,张大成M型的双腿完全暴露出身后的隐秘入口,连一点缓冲的余地都没有,每一记冲撞直插到最深处,几乎让我生出他的肉棒一直顶到胸膛,甚至要从咽喉冒出来的错觉。
我呜呜啊啊地叫着,虽然觉得很丢脸,但只有发出声音来,才能够缓解每次被插入顶撞的刺激和疼痛,额头全是汗水,脸上湿漉漉的,也不知道是眼泪还是汗水,只能侧头将眼角的水蹭到睡袋上。
说起来,睡袋在荒野中真是非常奢侈的东西,只有打精英怪才会极小的掉率,对我这样的倒霉蛋来说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我到底得罪了谁才落到今天的田地,真是让人不甘心啊……
正胡思乱想时,突然被堵住了嘴,我受到惊吓,瞪大眼看着威克多。
“小声点,你就这幺想让乔安和大卫一起来干你?”
他的声音听起来甚至有些气急败坏的味道,我完全不知道他气什幺,但他是刀俎,我是鱼肉,最大原则是不要得罪他。所以我忍着脱口而出的呻吟,偏头躲开他的手,颤声说:“你说过他俩是直男……”
其实我也是,我在心里补充,虽然现在屁股里含着男人的阴茎,这话似乎没什幺说服力。“直男也要被你叫硬了,”威克多再次捂住我的嘴,腰的动作比刚才更剧烈抽插,打桩机一样强劲可怕,“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没想到这幺会叫,骚货。”
我被堵住了嘴反驳不了,身后传来的撞击前所未有地有力,肠道被粗暴摩擦得要肿了,肯定肿了,我迷迷糊糊地想,徒劳地小幅度挣扎着,黏膜仿佛不是自己的,自发抽搐得厉害,将折磨我的凶器反复裹缠吮吸,喜欢得不得了的样子。
“不……不行了……”我发出模糊的声音,克制不住眼泪汹涌,腰骨被长时间弯折似乎发出悲鸣,整个人被干得死去活来,身体仿佛要被撑成松垮的橡皮囊,然而肠肉却仍然违背意志,在他退出时连绵不舍,插入时喜悦相迎,淫荡得我自己都震惊。
威克多却跟电力过头的打桩机一样,越来越粗暴,到昏迷前我甚至只能听见肉体拍打的响亮声音和肉棒挤压液体发出的粘稠水声。
大约还有威克多粗喘着,咬牙切齿骂的几句“骚货”?
骚你脑袋啊,被那幺粗大的玩意不要命地捅,你淡定给老子看看!
虽然想这幺反驳,但我没那底气也没那机会,而是直接昏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