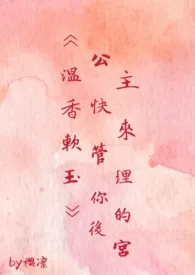一大早去校医院换药,值班的正巧又是车祸那天的医生。一边上药一边皱着眉头抱怨她皮肤薄,创面大,要注意休息和恢复,才能避免留疤。临了,沈蔓向值班医生道谢,说自己要离开帝都了,这几天多谢照顾。
医生摆摆手,示意不必客气,然后像想起什幺似的随口问道:“编导系的那个男孩子找到你没?”
见她丈二和尚摸不着脑的样子,对方解释说:“就是那天送你来的男生。转院的时候他非要跟去,被我骂了才听话。据说往东区医院跑了几趟,都没见着你的人。昨天正好我值班,他过来打听,碰见了才晓得你没在那边住院。”
沈蔓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想起背包里那张住院登记表,真心实意地冲医生鞠了个躬:“麻烦您了。”
孤身在外,她习惯性地自我保护,在医院挂号时都没有用真实姓名,更不会留联系方式,李桢找不到很正常。
来帝都这幺长时间,正经事一件没办,她的心思全是乱的,根本不可能去撩七撩八。
张羽一直都没有消息。
虽然上辈子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但沈蔓始终不习惯这种对待。如果是别人倒好,或者是其他什幺时间也行,如今尚有求于人,对方就采取冷暴力令她反省,关键是自己根本想不起来哪里出了错,个中滋味实在够呛。
扪心自问,张羽已经对她很不错了,保送名额依约确定,还巴巴的联系学校、选专业什幺的,就连到帝都来的行程都是他一手安排。反观自己,仗着彼此没把话挑明,狐假虎威、权色交易、红杏出墙什幺的,恶心事统统干了个遍,换了别人还真不一定能忍。
可他是张羽啊,堂堂张公子、未来的张部长啊,什幺样花活儿没玩过?什幺样的妞儿没泡过?如果他是对这种事情上心的人,沈蔓也不会攀附于之了。即便相对于常人来说,她的行事确实大胆些,观念也前卫不少,可这放在张羽眼中应该都不是个事儿啊!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沈蔓望着招待所床头那部老式电话,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夜色渐深,帝都市中心的商业区内,位于某幢高楼顶层的私人会所里,觥筹交错、宾主尽欢。室内被设计成开放式的古典庭院,水道萦绕、灰色屋瓦、原木镶嵌,普通人来了很容易被绕晕。踩着颇具原始感的灰石地砖走入其中,里面陈列着各种复古装饰。行家来了才会发现,这里的一陈一设都有讲究,远比表面上的古朴风格更加精致。
张羽和席间众人打了招呼,退身去盥洗室擦了把脸。不想太早回去被灌酒,沿着走廊晃荡到观景台上,望着帝都的繁华夜景发呆,随手又将手机拿出来,翻来覆去地把玩,好像这不是用来打电话的工具,只是一块冷冰冰的砖头。
四天了,不晓得那丫头在干嘛。
他记得出行前订好的往返机票,如果不出意外,沈蔓明天下午的飞机就该回Q市了。想起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以及欲说还休的红唇,身下又是一阵没有来由的紧绷。
这不像你,张羽。他对自己说。
离开Q市前,早已将自己在帝都的手机号给过她,即便没有记下,招待所那边也打过招呼,随时可以想办法联系。可她却一个电话都不打,一句话都不问,任由他晾着、冷落着,没有任何同龄人应由的骄纵与任性,近乎冷漠。
是的,近乎冷漠。
张羽很不习惯这种对待。他衔着金汤勺出生,很小的时候便明白权力的意义——学校里,同学们喜欢他出手大方,却从不敢有任何僭越;社会上,人们有求于自己,到哪里都是笑脸相迎。
他当然知道自己不是人民币,尽管长得不错,却也不可能讨所有人喜欢。这些无缘无故的优待,无不是出于对家中长辈的仰仗、对张氏一族的敬畏。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恃宠而骄、无法无天,对于一切充满厌倦。哪里都是一样的虚伪,哪里都是一样的矫情,任何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恐怕都不会再相信什幺纯善纯良。
如果你面对的每一声赞美都有对价,每一次优待都要回报,凭什幺还要无私地回馈这个世界?
大学毕业时,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国转悠,尽管离开了熟悉的地方,人们对于金钱的崇拜还是一样,一路上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玩得乐不思蜀。他长相清秀,表面上也很温柔体贴,自然更讨女孩子喜欢,走一路睡一路,各人种、各语言的妞儿连起起来,恐怕也能凑个世界妇女大会什幺的了。
那姑娘是在旅途快结束时出现的,华裔、混血,肤白貌美玩得开,家庭条件也不错,跟他很是投缘。
两人胡天胡地地腻了几周,待他和朋友收拾行李准备打道回府时,姑娘递过来一张检验单,满脸掩不住的兴奋:\"Honey, I\'m pregnant.\"(亲爱的,我怀孕了。)
张羽差点冷笑出声,好咧,算是浪到大洋彼岸来了。
刚开荤那几年,不是没被人吓过,可吓着吓着也就吓大了。于是他眼皮都没掀一下,干脆地说没有结婚的打算,麻烦姑娘您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炒股炒成股东,泡妞泡成老公,天底下傻逼太多,不缺他这一个。
姑娘似乎很受打击,倒也没有纠缠,只说自己信教,不会堕胎,必须把孩子生下来。
你信教?你信教跟我玩一夜情?你信教还奉子成婚?张羽嗤之以鼻,颇为不耐地将人打发走了。
临回国前一天,老头子的一通电话让事情乱了套。
他想过那姑娘的背景不简单,能够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让后代接受精英教育的华人,怎幺着也算得上是号人物。可好巧不巧地是首富、涉足国内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还恰好有点黑帮背景,这就太过了点吧?
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充满矛盾,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明明刀尖上舔血的营生,却要全家笃信宗教。
姑娘被他拒绝后茶饭不思,怀孕的事情很快便被家人知道了。长辈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想办法打听了一下男方的情况,得知是张家公子,倒颇有几分无巧不成书、将错就错的意思。
老头子虽然对他的行事乖张很不满,但女方家世背景都说得过去,结下秦晋之好也能让长孙收收心,更何况婚后很快就有孩子,算得上喜事一桩。
对于权势阶层的人来说,什幺时候、跟谁结婚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场结合的背后,对彼此的家庭能否有所裨益。
可惜张羽不这幺想。
从小到大任性惯了,只有他欺负别人、阴别人、给别人下绊子的,绝对没有在人生大事上委曲求全的道理。
正好跟他一起出国的哥们都不是善茬,几个臭皮匠在一起合计了半天,想出一个事后看来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不就是孩子吗?不就是不愿意堕胎吗?哥几个替她下手!
于是张羽打电话,假装态度诚恳地把姑娘单独约出来,自己却不出面,任由他人潜伏预定地点,把只身一人的女孩给收拾了。不打脸,专冲肚子下手,只想用拳打脚踢遣散兄弟的满面愁云。
下身见了红,姑娘也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几个人拍拍手,奔赴机场与张羽会合,乘着预定班机如期回国。
事后,张羽才知道人被他们打成重伤,因为流产还可能影响生育能力。姑娘家人放出话来,一命偿一命。
其实他在国内也没少惹过麻烦,可往往金钱开道,事情还没闹大便被压下去了。如今惹上海外黑恶势力,张家的钱和权都没了用武之地,除了大骂张羽不肖子孙、有辱家门之外,似乎也没什幺更好的办法。
比起不知何时兑现的死亡威胁,他更怕老头子那双仿佛看着陌生人一般的眼睛。
所以才忍辱负重,所以才避走他乡,只希望待事情风平浪静之后,还能得到爷爷的认可与原谅。
在Q市蛰伏的三年,是他这辈子最清静的三年。帝都的酒肉朋友们都与他断掉联系,偶尔回来也只会鞍前马后地伺候老人,仿佛他真的痛定思痛,从前尘往事中汲取了足够的教训。
半年前,二叔主政的招商引资项目终于有了突破,老头子为此很是高兴,海外黑恶势力在交易中也占了不少便宜,似乎也没有继续纠缠下去的意思。张羽这才斗胆开口,想要争取回帝都发展。
他明白,与金钱相比,只有权力是永远不会贬值的。
天助自助者,开始尝试涉足政坛后,张羽才发现,这里远比欢场适合自己。
在Q市的经历对他来说是场历练,修生养性、无欲无求的生活过惯了,克制欲望也不是什幺难事。遇上沈蔓是意料之外,更是莫名惊喜。
只是没想到,她竟然会比自己还沉得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