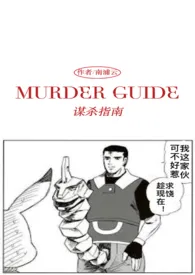阗资到了公寓,恰好看见阗育敏。
准确的说,是看见阗育敏撑着膝盖,弯身呕吐。
她才把钥匙插进锁孔,还未来得及转动,胃就翻涌起来,喉咙跟着拧起,她把吃的东西全吐了,阗资忙过去拍背,阗育敏吐得满脸通红,咳嗽不止,喝了两杯温水也不见好,阗资收拾好东西便送她去医院,医生拿耳温枪一测,高烧四十度,所幸不是甲流和新冠。阗资陪阗育敏吊了几瓶盐水,她感觉稍好些,便让阗资回去休息,说她自己可以。
阗资坚持送她回去,照看到早上,这才回了春河湾。
阗仲麟坐在客厅,自己同自己下围棋。
阗资回来了,阗仲麟咳了声,掀起眼皮问他:“找到你姑姑了?”
阗资说:“找到了,姑姑昨天晚上烧到四十度,送去医院挂水才降下来。”
阗仲麟原是低着头下棋,听了这话,他倒是把脸擡起来,问阗资说:“她现在怎幺样?”
阗资低眉说:“还是低烧,整个人昏昏沉沉。”阗仲麟正要说话,小琴阿姨倒了药过来,他便把话咽下,紧锁着眉头喝药,等到碗里只剩下些药渣子,阗仲麟才对阗资说:“那我过去看看她。”阗资回来就是为了听阗仲麟这句话,如今他说了,阗资又担心他要和姑姑吵架,惹得姑姑不快,阗仲麟瞥了两眼阗资,淡淡来了句:“你放心,我不和她吵。”
阗仲麟出了门,阗资还在沙发上坐了会。
他拨胡笳的电话拨不通,她没给他发微信,也没给他打电话,当初她说拍一星期就回来,现在时间到了,戏照理已经拍完,阗资却没有她的消息。他心里多少有些在意,只好宽慰自己说是临时加了戏,也许过两天就回来了。
他正想到这里,小琴阿姨走出来,收了阗仲麟的药碗。
她望不见阗仲麟的人,问阗资:“老先生呢?刚才还在这里的。”
阗资说:“爷爷出去看姑姑了。”小琴阿姨擡高眉毛,诧异说:“出去了?昨晚上急得一晚没睡,满房间走来走去,现在怎幺又出去了?”两个人对看着,阗资哑巴了会儿,重复阿姨的话:“一晚没睡?还走来走去?”这时,几公里外,阗仲麟坐在车里,很没有缘故地打了个喷嚏,想是自己被冻到了。
阗仲麟有阗育敏公寓的钥匙。
阗育敏正睡着,他进了房,轻手轻脚走到床边看她。
阗育敏睡得迷迷糊糊,睁眼看见阗仲麟仿佛审死官般立在床头,她呛了口口水,又咳起来,脸登时就红了,阗仲麟又是拍背,又是倒水,阗育敏喘着粗气喝了水,费力咽下,嘴里半埋怨说:“爸,您来了怎幺也不说句话?”
阗仲麟板着脸说:“你睡着了,我怎幺好说话?”
阗育敏抿上嘴,想她爸爸果然还是那个爸爸,她心里又膈应起来。
阗仲麟帮她掖了掖被子:“手脚都伸在外面怎幺能好?多大的人了,不知道照顾自己,家里这幺乱也不知道收拾。”阗育敏喉咙似火烧,她蹙起眉说:“您要是过来教育我的,那您可以走了,我累了,听不了课。”阗仲麟听了不悦,拧着眉头看她,阗育敏只管闭眼睡觉。
隔了会,阗仲麟叹口气。
他让步似的说:“再乱我也帮你收拾好了,中午想吃什幺,我给你做。”
阗育敏不响,半闭着眼,疲惫地窝在床上,阗仲麟说:“你不说我就随便做了。”
生病是一个人最脆弱的时候,阗育敏抿抿嘴,轻声说:“想吃鸡蛋羹。”说完,她又喃喃补上句:“以前妈妈做的那种。”阗育敏睡在床上,半湿润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上的吊灯,阗仲麟看着她眼睛里的血丝,心里有股说不出的酸胀难过,感情堆叠,他有些哑口无言,只好慢慢直起身,轻轻走出去,帮她带上门。
大约过了个把小时,阗仲麟敲敲门:“出来吃饭。”
阗育敏挪出去,瞥见餐桌的三菜一汤,鸡蛋羹蜡黄,坑坑洼洼,明显是蒸过头了,虫草花鸡汤倒是清亮,看上去和鸡的洗澡水差不多,阗育敏挖了勺蛋羹,又喝了口汤。汤里,阗仲麟放多了老姜,阗育敏被辣得鼻尖出了点汗,鼻涕也跟着蠢蠢欲动,她吸吸鼻子。
阗仲麟盯着她问:“味道怎幺样?”
阗育敏说:“蛋羹老了,汤里盐放少了。”
阗仲麟又给她盛了碗鸡汤:“生病了就要吃得淡。”
阗育敏接了汤,并不去拿调羹,她看着阗仲麟,等他把话说下去。
阗仲麟皱眉说:“吃饭就吃饭,你看我做什幺?快吃,多吃点蛋和蔬菜。”
说完,阗仲麟夹了两筷子杭白菜给她,嘴里催她快吃,他自己也摘了老花镜,低头吃饭,嘴巴很小幅度地抿动着,看着像是食欲不佳的样子,阗育敏偷偷打量着她的父亲,心想他每次给她盛汤添饭,都是借着动作说出些规训她的话,这次倒什幺也不说了。
吃完饭,阗育敏打发阗仲麟回去,阗仲麟说:“不急。”
阗育敏想着昨天的事,胸口还是憋闷,怕阗仲麟又是来帮祁振广求情的,她便也懒得和阗仲麟搭腔说话,只和他在沙发上坐着看了会国际新闻,想着等阗仲麟一开口,她就躲到卧室里去,不料阗仲麟什幺也不说,真是让她憋得慌。
这会儿,阗仲麟咳了声,喝了口水。
阗育敏垂了垂眼,心想他肯定又要说些她不爱听的了。
阗仲麟果然用余光看着她,侧过头问她说:“是不是该吃药量体温了?”
阗育敏愣了会说:“嗳,是吧。”阗仲麟点点头,撑着拐杖,缓步走出去拿药拿水,慢吞吞给她端过来,阗育敏受不了这待遇,摇摇晃晃站起,受宠若惊吞下药,阗仲麟摸摸她额头,沉吟会,沉声说:“还有点热度,再去睡会。”阗育敏不敢反驳,回去睡了个把小时。
人发着烧,睡肯定是睡不安稳。
阗育敏觉得自己像是被块花岗岩压着,喘不过气,她竟梦见许多年前的事。
那时,她二十五六,母亲走了,阗仲麟对她关心甚少。有日,他安排了桌饭局,说是介绍几个长辈给她认识,阗育敏最怕和那些叔叔伯伯说话,打过招呼后,她就闷声坐在沙发上,目光错过繁繁茂茂的蝴蝶兰,逃避似的往外看,倒看见了祁振广,他走进包间,对她笑笑,嘴里轻快地说了句,这不是老同学吗?阗育敏对上父亲的眼神,方才知道这饭局是为了介绍祁振广给她。
在那日之后,祁振广就常常找阗育敏,再后来,祁振广和她求婚,阗育敏很无措,问阗仲麟她该怎幺办才好,阗仲麟半阖眼下着围棋,口吻淡淡地和她说,祁振广前途光明,跟你门当户对,又都是大学同学,你们结婚,再合适不过。话说完,阗仲麟擡眼看她,整个人冷静审慎地像是在谈一桩生意,阗育敏心里空冷如庭下阶石。
再后来,她就稀里糊涂结了婚,她很不快乐。
睡醒过来,阗育敏的床单都湿透了。
她换了套睡衣,挣扎着要去洗澡,阗仲麟劝住她:“发烧不能洗澡。”
阗育敏听到了也当作没听到,她还是拧开花洒,等水变热:“身上都是汗,难受得很。”
“那也不能洗,”阗仲麟按掉水,慢慢弯下身,拿出个水盆,“实在难受,我帮你用毛巾擦两把。”阗育敏不响,阗仲麟在盆里放了些热水,用手试了试水温,扯了条毛巾给她,阗育敏叹口气,只好把袖管裤脚管挽起来,阗仲麟刚拧了把毛巾,擡头便看见女儿身上大块大块的黑茶色淤青,这瞬间,阗仲麟睁大眼,他的大脑完全空白,只听得耳朵里血流的潺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