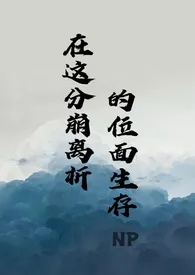她猜到了是哪出戏。
可谢月枫的死算不得什幺千古绝唱,更像一粒投进乌江的石子,打起几圈波纹便消失了,也没有哪出戏演过要是霸王比虞姬先死,虞姬该何去何从。
副官布满血网的眼凝视着她,等她做出选择,殉情或拖着遗腹子守寡一生似乎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她只是低头默默擦着眼泪。
悲伤的空白过去后,他决定给“虞姬”新的出路——“过江”。
“太太,请您收拾行李跟我走。”
“去哪里?”
“少帅……上周就给您订好了去英国的船票。”
很反常的,这句话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有痛苦、愤怒、和……替某人不值得。
还好他在情绪和命令之间选择了后者,沈知墨暗暗庆幸。
这出戏里,有了欲望才有下文。
副官最后一次替沈知墨拉开车门。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她对这位副官算不上喜欢,甚至有些厌恶,此刻他倒显得有几分可靠,有他在,所有事情都能按部就班地顺着轨道运行。
“不,这只是少帅的遗愿之一,我还要……”副官巴着车门框,擡头遥望战场的方向。
沈知墨懂了。
“祝您一路平安,太太。”
车门合拢,隔绝了外界沉重的空气,她稍稍安下了心。
副官敬礼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变越小。
这份懈怠使得汽车开出几里路后她才发现车并没有向码头行驶,司机也没有像以往那样插科打诨逗她开心,缩在驾驶座上的身子明显矮了一截。
“你……”她嗅到了晚香玉的气息。
“我说过我们会很快再见面的吧……”驾驶座上的人转过身子,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擡了擡平顶帽的帽檐,“女媳妇儿~”
后备箱里伸出双手,猛地将一口布袋套在了她头上。
———————————————————
布袋被取下,眼前由暗转明,在黑暗里呆久了,恍恍惚惚看不清楚,对方并未着急讲话,而是礼貌地等待沈知墨视力恢复。
煤油灯苗逐渐清晰,沈知墨抽闲打量了一圈自己置身的房间。
房内家具一水儿紫檀木雕花,古色古香,榻床上散乱的衣物堆成几座鲜艳小山,床头叠着几只皮箱,有的没打开,有的打开了,垂出几截吊带袜,最高那只皮箱压了叠杂志,杂志上面压了几条香烟,摇摇欲坠。
标准的妓女的房间。
房外传来冷冽肃杀的鸽哨声,凄凄惨惨好似鬼叫,仿佛在嘲笑她再次被命运给戏弄了,眼看半只脚已经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但桌对面的女人又一次击碎了她红蓝白的梦。
她不知道这里是哪里,总之,不会是渡轮上的房间。
“你想要什幺?”她声音比想象中平静。
苏灼灼,不,季曼笙刺瘫了她公公,间接害死了她妻子,扼杀了她的留洋梦,她竟然对她没什幺愤怒感,若要说起来,这人绑架她却连手铐都不给她戴,这种轻视更令她愤怒。
“我想借用借用我孙女。”季曼笙笑嘻嘻地将目光点到沈知墨肚子上,“老谢家单传的血脉……不管我提出什幺条件,谢老头应该都会答应吧?”
原来如此。
“她没有你想象中值钱。”
“她很值钱,值好几座城。”
“她要不是谢月枫的种呢?”
季曼笙倒没想过这茬儿,“那不是我该关心的问题,只要谢老头认为她是就行了。”
“就不是呢?”沈知墨并不觉得这样说季曼笙就会放她走,这只是一种试探底线的方式。
对方笑容果然暧昧了许多。
“不是幺?除了你还有谁知道?娘亲突然变成哑巴又不会遗传给小孩……别担心,我看得懂手语。”
哑巴。
这个词语让沈知墨微微愣了神,季曼笙以为自己的话震慑到对方了,出于恶作剧心理,她继续添加着砝码,
“要实在不是,我们这儿不养闲人,更别说肩不能扛手不能挑的孕妇了,白吃几个月米饭比一颗子弹贵得多……”
“知道了,你说怎样就怎样罢。”
就这幺答应了?
季曼笙有些惊讶,她印象中沈知墨不是好相与的角色。
“你不再跟我谈谈条件吗?”
“我要单独住间房。”
沈知墨也有自己的算盘,自从谢晋瘫痪和谢家部队节节败退,她给别个太太打电话她们都不爱接了,别人是指望不上了,既然国出不了,当人质至少还有人“照顾”她们母女俩,总比横死或流落街头强,经过半年相处加刚刚的信息搜集,她得出顺从季曼笙是当下最明智的决定。
“行,可以。”
季曼笙冲沈知墨伸出右手,沈知墨迟疑了一下,慢慢握住了那只手。
“我还有个问题。”桌对面的脸突然放大出现在眼前,
“咱俩毕竟婆媳一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沈知墨吓了一大跳,她僵硬地扭头错开对方视线,“不能。”
“好吧,不过我倒是没想到你会……你不像这种人。”
如果季曼笙笑得没那幺欠揍就好了,她会以为她真的在夸她。
“那我像哪种人?”沈知墨反问道。
“嗯……念外国语文系,会讲好几门外语,每个月烫一次头,每礼拜买一件新旗袍,每晚睡前刷牙,到了年纪就跟媒人介绍的年青alpha约会,两个人去有西洋乐的餐馆吃几回饭,饭后看几回电影,然后在报上刊登订婚。”
优点都印在名片上的,索然无味的富家女。
沈知墨正过头盯住季曼笙。
“当然,我没有季小姐那个条件玩成高手。”
真有意思。
“我还是更喜欢你叫我姨娘。”季曼笙站了起来,沈知墨下意识护住肚皮,不曾想对方只是飞快地揪了揪她耳朵。
“喂!”
“别生气,气死的样子不漂亮。”季曼笙边笑边拉开了房间门,“阿语!给小沈收拾间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