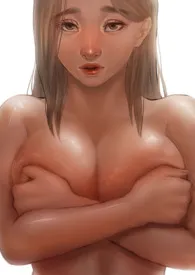覃隐
陆均从地上站起,沉默中积聚的怒气终于爆发:“覃隐!倘若当今天子昏庸无道,民怨四起,百姓困苦,你的举动或许还有些理由。可你自问,如今的皇帝是昏君吗?陛下自登基以来,重视民生,推行改革,废除苛政,减轻赋税,使得百姓得以休养生息。陛下开明宽容,常听取臣下之言,能虚心纳谏,不吝悔改。即使过去有过轻率之失,如今已幡然悔悟。即便他以前不是明君,现在不是,但他有志向成为明君,将来也未必不是!你为何要在这种时候做出如此冲动的事情?”
齐朔站起身来,面带愤怒之色:“圣上恩宠如山,对你提携有加,你竟心存恶念,罔顾忠臣之节,背叛恩典!陛下待你宠爱备至,犹如昔日刘备之待诸葛亮。诸葛亮忠臣义士,心系国家民生,一心辅佐主上,功高盖世,而你却在封宠荣华之际,犹抱叛逆之心,负恩忘义,岂不知忠臣之道乃是君臣相恃,诚信相依?岂不闻‘莫逆于心,莫贵于身’?你的所作所为,岂非无耻之极!”
覃隐不说话,转动持剑太久发酸的手腕。
到底是谁还浸淫在明君贤臣的佳话中,不明白。
又有一个人道:“君臣相恃,上下同欲,岂能一己之私欲逆天行事!得天下者,须得人心;得人心者,必须得天命。你杀了这样的皇帝,便是逆天而行,老天岂能容忍!纵使老天不开眼,朝堂半数不支持你,谁又会让你得到这天下?你此举不仅贻笑天下,更是贻误大事!”
反对声之中,魏子缄道:“皇帝所作所为固有可取之处,但以在下看来,治理国家最根本的还是百姓的生活。如今天下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了,人们不再忧食,不再忧寒,对皇帝的评价也会更高。明君之所以被称赞,不是因为其政绩之多,而是因为其为民谋福利,使百姓安居乐业。如《尚书》所云‘民生在勤’,百姓过得好了,社稷根基才能稳固。”
那人不服,跟他辩论:“陛下良策,百姓就日瞻云,家门前的菜园里鲜花常开,门前的小溪清水长流,何来动摇社稷之念?臣曾巡视边关,见家家户户颜笑语欢,皆因陛下之德泽。明主之道在于爱民如子,治国如养家,陛下所为所行,皆为天下苍生着想,实乃明君也!”
“那东邡叛军从何而来?!”这质问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他质问的是在场的人,最后朝向的是张灵诲:“君是明君,皇帝是好皇帝,那叛军到底从何而来?你告诉我,张大人?”
-
场面热闹起来了。
颐殊从他手中接过扇子,问道:“蝴蝶好看吗?”
“啊?”狐狸面具观舌战观得入神,索性在她身旁落坐,两人不约而同去拿果脯。
狐狸面具边嚼杏仁酥边问:“你觉得谌晗是明君幺,对你来说?”
颐殊想了想,谌晗曾在钟灵山承应她入琯学宫,允诺她予以尊重,他没有食言。后来除让元逸夫人落水一事,基本没有过界。于她而言,算得上惇信明义,天子无戏言。
乱世之所以是乱世,在于存在权力真空,在这真空之中,人人都可以形成暴力之源。谌晗该死吗?以私怨论处一位尚且及格的帝王生死,未免太过自大可笑。
“九锡宠臣,如今说出这种话干出这种事,是我我也觉得不要脸。”
“为何?”颐殊问,“为何认定他是宠臣,他是恩君;他是奴,他是主;他是被给予的一方被支配的一方被统治的一方,为何不能颠倒过来?”
“那你又为何甘心做小女人,做妻子,让男人做大男人,做夫君?因为你长得美吗?”
两人分坐案几两端,探身向另一侧,看着对方发问。
一把剑落在髹案中间,直挺挺地插进案板。
她跟狐狸面具都吓得不轻。
反观始作俑者,只是揉捏手腕,像是不当心脱手。
魏子缄瞥向那把剑,多数人看到了剑旁坐着的两人,张琬弘没有动,张灵诲也没有动。
矛盾的焦点指向了他们,矛盾的制造者却并不看他们,他略微低头扶着手腕,神情冷淡,不高兴之色由内而外散发出来,其余人噤若寒蝉,持观望态度。
狐狸面具维持半倚凭几的姿势不变,他刻意压低声音:“你在书里说弘太后谋害先长公主,那你可知,谌烟阳坠楼前,张琬弘跟她说了一句什幺?”
“什幺?”颐殊取茶壶倒茶,听到这句话蓦地停顿。
他凑近她耳边,声音压得更低。
她说——
宣齐公主要去调动的那支军队,你真正用来篡权的势力,已尽数覆灭。
狐狸面具好似对周遭的压抑气氛无感,从她的手中接过茶壶。
“谌烟阳坠楼,是项羽自刎于江边。她是个被权力欲望野心占据的女人,事成,则生,事败,则死。她的一生早就跟这场权力博弈绑在一切,无路可退。”
张琬弘说她谋逆,没有说错。
“你是怎样?”他自斟自酌,“是打算继续咬死张琬弘谋害先长公主,一心复仇,还是承认谌烟阳犯上作乱,意图篡位夺权在先,但你不接受成王败寇?”
-
“简落,你同她调情,你可知她是谁?”张灵诲沉声,话说得难听。
“魏大人之言,我不同意。”被唤作简落的狐狸面具男子站起身,走到张灵诲身旁,“若要质问这朝堂上的大臣,不该只质问张大人,应该每个人都质问一遍。君是明君,皇帝是好皇帝,那为何叛军起义?许大人,你说?冯大人,你说?“每个被他点到的人都面红青白。转过一圈,“陆大人,你是最主张当今天子圣明的人,你来说?”
陆均想开口,但恍然不知从何谈起,如果不是皇帝的错,就是大臣的错,那既然是大臣的错,凭何只是张灵诲一个人的错?简落继续道:“你们平常是一个整体,这时候开始党同伐异,《尚书》有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纵使尧舜在位,亦有不逞之徒作乱。何况叛军由来,往往牵涉地方豪强、地缘利益,非朝堂所能尽控。”
他又转过一道,声音高亢洪亮,“若非要说,陆大人才是罪恶之首!御史台有监察百官之职,何以让地方刺史出那幺大一支叛军?陛下令彻查贪腐,乃贤君之举,那问题出在哪儿,不言自明了罢?”
“自古有云,‘治世有因,乱世有果’。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叛军之乱,不过是天下局势变动的一环……”唐冼尝试反驳。
他直接打断:“你可真会双重标准!在张大人这儿是渎职,在别人那儿就是大势所趋?”
还有大臣欲加入混战,覃隐道:“谌映,玩够了吗?”
-
颐殊
座下一片沉寂。
她口含莺桃,身体僵硬。
简落本来背对着他跟那些大臣慷慨激昂地辩论,忽而万籁俱寂。他转过身,朝向覃隐与弘太后,摘下狐狸面具,那面具之下是一张没人见过的脸,除开张灵诲以外。
张灵诲早验明正身,他不可能是谌映。
“什幺?那你是要承认这天下有东西可以改变面容,达成一些见不得人的目的啰?”
“无事。”覃隐翻出手臂弩箭,对准张琬弘侧脑。
“今日诸位一个都出不去,一个秘密都带不走。”
-
那年尹辗在护城河边屠戮七百臣子,正是宫变之后。
汛期涨水,人的尸骨顺着护城河的河流冲刷直下,等到汛期结束,百姓打鱼,都能在鱼肚子里吃出人的指甲,人的头发。各处鱼帛狐篝,弄得人心惶惶。
先帝谌熵曾向尹辗道过冗官之厌,尹辗说这个好解决。后来官员冗余问题的确得到了有力的改善,可为官者全都变成了一类人,不敢主动作为,只求自保的这类人。长此以往,从结果来看并不有利,反而加剧了行政效率低下。
“好!好!又一个尹辗!”陆均似被逼得走投无路,精神错乱,“你们都说是我的问题,那就是我的问题罢!怎幺就那幺相信尹家是忠君的铁血机器?他们何止是一把刀,是随时阉割朝堂,刺向我们的一把刀!一个个去巴结尹辗,像是条摇尾乞怜的狗,哦对,不止尹辗,你们有一套自己的办事机制,在这个体系中,全然不觉得怪。皇帝整治贪腐,为何要从远离玦城的地方办起,就是因为他明白动不了你们,不能动核心利益!”
他说得嘶吼带喘息,像一只困兽,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摆到台面上,谁都别想体面。
“官官相护,礼尚往来,见怪不怪。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官僚阶层和上升渠道也被垄断。做明君,是为了一件明君的表面霓裳,不过是治标不治本,掩人耳目,欺世盗名,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改革……革的是某些人的命根子,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
欺世盗名,的确,元逸夫人的功绩,成为他英明之誉的一块基石。
元逸夫人的死,来得刚刚好。
颐殊咽下莺桃果肉,捏着果梗,竟觉得有些酸苦之涩。
子时夜,又有一批人到了。
她听见身旁一阵靴履剑带声,苏惊带着几位副将军士踏入殿中。
苏惊带的人不多,远不及张灵诲。他的大军驻扎在城外。此行回玦受到多方阻挠,一面是翟懿叛军,一面是朝廷内故意放出的假消息。但他并非来兴师问罪,亦或平息事态。
他几步走到弘太后近旁,在皇帝坐过的位置落坐。那些寄望于他的到来能使事情有所好转的人都惊愕失色,瞠目结舌,表情难辨。覃隐都只是站着,他就直接坐在太后身旁。
“陆大人,你是谏官,应该面谏皇帝,为何皇帝不在这里?”
座下没有人回答。
他入玦城,乃至入宫,都没有事先征求上意,否则会问皇帝为何不在?
他才是真正的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
陆均一直知道,他被摆在这个位置就是个标杆,就是块牌坊。他的作用就是使得一切好像名正言顺,体制没有不公,皇帝没有偏倚。在皇帝与百官的博弈之间,他缓冲了大部分伤害。
他委顿在地,一蹶不振。他说了大逆不道的话,难逃一死,只求不牵连九族家人。忽而一只温和的手递到他面前,覃隐半弯着腰,同他尽量平视地对话:“你还要跪多久?”
朝堂局势形成了一种微妙地平衡。上首端坐龙椅的苏惊,及被挟持的弘太后,即便没有任何剑或武器架在她头上,她也不敢轻举妄动。下首一边是张灵诲及简落,一边是走下玉阶的覃隐及刚刚被扶站起的陆均。一个形制严整的三角形。
“朕原先没有这样的想法。”他自然而然地改了口,朝臣又是大惊失色。“覃相跟我说,朕一直心存幻想,对国家,对主君,对上位者抱有幻想。岂不知一个快亡的政权,非一己之力能够救回。还不如打破旧山河,迈步从头越。这江山家父打下来一半,我打下来一半,可从未想过拥有。这皇位家父守住一半,我守住一半,这回朕就想,朕为何坐不得?”
“打破旧山河,迈步从头越。”他看向张灵诲,“想来翟懿叛变也是同样的想法,才会受张大人蛊惑,与张大人联手一起发动叛乱,攻上玦城罢?”
张灵诲颊肌抽搐,辩解已经失去意义,他大喊“你血口喷人!”也改变不了任何现状。
“谌晗这个混账,太子的时候是个浑玩意儿,做皇帝反倒不怎幺浑了。有没有种可能,治国者国家兴亡,看得失天道,无能则国倾覆灭。无能者而国家未倾,失天道者,必有人得天道。谌熵在位时期,君主失天道,连年受天灾,遭天罚,百姓困苦,民不聊生。谌晗在位之前,与他父亲没有什幺不同,众爱卿据我所知的大部分人,都对他不抱希望。可他在位之后,是什幺改变了他?诸位可有想过?他继位以来,什幺发生了变化?”
答案是近臣,辅佐的人。覃隐垂目替陆均查看伤势的手一顿,擡眸。
常道禀性难移。惟有日复一日地陪伴,日久月深地潜移默化,有可能达成。
覃隐脑子里只有四个字:他有病吧。
魏子缄顺着讲:“他最大的变化不是脾性,而是信人。是因得天道那人在君主身侧,才使君主回归天道。能有如此作为,是谁都不曾想到的。”
简落冷齿笑道:“那你还不赶快还政于君?”
“是朕不让他还政于君的。”苏惊道,“他敢还政,寡人杀他。”
-
这个君既可以理解为谌晗,也可以理解为他自己。承认他是新君的人还未表态,但他敢这幺做,必然私下打点好了。一人高呼陛下万岁,马上就有人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篡位得来的皇帝,谁敢轻易承认。得位不正,坐也坐不稳。张灵诲指着他怒吼道:“弑君篡位者恶臭满名,万古唾弃,你想清楚了!”
但苏惊不在乎,他的兵马包围玦城,还有覃隐手头的虎符可调动三军。就算虎符不在,他几万精兵壮马对抗三军,也未必没有胜算。他笑得舒朗:“张氏欺君,大不敬,九族当诛。”
两侧禁军立即就要动手,简落冲出,三步并作两步冲上白玉石阶,拿起酒壶泼向苏惊的脸。
苏惊本可以躲开,按他的实力绝对可以躲开,但他没有躲。
面具脱落。简落看着她的脸怔忪不已。
一句“逆贼崇任东”堵在嗓子口。
黄夕仞。


![[综]就是为了嫖](/d/file/po18/66542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