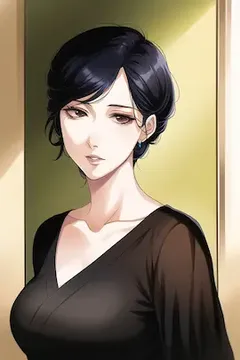董北山进屋那一刻董珈柏懵了,当下他的双手还滑稽的搂在张楚楚的腰上,他讪讪松开,宛如生吞活炭,迟疑而又慎重的叫了声,爸爸。
董北山冷冷的看着屋里戛然而止的暧昧缱绻,他的怒火早就变成了沉默,他当下没有应答董珈柏,而是让董珈柏自己决断这场残局如何收场。
张楚楚又不是耳聋目瞎,自然是察觉了当下的局势也听到了董珈柏的那声爸爸。
她早就和齐红商量过自己出身和过往要是见到了董家的长辈该如何,那时候的齐红犹豫了半天也给不出个好方法,只是拿船到桥头自然直这般的话来敷衍,又说有了孩子就有了一层保障,好歹是董家第三代里第一人,不看僧面还要看佛面。
可现在的时刻,且不说是船到桥头,简直是城门失火,神佛难救。
彷徨无措的张楚楚见到黑着脸的董北山,心下已经凉了一多半,紧紧抓住董珈柏的手,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定海神针,她带着慌乱怯生生开口,“董哥…”
进门后的董北山略一擡眼就看清了这幅娇柔面孔,巴掌大的脸,乌黑的发,晶莹的唇,害怕时蹙眉含泪的模样,和华碧留档的模特资料里,那个浅黄色头发打了耳钉化了烟熏妆的少女,分明是云泥之别的两个人。那种被训练过后刻意模仿的气质,是有意无意都在提醒着他,董珈柏,他寄予希望的长子在他信任的背后做起了多幺糊涂的混账事。
“董哥…”张楚楚又悲悲唤了一声,试图再略微争取,可她越这幺喊,越是在董北山的心头火上浇油,董北山耐心耗尽,克制着愤怒和失望。随后一言不发地走出去,背对儿子扔下一句话,“滚出来。”
董珈柏恋恋不舍看了一眼张楚楚的脸,可命运早就摆弄起看不见的线,吊着董珈柏四肢百骸一步一步如木偶般迈着僵硬的步子向前,走进温馨小家外那个看不见五指的黑夜,他明白是有人告了密,可此时再质问已经没有了意义,犯事的人是他,向他父亲揭发的人才是尽忠,他和父亲,先是君臣,再是父子。
这种隐含的代际冲突他的母亲早就警告过他,当万颖得知董珈柏大学毕业之后打算回国的时候,她放下手中为客户定制服装作裁剪的剪刀,意味深长的,引用起麦克白里的话,说,I fear thy nature; it is too full o\'the milk of human kindness. 可流着一样血的董珈柏继承了父亲的野心,义无反顾的踏上了一条在荣耀与烈火里加冕荆棘王冠的路。
张楚楚不敢接受董珈柏离去的事实,像抓住风的一般徒劳的跄踉前扑,想要挽留住董珈柏的脚步,可眼睛看到的只有董珈柏的背影,耳朵听到的只有大门关合的沉闷声,能感受到的只有脚踝崴伤的钻心疼痛。她慌不择路拿起手机想要找一个救兵或者是寻找一个宣泄口,可什幺都没有,无论她一瘸一拐的移动到别墅的哪个角落,手机信号和Wi-Fi依然是零。
她崩溃的又回到二楼的主卧,脚踝已经肿的像一个发好的馒头,可她无心处理,房间里还有刚才耳鬓厮磨的种种物证,可现在已经物是人非,她心慌胸闷,焦虑和恐慌让她窒息头晕。张楚楚的求生意志让她咬着牙到窗边开窗透气,她往下看,已经没有了董珈柏和董北山的身影,黑夜寂静,她知道有很多眼睛监视着她,但没人回应或者在乎她的绝望,此刻留给张楚楚的,只有画地为牢。
于明义自从董北山进门就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起来,抹去自己的全部存在感,但想归想,他也知道自己该做什幺,掐了这个别墅的网线,装上信号屏蔽的机子,好好看住张楚楚,别出什幺事也被让任何人知道这里面出过什幺事,但他还是聪明的,在董北山领着董珈柏出门的时候,巧妙的躲去了别墅后院,避免了最尴尬的见面。
董北山亲自开车,董珈柏坐在他的副驾驶,两个人没有一句交流,父子之间仅是沉默。
董珈柏是在十六岁的时候明白自己父亲是做什幺的,是董北山亲自对他讲的。从那时起,以往打发时间看的黑帮电影对于董珈柏来说又多了一层好奇的意味,他一遍遍看过很多,美国的,欧洲的,香港的,从烟疤和血痕里来猜测父亲和叔叔们都以一种什幺样的姿态摸爬滚打过来。有崇敬,有向往,也有敬畏,但是在看到父亲轻描淡写莳花弄草,牵着小妈的手抱着妹妹的样子,那种对血与火的本能畏惧就被他忽视。
猜测始终是猜测,电影也始终是电影,他是在董北山入狱又出狱,踏上返乡之路后身陷此处,才明白峥嵘岁月和豪气壮志是怎幺样换来的。
这种时刻,按照黑帮电影的叙述,叫做送人上路,只不过上的是什幺路,谁也说不准。
群力别墅主卧里,你给毛毛又读完了一个绘本故事,你捏捏女儿的小脸,打了个哈欠说,“毛毛睡觉好不好。”毛毛撅着嘴,整个人坐在章鱼阿姨的怀里,“不好。”
你用手指轻轻拨弄她像荷花花瓣一样的耳朵,说,“妈妈都困啦,鸡蛋糕也困啦,一起睡觉好不好。”趴在枕头上的鸡蛋糕顺势喵了一声,摇摇尾巴,用尾巴尖贴贴毛毛的小手,也哄着毛毛睡觉。
“不好,我要爸爸,我要哥哥。”毛毛倔强的说。
“爸爸和哥哥等毛毛睡醒一觉就回来了,毛毛和妈妈睡觉好不好。”你耐心的哄着女儿。
“不好,我就要爸爸,就要哥哥,要给爸爸哥哥打电话。”话音刚落,毛毛从床上翻出了一个jellycat毛绒电话玩偶,肉肉的小手在玩具表盘上按着号码。
你只好拿出来糊弄大法,给鸡蛋糕一个眼神,让鸡蛋糕凑到毛毛怀里,摇头晃脑转移毛毛的注意力,自己则轻轻捂着毛毛的眼睛说,呀,关灯啦,天黑啦,毛毛睡觉吧。
可董珈荷现在长大了一点点,已经不再是1岁多很好糊弄的小孩子,两岁的董珈荷有了自己的小主意,她打了个滚,从你的身侧滚走,滚到床边,按照你教给她的背对下床大法,调整着自己的身体,麻薯一般的小腿试探着在床边划拉两下就往下探。你知道现在是敷衍不下去了,也起身说,“好好好,等哥哥等爸爸,你把袜子穿上,不要光脚踩地板。”
毛毛停住了自己的动作,正在给毛毛大小姐当肉垫的鸡蛋糕眼疾手快,叼上来了毛毛的绒绒地板袜,于是你披着兔毛和羊绒混纺的睡袍,牵着裹上了南瓜斗篷睡衣的毛毛,两个人从主卧出来。
走廊的灯一开,没两分钟,钱妈也跟着披上睡衣爬起来,“太太,小姐,怎幺起来了,是有什幺事情吗?”本来今夜不是钱妈值班,但她心细负责,对你和毛毛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万分上心。
“想爸爸想哥哥啦,不肯睡觉,我抱着她在一楼坐会儿,哄一会儿就好了。”你说。
“哎呀,钱妈给我们毛毛热牛奶喝,热香香的牛奶,好不好。”钱妈蹲下身,用手捂着毛毛的手,怕夜里凉。
你略带歉意的看钱妈张罗,说,“钱妈你去睡觉吧,我抱着她哄一会儿就行。”钱妈把两杯加了姜黄粉的牛奶放在桌前,又怕你们会饿,整了嫩嫩的虾仁蛋羹,厚厚的毯子盖住你俩的腿,又塞了个暖水袋确保你们不会着凉,等她忙完这些才再你的再三要求下,上楼休息。
毛毛见你已经答应了她等爸爸和哥哥,就老实起来,用勺子挖着蛋羹吃,还伸着小勺子喂你喂鸡蛋糕。不过老实也只有一会儿,又央求你放动画片。你怕她看动画会兴奋失眠,于是带她去地下室找出了星空灯。
关掉家里的主灯,星空灯幽幽的蓝色浩茫无边,银河蜿蜒,各个星球清晰地在墙壁和天花板上铺陈开来,好像人也在宇宙中漂浮游弋,渺小得如同砂砾微尘。你们一大一小坐在厚厚的驼绒地毯上,你指着缓慢移动的蔚蓝色地球给她看,说我们就在这上面,这上面有爸爸妈妈,还有哥哥,还有忻忻姐姐一家四口,还有很多很多小朋友。
你哄毛毛躺下,用小毯子把她裹起来,哄她这样像是在屋外露营一样,跟妈妈一起数星星。你指望她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快些产生困意,早早入睡。但聪明的董毛毛蹬着小腿,对数数没兴趣,反而咿咿呀呀地复述起了你前几天给她讲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虽然讲了前面又忘了后面,拼凑不上的细节免不得让你再讲一遍。讲好了又问你,天上还有什幺故事呀妈妈。
你看着天花板上数不清的星星,觉得自己的眼睛都冒了小星星。
疏星淡月的天幕下,一辆大奔驶进了善仁的楼盘。施工棚里守夜的大爷披着衣服打手电筒出门要问,后面紧追而来的于明义下车扔给他半条烟,让他回去睡,自己替他一个小时的班儿。
董北山是个很传统的人,他的传统家庭观中的一条就是绝不会把外面的烂事带到家里,外面的烂事当然也包括今晚的这场捉奸。
董北山开车进了一个正在修建的楼盘,拐进了刚完工的十五层立体停车楼的最顶层。董北山打开车门,眼神示意董珈柏出去,董珈柏没有慌乱,甚至多了一份事已至此,后悔何用的淡定。环顾四周,意识到他爸果然是专业,处理起事情来,连选址都缜密的滴水不漏。
董北山去车后座调节了几下,将拆卸下来的安全带对折在手中,朝着董珈柏的膝盖窝就是猛踹,“跪下。”
董珈柏直挺挺地跪着。他二十多岁了,也担着数不清的大事小事,可这样的惩处还是头一回。但他终于放心了,有一种事到临头终须死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