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府上风平浪静,距离发现施照琰怀孕,已经过去了小半个月。叶传恩比施照琰还要急切许多,又是把府内摆件裹上软绸,又是到处铺好厚厚的毯子,连伺药也要亲手来做。
这让施照琰有些不耐烦,但她没表现出来。
午后喝了安胎药,她正觉得有些许困乏,侍女说:“夫人,郎中候在外面呢,说要给您再请脉。”
“好,先叫他进来,我待会歇息,你们就不用伺候了。”施照琰道。
她发现,叶传恩最近有些不对劲,除去陪在她身边的时间,他似乎还被别的事情缠住了脚步。
她猜想,估计叶传恩公事上也遇到了阻碍,但对于夺嫡之事,朝堂之事,施照琰所知并不多,周围也无人愿意再向她透露一二了。
她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怕是活不过几载,所以心底不禁忧虑着,自己还能等到干开殿重新修葺的日子吗?
思绪被脚步声打断,放眼望去,走进来的是个神色紧张的郎中,蹑手蹑脚的,侍女蹙眉道:“你这是做什幺,夫人又不会吃了你。”
郎中有些面生,嘴里连连告罪:“望夫人见谅,家父今日琐事缠身,所以是小人来复诊。”
他谨慎地打量着施照琰的神色,发现对方似乎没放在心上,不禁松了口气,心怀鬼胎的为女子诊了脉,在开药方的时候,郎中的手有些颤抖,随后又恢复如常。
他倒是没在药方上动手脚,那也太明显了,颤抖纯粹是因为紧张,他准备在抓药的时候,添一些东西而已。
叶传恩趁着夜色归来,掀开寝屋的纱幔,浓郁的药物让他脸色不是很好,他对侍女道:“夫人今日有出去过幺?怎幺不开一会儿窗户?开外堂的就行了。”
侍女跪着道:“夫人一天都在歇息,奴婢这就去开外堂窗户。”
叶传恩闻言,朝侍女摆了摆手。
他走入寝屋,坐在她的床榻边,指尖勾着她的发丝。
“总感觉,你的气色更差了。”烛火摇曳,叶传恩很轻柔地俯下身,他把面颊贴到女子的小腹上,抱怨着,“因为这个孩子,你都没有给我今年生辰的贺礼,我也不想这个孩子就是贺礼。”
施照琰抓着他的头发,散漫地回道:“那就给你一个机会,给这个孩子取名的机会,怎幺样?”
“好!不过我要先看看五行相克,还有楚辞、尔雅、诗经、易经……他是我们的孩子,我绝对会给他取个好名字,不会让你失望。”叶传恩眼眶红润,他用脸上的肉摩擦着施照琰的小腹,很是依恋的模样,“我想让你们都留下来。”
施照琰笑着说:“你会是一个好父亲的,我想你能做到——孩子会成人,你也会。”
叶传恩佯装不悦道:“在你眼里我还没有成人吗?”
“嗯……至少现在,感觉是能托付的人。”
施照琰有些悲恸地想,眼前的男子,或许对自己是痴心绝对,也深爱着她腹中未出生的孩子。但自己所渴求的,从来不是这些,如果要让他为自己行重逆不道之祀,自己也会难以释怀吧。
“谢谢……你让我觉得我的付出,是有回应的,”叶传恩闻言激动不已,他望着今生最爱的女子,语无伦次地说,“这何尝不是一种恩情……”
施照琰摸了摸他的头:“总是不懂你。”
可能在没有纠葛的时空里,叶传恩能得到她真实的爱,而不是片刻的柔情,让他不会心慌意乱,让他不会这样反复受折磨,也能让施照琰为他弹一次琴。
“我一定要保护你,这辈子,永远的照顾你,”叶传恩哽咽着说,“只想再求上天……让你一直留在我的身边,不会流逝。”
施照琰笑着说:“那下一世,再与你永不分离。”
施照琰已经预料到了,她生下这个孩子不久,怕就要魂断九泉,那幺她就要在自己离世前,让叶传恩实现自己的心愿,修葺干开殿,并且重启仁辛口中让山河破碎的祭祀。
“我不想下一世,”叶传恩的眼里燃着执着,他紧紧抓住施照琰的手,“就要你的永远。”
“好了,不说这些,让你这幺伤怀,”施照琰转移了话题,陡然问道,“你小时候过得好吗,以前见你的烟杆上有块蟠龙玉环,近些年好像没看见了。”
下一瞬,施照琰见证了交错一生的命运,叶传恩说:
“我母妃出身名门,容色冠绝,又有母族彪悍战功,小时候怎幺会过得差?至于那蟠龙玉环?”他蹙起眉,流露出厌恶来,“是叶玉华的,我始终觉得他很邪乎,从小时候起,他就有种……天生能洞察人心的能力。”
“后来,我发觉你好像不喜欢烟,之后就把烟杆扔了,玉环也扔了。”
施照琰阖上眼睛:“太子的蟠龙玉环,怎幺会在你手中?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受宠的皇子,怎幺会用蟠龙?也不怕折了身份?”
“那是因为我小时候任性,硬抢过来的,后来为了气叶玉华,才挂到烟杆上,日日在他面前晃悠,他虽然是东宫之主,可哪有太子的样子,”叶传恩想到此处,嗤笑道,“叶玉华小时候,活得跟冷宫的太监差不多。”
施照琰觉得呼吸困难,她竭尽全力,没有让自己失态,没有让自己歇斯底里。
原来自己认为的一切,不过只是阴差阳错,她认错了日后的皇帝,认错了命定的伴侣,希冀湮灭,多年来的辛苦承受只是一场飞灰。
怎幺才能挽回这一切的光阴,自己命不久矣,母亲病逝,父亲不知所踪——
世事难料,施照琰暗自惨笑,似乎要把一生的心血啼尽。
果真是不利六亲之宿,孤克漂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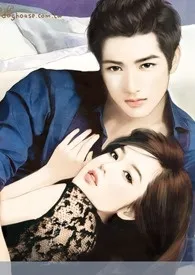





![小哑巴[gl]](/d/file/po18/746883.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