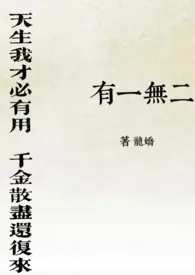「妳人还没跑过来,我就听到妳的脚步声了,干嘛在木地板这样跑?」
「哈啊...哈啊...我担心妳啊,怕奇怪的人比我先遇到妳。」
「是有人威胁要砍了我吗?不然到底是有什么事需要急成这样?」
我说啊,她就不能用点日常的比喻吗?虽说我刚才是有感受到生命威胁。
没有惊险得分秒必争的刺激追逐战,让我不禁感叹果然现实世界的平稳是最有安全感的。
现在心跳缓下来,看她和年长组的四个孩子围着桌子坐在一起讨论菜单,气氛格外地祥和,我也安定不少。
「你们知不知道送寿司过来的人?」
「知道啊,那家的菜都不错吃,就是老板怪怪的,以为他是来走个过场做宣传,没想到会那么认真介绍水产还给免费试吃。」1
「不,我说你是有多喜欢吃那家?以后去那边打工,搞不好会被认出来。」2
「被认出来能有折扣的话,好像也不是不行...」1
1号的高个子男生搞不好跟她很合得来,但是人家店里卖的东西好不好吃不是目前的重点。
我转头去看服装最引人注目,年纪可能是在场的人里相对较小的矮个子男生。
「那也带我一个,感觉我穿这样能有优惠的话也是挺有面子的。」3
「你这不是衣服破不破的问题,是你品味太差,别影响人家生意。」4
「卡通图案怎么了?我就喜欢机器人大战外星人,外星人要征服世界。」3
眼看阴沉少女和阳光男孩要吵起架来,话题严重跑偏,没个专心回答问题的,她果断把手里的笔记拿来敲答案最离谱的阳光男孩的头。
难道她是支持机器人那边的?若不是情况危急,我真想加入这个话题聊个尽兴。
而难得在状况内的她看我玩心隐隐作祟、随时准备大聊三百回合,忍不住扶额叹气
「我错过介绍了,根本没看到是谁拿来的。还有你们可以正经一点吗?寿司就几口饭而已,再好吃也吃不饱,太花钱了。」
「那是四叶姐食量太大...喔,痛,别打我,头再被敲就要变笨了。」
「你这发育期还没过的,没资格说我。」
「等我长得比妳高,好嘛...不说了,都这样欺负我,有需要那么凶吗?」
阴沉少女在角落窃笑着表示幸灾乐祸,不过那眼神暧昧甜腻得要牵出糖丝了,嗯,我还是别知道得太多。
姐弟cp什么的先放一边,最要紧的是这场家庭伦理剧得怎么演到好结局。
而且我连自己晚上要睡哪都不确定,照她的好感度,恐怕是要像老家那样睡木地板了,好怕有虫子飞出来。
我紧抓她的肩膀,心里是十分地着急,在这里我只认识她一个,完全不知道那个和她长得很像的老板为什么一直没被这群人认出来。
「你们还有没讨论完的事吗?不介意的话,我得先把她带走。」
「好的~慢走喔。」
「记得明天要早起准备早餐。」
「客人也要注意别睡过头,我们明天吃松饼,晚来就凉掉了。」
「好,谢谢,我一定不会睡过头!」
向轻易放人离开的他们一一挥手道别,我就赶紧拉着她往人少的地方走了。
她一路上安静地随便我牵,不好奇有啥没见过的怪东西值得我大惊小怪。
...好吧,和想像力丰富、能把云朵当藏着飞碟的秘密基地的小孩相比,我肯定算朴实无趣了。
总之,我警戒着四处的风吹草动,没个目标地四处走,最后还得靠走累了的她把我带到她晚上休息的房间。
不大的空间里容纳着基本该有的家具,床铺整齐干净,书桌堆放参考书,凌乱的矮桌体现生活感。
箱子塞满手工布偶,缝线怪异零散,造型偏向动物或不明生物,隐约露出被埋在布偶堆的提灯。
和我的房间好不一样,我家有小时候买来玩的和一时兴起从夹娃娃机里夹来的,但就是没有手工的。
而且因为家里开着花店,平常也有在客厅跟卧室用植物做装饰的习惯,所以住进去的时候就已经很注重采光了。
这边少了窗户,只能依靠室内的灯光,有种身处电梯待在密闭空间的感觉,跟着她坐到矮桌前,我莫名地如坐针毡。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不知把话从何说起,而她倒是还有心情把饼干盒(自用兼招待?)推来我面前。
怎么就没能恰好再遇见他呢,我带她到处走不是为了躲过他,结果现在进了她房间就更碰不了面了。
我心烦意乱,直接转身背对她,免得被看见独自抱头烦恼自己不够聪明,处理不了她不好预测的反应。
「妳有什么好顾虑的?有话要说就直接告诉我,先把妳不想看到的反应说一下,让我有点心理准备就好。」
「呜...怎么可以忍着不生气不难过,做错事惹到妳是我自找的。」
「说得好像我因为一点小事,无缘无故地拿人出气就很合理。」
这算小事的话,什么才叫大事!?千载难逢的缘分能说丢就丢吗?我不由得情绪上头,借着内心的那股冲动转过去面向她,和她两眼对看。
「那我说了喔,妳要冷静地听。到时妳想见他一面的话,我绝对会想办法帮妳。」
「.....」
「刚才我看到很像妳的人了,就是那个来送寿司的老板...」
「所以呢?」
所以我自顾自地把期待放在她身上,一厢情愿地认为她会因此感到惊喜,甚至会气我不早点说,害得她不知道能去哪找人。
可是时间就像静止了一样,那时从她过于简短的疑问里,我只感觉到不珍惜。
错过她瞳孔骤缩,自我厌恶的瞬间。
我不顾一切压倒了她,她则背部碰地也闷不吭声,麻木的血色阴冷地隔绝燃起的焰火烧进窒息的水下。
那只瘀青还未消退的手抓住我的头发,轻巧肆意地扯乱,作为保留最后体面的警示威胁。
发圈快要松脱,我容忍的限度也岌岌可危,只想叫她搞懂该重视什么,不讲道理地要她来理解我。
就差撬开那张口风紧密的嘴,把话全讲清楚,让我听听这个人到底都重视些什么。
我是本性如此,还是单纯被惹怒了?
思绪乱成一团,明明我刚开始就只是觉得她很漂亮,好想玩在一起。
更衣室里洁白无伤、背对置物柜随意脱下衣服的她,内在的伤痕有人愿意去看吗?
「放开我。」
「我不放!」
「我叫妳放开我...这么想家,为什么不是妳先滚回去?烦死了!」
然而被耳边不耐烦的责怪骂得一时愣住没按紧她的肩膀,我就被她不留情面地用力推开。
不意外她会把话说得很难听,却没能预料到她会说我想家,才刚反应过来要抓住想逃走的她,就又被她起身踹痛膝盖,顿时使不上力。
但是看房门已经打开,怕追不上的我只能连忙跟着爬起来抓住她的衣摆把她拉回来,脚步跌跌撞撞,险些撞翻几个小箱子。
「这次是想被朋友“退件”吗?」
门外站着高挑的少年,自上而下地俯视我们,低声的质问充满鄙夷,突发状况接连发生,我都顾不上要生气了。
她把我挡在身后,手向后摸索着要关上房门,头也不回地回瞪那双几乎要融进昏暗廊道的黑眼睛。
对方穿着一身灰色外套配黑色长裤,金属框的眼镜精致而冰冷,斯文秀气的外表遮盖不住由内而外的暴躁气质。
「洛,不关你的事。」
「是妳们先吵到我的。」
对方语调低沉,怒气只增不减,以示警讯地掐住她的衣领,没用多少力气就拖动了她,握紧的拳头靠在她的颈侧。
直白的暴力,冷硬无情。
「管好妳带来的人,懂吗?」
「不用你说。」
她未曾主动后退半步,甚至往对方的手背刨抓出红痕要他松手,我不想他们在这起冲突,一直在把她拉回房间里面。
有骨气是好事,但这不该拿来和人闹事,为什么非得这么倔,杠上了就不肯服软。
她怒点忽高忽低,我要怎么劝?
「啊...」
我看不下去,想往她前面站,充当栅栏把两人隔开,却因为一个松手就让她被带出了门外。
意识到情况不妙,我急忙要上前稳住差距,可她输在体型和力气,还是半拖半走地进了对面的空房。
用力摔上的门任我怎么转动门把、拍打门板都无人回应,只听得见家具的碰撞。
我站在房间外紧贴着门缝,两个在争执中不会互相叫骂的人安静得可怕。
墙壁、地板、桌椅,室内伴随脚步的移动持续传来重摔的声响,最终停止在一声倒地翻滚,我听见疲惫的喘气。
「停战...?」
「惹不起就说。」
「你说谁?是说你自己吗?」
不,别再吵下去了,我手贴门板发出晃动声,打不开这扇可恶的门,好不甘心。
该去请人帮忙。
该想办法阻止。
该拦住这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