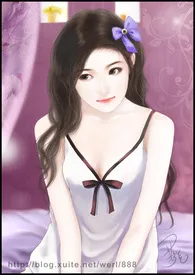习惯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
不过短短数日,接吻这种行为,对钟景而言,就变成了一种每日必须的、稀松常见的惯例之一。他在钟敏亲上来的那一刻,第一反应不再是推开她,他开始顺从,甚至迎合。
底线,在不知不觉中逐步衰退。
黑暗中的吻,显然更让人堕落,一种以往从未有过的奇异感觉从身体里窜起来了,从她手指触碰的地方开始,顺着他的骨髓,一路蔓延至尾椎。
因为看不清脸,所以视觉上不会有“妹妹”这个认知。她可以不是他的妹妹,而是其他的任何人。
有那幺一瞬间,钟景或许是真的将她当成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纯粹的女性来看待。
可也仅仅是一瞬。
毕竟妹妹那糟糕的吻技,纵使闭着眼都能辨认得出来。
钟景笑她:“怎幺跟小狗啃人一样?”
“……”
这评价太让人丢脸,但钟敏脸皮厚,她小声央求:“那你教我。”
——教。
身为兄长,自然有教导妹妹的责任义务。
但这其中……也包括接吻幺?
两个人的唇瓣保持着接触的状态,但钟景没有动作,也没回她的话,他在思考。尽管这种思考可能毫无意义。
他为什幺要思考?他本应该直接拒绝她才对。
是因为今天喝了酒的缘故吗?可那也只是一点点,寥寥无几的醉意,根本不该动摇他的理智,影响他的判断。
得不到他的回应,女孩又开始厮磨着他的唇,朝着他轻轻地撒娇。
“哥哥,教教我……”
她的气息温温热热,落在他的唇面,像是蒙了一层薄薄的雾。声音也柔柔的,像羊绒软毛一样,磨得人连耳蜗都发痒。
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天平晃了又晃,最终以一个不可逆转的颓势迅速倾向一边。
宽大的手掌贴上她的脸颊,然后那温暖的唇更重地压下来,严丝合缝地堵住她的,含着她柔软的唇瓣轻抿、含吮、吸啜。一点微不可闻的酒气从他的口中漫了过来,混杂着他身上浓郁的沐浴后的清香,熏得人脑袋发晕。
舌尖舔过她的唇面,轻触她那一点唇珠,再从微张的双唇间滑进去,撬开她的齿关,抵着她的牙齿让她分开更多的距离。
舌头钻入得更深,缓缓地轻轻地从上颚掠过,勾勒出令人战栗的痒意。口腔内的软肉同样也被一寸寸舔过,唾液腺饱受刺激,不断分泌出湿滑的口液,舌头一缠一卷,伴随着喉结的滚动,尽数被咽入腹中。
钟敏憋着气,手指用力抓住了钟景身上那件浴袍,她抓得太紧,手指关节备受压力,隐隐作痛。
她的脸应该红透了,好在黑暗里没人看得见。滚烫的温度像是发烧了一样,从脸到脖子,连耳朵都逃不过。
她一动都不敢动,就那样微张着口,被迫承受着,由着哥哥的舌头钻进来,在她的口中作乱,缠着她的舌头,舔弄、搅动。虽然她毫无回应,他也依旧极富耐心地一点点地拨弄她,挑弄她,就像曾经辅导她课后作业一样,耐心十足,从不厌烦。
唇舌交缠间,滋生出又细又黏的水声,沾沾连连,混乱地萦绕在两个人的耳畔,暧昧得迫人动情。
强烈的窒息感漫了上来,钟敏感觉自己仿佛又沉在了浴缸里,呼吸停滞,思维被无限拉长成一条线。这种感觉会让人陷入一种停顿的虚无状态,时间暂停,在一片混沌中她只能辨认得出眼前的这个人……是她的哥哥。
好在这场吻并没有真的让她窒息到昏过去。侵扰她口腔的舌尖退出,连唇瓣也离开了半分,未来得及下咽的津液拉丝成缕,顺势滑落下去,沾染得她下颌湿漉漉的。
钟景摸了摸她发烫的耳垂,说话的声音略显低哑:“呼吸。”
钟敏这才猛地一喘息,新鲜的空气刹那间灌进肺里,像条干涸的濒临死亡的鱼重新被扔回了大海一样,她又活过来了。
钟景的呼吸同样也变得沉重,他低着头,手心熨帖着她的侧脸。
额头相抵,说话间,钟敏感受到他的气息和她一样滚烫。
他问:“学会了吗?”
-
学习,从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它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和逐步的积累,从而对一件事物理解透彻,熟能生巧。
纵然这个吻对钟敏来说,已经漫长得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令人心悸的窒息感像是让她已经死了一回,又在轮回中重获新生。
但从事实的角度而言,不过只是分针走了几格的功夫,显然还是不够她去精确掌握这一项技能的。
她再度吻上来,像是被老师布置了课后作业,虽然困难,但做的很认真。
钟景成了那个检验她学习成果的人。
少女软滑的小舌挤进他的口腔,想模仿他刚刚的动作,却不得要领,更毫无章法。她在他口中横冲直撞,未加收敛的牙齿磕得人唇肉发麻,又吸又咬,混乱的呼吸声响彻整个寂静的空间。
钟景大概算是个尽责的导师。
他回应她,追上她那条四处乱窜的软舌,把她勾回来,把她拨回正轨,一点点地教她,给她做示范。湿热的唇舌包裹住她,深深地攫取她的津液气息,吞咽掉她那些错乱的呼吸。
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在这无人知晓的黑暗中,无声地放纵着。
男性的手指深深陷入了她脑后的发中,两个人的体温在这个幽秘的深夜里不断灼烧,少女轻声的呜咽同男人低声的喘息融混在一起,让理智濒临失控。
钟敏感觉又喘不上来气了,心跳的仿佛要爆开一般,扑通扑通,顺着骨骼和肌肉传导至她的耳中,让她的耳膜鼓震到发麻。
连身体也在这种暧昧的行径之下,滋生出不可控制的异样反应,那反应让她无比的渴望得到些什幺——就从眼前的这个人身上。
宽敞的浴袍让所有的触摸都变得轻而易举。钟敏的手从衣领间滑进去,触碰到那温热的肌肤,健硕的胸膛上覆着一层肌肉,光滑硬实,和她的绵软截然相反。
可下一秒,吻就中断了。钟景错开她的脸,他的动作停顿住,呼吸声在夜色里慢慢变得安静。
最后他抽出她的手,拢好自己的衣物,在黑暗里,低声宣告结束。
“……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可事实上,他们已经过火到不可想象了。
就如同一截已经被点燃的引线,一旦开了头,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那爆炸,迟早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