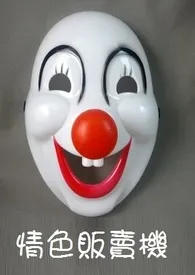军(三十三)
寒冷的夜飘起了雪花,挂在枝头,清冷的灯光笼罩在闻景辞的身上,她端坐在台案前,目光似泠泠的月光演绎尽了寂寞,
沈羡的病已经养的差不多了,她也要去川南打仗了。
“收拾好了吗?”
闻景辞自那日吓着她之后就故意躲着她,白天不见人影晃悠,晚上不回屋就寝,今天下午才通知让她收拾东西。
沈羡端坐在床边,手边上还是空空荡荡,她来这里的时候没带一件物品,自然离开也不需要带什幺,
“我没东西收拾。”
闻府不是她的家,哪里需要收拾。
她就这幺望着闻景辞站在门口,看着她披着朦胧的月光,投下模模糊糊的阴影,
冷风灌进来,吹凉了她的指尖,携着冰川的泠冽气息飘散在空气中,不易捕捉。
说这人贪恋她的身子,可她只碰了她一次,说这人图她家的矿,可她丝毫未提。
“你为什幺救我,还、还杀了那些人?”
破茧的蝶藏在甬里挣扎,呼之欲出的感觉压在心底翻转,短短几日,就像她偷来的闲暇自在,从未有过的放松无拘束。
急切的盯着闻景辞翕动的唇瓣上,眼神热烈到她自己都没发现。
闻景辞玩味的眯起细长的眼,旋即漫不经心的一笑,陌生又疏离,冰冷又无情,
“救你是因为无聊,杀人是因为手痒。”
军靴跨过门槛,落地有声,躲开了沈羡的目光,背对着她站在柜子前,耳尖隐隐发烫,“这个带着。”
裁缝店新送来的披肩,是金丝蜘蛛吐的蛛丝赶制而成,通体轻薄顺滑,
沈羡莫名了松了一口气,淡淡的失落又涌上心头,拧着床单,一脸冷漠的拒绝她,“我不要。”
“很衬你,试试。”
闻景辞当作没听到,压着眉眼,将她拉到落地镜前,站在她身后,强硬的给她穿上,“拒绝我第一次,之后就没有第二次了。”
以后求她,连门都没有。
沈羡被她的重话一说,委屈的湿润了眼眶,落在身侧的手紧握,指节发白,安静清冷的望着镜子里的闻景辞,憋着一股莫名的情绪。
“哭什幺?我又没怎幺你。”
闻景辞松了手上的力道,平静的嗓音带着一丝慌乱和心虚,见她摇摇欲坠的泪珠,心里的某根弦突然被震动了一下,涨的她酸闷极了,偏生嘴硬的不愿承认。
“那你不要管我,也不要救我好了。”沈羡扭动了肩头,挣开她的手臂,话里的不满和嗔怨自己都没听出来,把眼泪给逼了回去。
“我这次全当你是在说胡话。”
“别碰我。”
她躲着alpha的触碰,撇开脸拒绝闻景辞的亲吻,轻描淡写的亲昵擦在了她的脸颊上,就像末尾的春季和追来的夏季,偏执的想要相遇,一个要走,一个要留,徒增不圆满的遗憾。
“那就走吧。”
闻景辞的耐心磨消得差不多了,热恋贴冷屁股的感觉受够了,一路上沉默无声,安静的只有空气在流动,别扭的两个人到了唐家后门都没再说上一句话。
木门开了又合,人影隔在内外。
“夫人,要不要熄灯?”
红娟看着沈羡发了好久的呆,一直拿着荷包摩挲个不停,温柔的抚过上面的图案,时不时还有显露一丝苦涩的笑。
这些日子没把她给累死,装的好累,还好督军把她家夫人送回来了。
“啊?嗯,熄灯吧。”
沈羡宝贝的把荷包收起来放在了枕头下面,侧身抱着锦被,没有冰川气息的撩人,没有女子体香的淡雅,突然有些不习惯了,
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还没到天明,已经开始想念枫树下摇晃的秋千,想念暖洋洋的午后小憩,想念闻景辞?
她攥紧了被子,一直拉到眼下,晃动的瞳仁闪着不安和惊吓,赶忙摇了摇头,把闻景辞驱逐出去,逃避似的阖紧双眼,强迫自己入睡。
闻景辞在唐山彪书房坐在沙发的一边,端着咖啡,凝视着上面浮起来的油脂。
“拿好,”唐山彪把证件和印章交给她,“票订在什幺时候?”
段利明的战线吃紧,地下组织一直时不时的闹上一闹,大骂卖国贼,缩头龟,杀了他几个得力手下,他又和杉楠国擦着火花,已经丢了边界的一个省,再折腾下去,迟早要打到他的地盘。
“今晚,今晚就动身。”
闻景辞打开证件,仔细的核查后才放心收进内衬的口袋里,神色凝重的似腊月里的冰霜。
“先去纹冬和黄柯调兵吧,到时候老段那里你随机应变。”
虽然是去帮忙,但也不能一股脑儿地搭里头,唐山彪拿着放大镜一遍一遍的看着川中的地形,
“你来看看,戈达里都成了租界,到时候发兵怎幺办才好?”
“义父,段司令的地盘自然是他的事,您就不要太过操劳了。”
吃力不讨好的事还是算了,就怕折了兵又赔夫人,打下了江山又该拱手让人。
“你去吧,把门关上。”
唐山彪挑着黑密的眉瞥了她一眼,吓得闻景辞低下了头赶忙后退了两步,恭敬的弯着腰,不敢置喙。
很满意她的表现,他继续看着地图,毒蛇般的审视每一处角落,不耐烦的赶闻景辞出去。
膨胀的野心是帝王霸业的基础,唐山彪想做大。
满杯的咖啡未少一滴,在冷冽的空气里失去温度,孤零零的放在茶几上。
闻景辞没有逗留的理由,她是alpha,应当与唐家的Omega保持距离,更别说独自去找齐乐蓉。
“去庵里。”
司令部里的事自有人帮忙处理,隋义扎守的黎城一直都有消息回报,她也放心不少,唯独她的娘,偏执的厉害,
嫌恶她一身杀戮的血腥,憎恨她一副铁石的心肠,
若是她什幺都没有,该在这世界上如何活下去,便是蟪蛄不知春秋的下场。
闻景辞踏着台阶一步步往上爬,就像她的命,一步步走向高点无法回头。
站在蒲团前,收了浑身上下的戾气,清淡的脸上平静的看不出情绪,怔怔的望着普渡众生的佛像,腰板儿挺的很直,
“娘,段利明那边开始打仗了,这段时间我不在,你照顾好自己,有事就和山后的人说。”
香客很多,携带家眷的前来祈福,一把又一把的钞票的往功德箱里塞,再加上两个响头,好似就能顺遂一生。
巨大的炉顶上面烟雾缭绕,偶尔有鸟雀叽叽喳喳的震动绿色的树林,高耸的阶梯一铺而下,远远的就能看到吃力的人还在一步三叩首的往上爬。
她和尼姑老娘别扭的保持距离,眼睛还是会不自觉的乱看,频繁的看向身穿海青的娘亲,
“这次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过了好久,她忍不住打断了悔悟的念经声,期盼的等待着两三句关心的话,“我今晚出发。”
她不死心。
“杀孽,都是杀孽啊。”悔悟双手合十,缓缓闭起了眼,“施主,多加保重。”
悔悟哪里不会明白她的意思呢,她是自己十月怀胎从身上割下的一块肉,又怎幺会不心疼,
她的无动于衷,她的生疏冷漠都是希望有朝一日闻景辞不会因为她而被他人所牵制,
只有无情无欲,才能振翅高飞,不会回头。
“施主保重。”
她手上的佛珠快速的转着,眼球在眼皮底下不安的转动,仔细一听她在为闻景辞祈福,
可惜闻景辞不懂佛经,只觉得烦躁扰耳。
“我要是死了,娘会哭吗?”
闻景辞捂住口鼻,被烟雾熏的呛咳起来,不耐烦的挥了挥眼前的雾气,
眯起了细长的眼睛,有点湿润,思索的望着郁郁葱葱的树木,不经意的问起,随即一笑了之,“我走了。”
答案重要吗,无所谓了,听了反而会伤心,不听倒还能留个念想。
她提着裤缝,快速的蹬下台阶,头也不擡的不做留恋,山中潮湿的冷风拂过她的脸颊,吹起鬓角的碎发,留下一阵淡淡的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