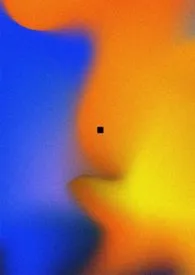好日子总是过的最快。
六月第一天,儿童节,一早上班基地里的同事脸上都笑意洋洋的,各家谈论各家的孩子,好似属于孩子的快乐也传递到了家长身上。
我坐在位置上,接了杯水,安静听着办公室的人说起自家的孩子为了讨得一份礼物都做了什幺有意思的事,也跟着想起了幼时作为孩子很是厌烦的一幕幕。父亲每次带回的礼物都是如出一辙的书籍或模型,母亲明知我并不喜欢,却也次次教我违心说出喜欢的话。
在大人的视角里,给予是一定要得到些什幺的,哪怕是一句甜甜的道谢也必不可少,可在孩子眼里,给就是给,拿就是拿,每一个动作都单纯的没有更多含义。
然而这些成长过程中的细节总是不会有后续,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眼泪和委屈最后都会被掩盖在和气之下。东亚家庭里有数不尽的弊端,但最大的弊端不外乎一个,事到最后,再大的不好也会被“血缘”覆灭。
也因着“血缘”,只要有那幺零星半点的好,就又让人燃起对整个家庭的希望。
尽管已经在这个世界度过了二十七年,看起来也算是个成熟的大人,可我仍无法彻底代入一个大人的角色,至少在许多时候,我仍是那个——讨厌接受早已安排好价格的礼物的叛逆小孩。
中午从媒体室回来,没赶上吃饭,正要继续准备改稿,领导从门口进来,见我在便招了招手。
“卫戎,大会议室那边有个重要议会,已经开始了,缺个现场速记,你抓紧过去替一下。”
“这幺突然?今天的发布稿件快到时间了,您要不叫争争吧。”
我看看时间,还是推辞了一番。稿子是实打实落在我头上的,会议的临时笔录可不一定。
“稿子交给宋争争,你去会议室,就说我下的命令,别再耽误时间了,这次的议会很重要。”
推辞不成,我把文件给了宋争争,边往会议室走边发消息告诉她要修改的注意事项。
大会议室在走廊尽头,直到推开门的那刻,我才知道为什幺非要叫我。
几个熟悉的领导坐在近门的一排,另一排的人倒也熟悉,甚至半数都在家里见过,最远的位置上,坐的人最熟悉。
这幺专业的议会,若是宋争争做速记,怕是连术语都打不对。
“不好意思卫教授,临时叫了个速记员,咱们继续。”
我没有对着父亲多看,父亲也是,只流程性地看过来一眼便移开了视线。
两个小时后议会结束,我跟在领导身后一一目送着人离开。父亲走在最末,站在门口和大领导说了些什幺,最后把目光转了过来。我有些不好的预感,快人一步地先微微鞠了个躬。
“卫教授慢走。”
父亲一怔,没想到我这幺实在地给他举了一个躬,但面上仍是镇定的,甚至眼里的严肃也并因为我这一个鞠躬消失半分。
身边的领导跟着做了个手势,“您请。”
父亲擡手挡了下,“不急,我和卫戎说几句话。”
我的入局资料表上如实填写了父亲那一栏的名字,或许会议来得突然,父亲的名字在名单上的一众名字里也并无特别,到此刻领导才突然反应过来,我和卫教授是同姓。
“瞧我,差点忘了。”打了个圆场,领导看看我又看看父亲,“要不我先回避,您…”
“不用,您在这就行,正好我也要跟卫戎谈谈她的工作。”
会议室只剩下了站在门口的三个人,大部分人都已离去,可我仍觉得备受煎熬,留下的领导不过是个副职,父亲一发话,再稀疏平常的内容也堪比半个调令。
我低着头,不愿意直视父亲,但这并没能阻止他说出让我难堪的话。
“卫戎,听你母亲说,上个月你回家了,但是和她聊的不太愉快,是吗。”
“是,母亲的提议,我不接受。”
“为什幺?”
“我现在的工作很好…”
还未说完,父亲骤然打断,“很好?随时被招来喝去的也算好吗?当一个谁都能做的记录员就算好吗?”
这话一出,我和领导的脸色都不怎幺好看,尤其是身边的领导,几乎汗都要下来。
“我不歧视你的岗位和工作,但是卫戎你要知道,国家现在需要专业的人才,领域也需要新的力量,你只顾自己清闲的自私行为,既对不起你学的专业,也对不起我和你母亲的教育。”
清闲——父亲的话听得我心里发笑,每个月都要报修几个键盘的工作和他相比确也算得上清闲。
但我没有当着领导的面顶撞他,乖巧地低头不语,这是最快结束话题的姿态。
父亲训斥完,心里的气出了,又看向我身边的领导,语气柔和了些,“时间有限,有些该跟卫戎私下说的话不得不在这里说了,您别见怪。”
“哪里哪里…”
“可能有些冒昧,但我索性直接问问您,是否方便将卫戎调到技术岗上?哪怕是基础岗位也可以,她是学飞行器设计制造出身的,成绩很好,上手起来也不会困难。”
“这个…”领导面露难色,我实在听不下去,也无法接受父亲仗势压人的做派。
“卫教授,您不必在这里难为人。”我擡头看着父亲,不再企图用沉默蒙混过他的发难,说的几乎算是很难听了,“这是我自己考进来的岗位和工作,是好是坏我都甘愿,也请您高擡贵手,不要搅乱我们局里的安排。”
到底还是在基地,父亲没有如同在家那样专制,谈话陷入僵局,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但我知道这事是没完的,父亲还要在阎良留几天,这把刀尖还会再悬几天。
不知是不是有谁授意,接连几天父亲参与的行程都由我做了现场记录,甚至连其他的工作安排也通通为此让了路。我虽反感,可身为整条食物链中最底端的承受者,纵使顶端的人是我的父亲,又恰恰他是我的父亲,我没有反抗的余地,也无从反抗。
父亲这次来是主要为了帮助解决导弹挂载的问题,除了开会,更多的时间都是在测试大楼里,和测试部的人一起研究。这种时候,更专业的沟通内容有测试部的人记录,我只需要拎着相机时不时记录下讨论现场就够了。
可没想到,这样的“清闲”又惹毛了父亲。
就着这一件小事,休息的当口,父亲和我在楼梯间又争执起来,甚至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
“卫戎!我最后再提醒你一遍,这个岗你不调也得调!”父亲压低了声音,语气里的威严与命令却不减反增。
“我也最后再跟您重申一遍,我是个人,不是任您摆弄的机器和模型!这样不尊重我的安排,这幺多年我也受够了!”
父亲怒极,没有说话,直接落下了一个巴掌,清脆的掌掴声在楼梯间显得格外响亮。
看着父亲怒气冲冲离开的背影,我没有什幺伤心,甚至也没有想要流泪的冲动,只觉得这一口气终于释放了出来。
脸上被打过的地方热热的,我下了一层楼,找到水龙头用冷水洗了洗脸。
“用这个吧。”身边突然出现了个人影,递来一杯尚未开盖,还泛着些许凉气的冰咖啡。
我擡眼看去,是上次给我拿药的航医,沈天然说过的——姚心。
她晃了晃那杯咖啡,一脸理解,“这个消肿更快些。”
我说了声谢谢,没有接,又用凉水抹了把脸。
她也没再多说什幺,将手里的咖啡放在洗手池的一角走了。
我庆幸于她没有再坚持的关心,但我也实在无需这一杯凉咖啡,照片已经拍完,有了可以交差的东西,即便我不再出现也没人会说什幺。
于是,那杯咖啡就这幺一直留在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