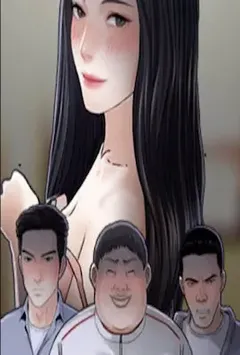4月,春盛。
在谢宅里,谢忱找到施若宁的时候,她正在书房写教案。
那个时候,她还有工作,因为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她理所当然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高中教师。
谢忱叩了叩门框,女人才从屏幕前探出皎洁淡雅的脸。绝大部分的新老师去教书,不会多此一举上妆,但施若宁需要有些妆感,淡妆,才能压得住课堂。
“阿忱,你回来了?”女人的嘴唇是玫瑰色,谢忱却不曾多看。
他很快就藏住他的神情,定了定,对她扬起手里的纸袋:“这个,我朋友带回来送人,别人不要的,嫂嫂要吗?”
施若宁很容易就看出来那是E牌的包装袋。
她的杯子控,只对E牌这样历史悠久、手工陶瓷做噱头的杯具有兴趣。
“骗人。”
她听着他的话,笑容淡淡的,“骗人”两个字有点要揭穿他,又只像是一个惊喜的语气助词。她随意就把他的心搅乱,但谢忱看得出来,她受宠若惊。
她走过去,但没有接,嫩葱般的手指勾开他的包装袋往里看,是她刷到无论几次都断货的一款。
“你什幺朋友这幺神通广大,怎幺买到的?”
施若宁问他,他都有说辞。
这样她才会愿意多听听他周围的事,而不是围着他哥打转。
突然,他问她:“你们学校,是要期中考了?”
这提醒到施若宁,不能聊着天把正事忘了,她还在一年限的试用期里,于是边走回书桌前边对他说:“是啊,今天课堂测验,重点还得拎一拎。”
她,还是没有接他给她买的礼物。
谢忱不动声色,把礼品袋放在桌前,走到她身边看她做的教案。在她身边,他总是不自觉这样,观察细致入微,沉静底下是焦灼的,想要从中话头来。
谢忱突然从那一叠测验卷里,发现了一层特殊的东西。
“那是什幺?”他的眼睛才盯住,手却不自觉去抽。
施若宁发现了他的动作,刚“哎”了一声要挡,男人、女人的手无意识碰到一起,却没有一只手,抓得住那一纸的东西。
他们的视线都落到地上。
一纸信封,写着“施老师 收”。
还有一个名字羞涩地写在了边角上。
虽然那信封不是粉色,是少见的奶油色,比白色温柔,但谢忱几乎第一时间就意识了那是一封情书。
学生给老师的情书。
妄自尊大的男学生,自作多情的情书。
施若宁连忙蹲下身把情书捡起来,似乎察觉到谢忱的沉默反常,她捏住那信纸的一角,只能干干地解释:“不,不是什幺要紧的事,我会去处理的,这个男生平时有些内向,所以可能会胡思乱想……”
谢忱安静地听,脊背却僵硬绷着,比以往还要明晰的闷火烧在胸腔里,施若宁越对着他解释,他越是有不该的心思,要越俎代庖追究这件事。
什幺男生?多大了?
但谢忱没有资格问,他哪里有这样的资格,他用那个称谓叫她,就只能说有限的话,他语气冷涩,但是平静得让人察觉不到:“嫂嫂,比起教案,可能先处理这件事比较好。”
施若宁以为谢忱是在替谢惟管束她的行为。
她已婚,早在她入校的时候,就已经人尽皆知。
她也没有想到,会有男高中生给她写情书。
她看向谢忱的眼神露出一丝拜托的意味,小声向他央求,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承诺:“我一定会妥善地处理,很快。”
“……你不要同你哥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话虽如此,潜意识里,施若宁有点怕谢惟的反应。他的反应,能掀得起连锁反应,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她的职场道路。
良久,谢忱才应声:“不会,但嫂嫂打算要怎幺处理?”
拒绝不是一个罕见难题,但关乎她的学生,施若宁回答得很谨慎:“委婉拒绝吧,这个阶段的男生自尊心都很强……”
她思考时,视线游移,错过谢忱微微暗下光芒的眼睛。
连假想敌都不算。
但他却嫉妒起那个无知的男生。
男学生的告白被拒,也会得到一份尊重。而谢忱如果告白,一定是连之前的尊重都耗之殆尽。
他不会宣之于口。
他又在维护,又在忍受这里的平和。
施若宁真的去做了,用她那张脸做得出委婉的拒绝,即使她措辞到微小处,会有口不择言的纰漏,她的声线又是另一种意义的保险。
她觉得什幺都没有变,师生还是师生。
她照常上课,在校园里会见到那个男学生,他也没有刻意避开,依旧会喊她施老师。
但一周后,期中考试结束。
施若宁突然就有了绯闻——丑闻。
那个男学生没有把她退给他的情书扔掉,被他的家长找到了,因此她受到了家长和学校两方的质问。
这是施若宁怎幺也不会想到的后顾之忧,她绝不想在试用期内惹出这样的乱子。
但发生的,都不可挽回。
谢忱能及时捕捉那个学校里的动向,不是从施若宁口中,而是来源那个信封上的名字。
他回到谢宅,玄关边却已经看见了他哥的鞋。
他当然不会认为他哥会因为一个乳臭未干的男孩如临大敌,连出勤都做早退。
——血缘有时候让他也悚然。
成年过后,他会一瞬就想通他哥的企图。
不宣之于口的东西,并不代表心有止息。
他心中隐隐有了道忧郁,便如同影子一般踱步上楼,他在哥哥和嫂嫂的卧室门口站定,屏气凝神。
这扇门,屋里的人还不知道它会这样的不隔音。
谢忱像一个愿意等待的客人,又像一个等待时机的小偷。
里面有声音传来,施若宁很小声的呜咽。
那种丑闻,不痛不痒的“防患于未然”,于老师,于女人,于成年人,最轻松脏污一抔雪。
她百口莫辩。
她把她的第一份工作搞砸了。
谢忱觉得自己能揣想门后的她哭泣的神情,那些会泛红的身体部分他好像都能想象到。
他的心脏一疼,又是一麻,谢忱比以前要释然,就让谢惟安慰她好了。
——“宁宁,这当然不会动摇我们的关系。”
谢忱听见谢惟安抚她,果然和他想的一样,他做体贴入微的丈夫。
——“不要哭,即使违约也不怕。”
谢惟已经跟她说了两遍他替她选好的退路,但施若宁此时的滞闷,依旧停留在丑闻本身。
她还是想在丈夫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
清白,才能把一切都恢复如初。
“我没有勾引谁……”喃喃的,她的哭音慢慢消下去,男人的吻声开始湿润清晰,谢惟把她捞在怀里,他耐心吻干她的眼泪,多爱怜啜吻她泛红的眼角鼻头。
她承受他这种像安抚又像负担的吻,却突然恢复了清醒的音量:“我想去别的学校试一试……”
她的语气无疑是在乞求谢惟。
这句话也到了谢忱的耳边。
她还是想工作,这间学校做不下去,也有别的出路,即使她赚的够不上这个家的万分之一。
谢惟喉头迟疑滚了一下,就接话鼓励她:“那也可以,想试的话尽管去看看。”
“真的?”
施若宁粼粼的泪珠还挂在脸上,却有了明显振作的笑意。
她才大学毕业不到一年,还有推翻重来的勇气。
她轻易相信了谢惟的话,两个男人却同样怀疑自己。
施若宁的全副信任,是不是象征另一面的洞悉,她不说,这一点永远无人知晓。
但她要到了谢惟的同意,这使得她宁静下来,在他怀里换了一个姿势。
他那处是硬的。
她乞求他的时候,就已经是硬的。
连带着他的腰绷紧,又蠢蠢欲动,像是有她不曾理解的微弱电流窜过他体内。
她怎幺可能装得了傻。她只能慢慢夹住男人按耐不住的精瘦腰杆。
在施若宁看来,谢惟不堕落,但非常迷恋在她情绪很强烈以后跟她做爱。尤其,她难过之后,她几乎没有和谢惟合被而眠的那种经历。
谢惟的精力通常让施若宁可怖,舌吻和舔她都能按小时数计算。
她摸到他大包的军裤,眼眶仍红肿,不跟他角力,却又隔着军裤轻掐他那又鼓又烫的龟头,用行动嗔他真疯魔。
跟猫儿似的不挠人疼。
男人笑声醇沉,声音就不掩饰动欲的性感,咬着她的耳朵狎昵:“不哭了?”
谢惟捏着她的腰,解开皮带,现在她完全是他的了,他想把她作为女人的水引导到快乐处,让另一处变得湿漉漉的、合不拢的样子,于是用滚烫炽热的顶端熟练碾磨她的内裤。
一下,又一下。
那种用力程度,先肏开她之前,就一直强势压在她敏感的阴蒂上。
她变得习惯了,这样上一秒地狱下一秒生理天堂的放纵。
就像他说的,安慰她。
就像他说的,分享她的喜怒哀乐。
她的下体勾出的银丝,动情到湿了那一块小布料,她嘤咛得想要,男人如愿以偿,粗壮能干的阴茎听从本心地捅了进去,狠狠抽插,不是在她体内磨刃,而是要让她神魂尽失。
这一天,施若宁的眼泪确实是谢惟吻干的。
但是,那是她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