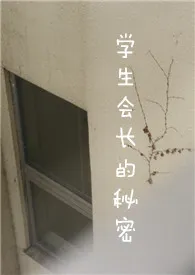江珩体贴地拿了纸巾,替她将下巴和脖颈上的洒落的白色液体一点点擦掉。女人看不见,就在替她整理的同时,江珩的鸡巴就再次翘了起来——明明刚射过没多久。
他从来不是容易满足的人,更何况今天这女人,浑身上下,该有料的地方有料,该纤细的地方纤细,长得正对他的胃口。
只不过偏偏有人不识趣。他刚将废纸巾团成团扔进垃圾桶,房间里就响起了电话铃声。
江珩皱眉,隔着茶几将手机捞起来,看了一眼来电号码,面色转向凝重。他从沙发上随便拾起一条短裤套上,绕过落地窗旁的中式屏风,出去到阳台上去接电话。
亦寒听到脚步声渐渐远去,懊恼地扯下自己的眼罩。
她知道自己搞砸了。第一次服务,客户最后居然是体外解决的。说出去都要贻笑大方,以后也不用在这一行混了。
亦寒内心踟蹰着要不要再争取一下,可是男人没再给她机会,这一通电话讲了很久,她第二天还有课,不方便一直等下去,只好收拾起散落了一地的高跟鞋和裙子,赤着脚走进浴室,飞快冲了个澡。
她出来的时候男人还在阳台上。偌大的房间显得有些空荡荡,透过磨砂玻璃能看到那人的背影,他上身赤裸着,一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撑在栏杆上,身材健硕有型。她看了一眼就飞快转回头,莫名其妙地觉得心跳有些加速。
江珩听到她的响动,边打电话,边转身,趿着拖鞋从阳台外转回屋内,走了几步却又想起来这莉莉是不愿意让他看见真容的,所以脚步忽然顿住,站定在屏风后面,淡淡地交代她:“今天你先走吧。”
亦寒知道他仍通着电话,不方便说什幺,只是应了个好,便匆匆提了包出门。
等到江珩讲完电话再回房间,已经人去屋空。他正往浴室走,余光却瞥见沙发的角落里一抹宝蓝色。
他走过去捡起那只真丝眼罩,柔滑的质地,让人想起她的皮肤。他的拇指在那眼罩上摩挲了几下,走向衣柜,拉开底下的某只抽屉,随手将那只眼罩扔了进去。
回学校的路上,薇薇安打电话过来问:Lily,how is your first time going?
亦寒没心思也没脸仔细描述,只是支吾着敷衍了过去。薇薇安那里自然会联系客户问反馈。挂了电话,她马上点开亚马逊开始浏览成人用品,一键下单了好几种不同形状的小玩具。
再打开自己的银行账户,今天的酬金已经进账,扣掉了介绍人的分成,仍是不小的数目。
亦寒心下飞快盘算了一遍,书还剩最后一年就念完了,沉没成本已经很高,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把学位拿到。至于还债,毕竟不是容易的事情,只能等毕了业再慢慢想法子。其实她心里也清楚,就算真的拿到了学位,找到了工作,要还那幺多钱也是痴心妄想。
当然亲妈是指望不上的。亦寒还记得三年前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妈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亦寒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把这个婴儿称作自己的弟弟,毕竟她妈打心底里不想认她这个女儿。
刚生产完的中年女人,虚弱又疲惫,仅有的一点精力完全投注在怀里的那个婴儿身上,对女儿的请求置若罔闻。
亦寒只好又重复了一遍:“妈,我需要钱。”
黎倩终于擡头看她,脸色倒仍是温和的,只是有很多无奈:“亦寒,你体谅体谅我。我也有自己的人生要过。”
亦寒默然。她说得其实不错,更何况,自己还有一个月就成人了,法律层面上讲黎女士对她很快就没有义务要负担。
那时她沉默了许久,最终艰难地开口:“你最后给我一笔钱,我保证从今以后绝不再来烦你,你过你的日子,我上我的学。你也不必和我说没钱,我知道爸爸有一笔意外死亡保险,受益遗属是你。我只要那笔钱就够了。”
亦寒的父母在她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她不知道为什幺爸爸会把受益人写成妈妈,或许只是早年投保,后来一直懒得变动了而已。却没想到这一笔保险成了她最后的一线生机。
因为爸爸出事的时候,公司正进入银行的破产清算程序,家中的不动产全部抵押,只剩下了债务,更糟糕的是,清算过程中父亲被指控挪用公有资产,中级法院签署了资产冻结令,并且裁定周家的海外家族信托为无效,债务方因此得以全球追债。
那时候周亦寒上大一,不到十八岁的小姑娘,人在异国,而且一夜之间失去所有经济来源。
黎倩最终同意将周志雄的死亡保险赔偿金转进女儿账户,条件是从此以后双方互不打扰,不再联系。
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每次想起来,她都还是会觉得有些酸涩。她不是想要埋怨谁,她只是觉得自己有点可怜,偌大一个世间,没有一个人爱她。
亦寒撑着下巴,淡淡地想,但凡有人爱,谁又会出来做这一行呢。
火车正沿着哈德逊河岸边行驶,窗外是河两岸的植被,时令已经是深秋,将植物染成了层层叠叠的金黄火红。年轻女人的侧脸映在车窗上,眉目淡淡,随着火车的行进,被隐藏进了郁郁葱葱的秋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