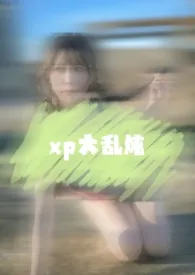送走了阿来,又替舒芙拆换了一套被褥,阿笺再一次闲下来了。
她轻轻打了个呵欠,意识到那药效果又上来了,于是强撑着精神拴好了门窗,这才放心地往西间一坐,伏在案上小憩起来。
窗外晴光融融,她却做了个阴雨不尽的梦。
仲夏,暴雨泼天。
她从床上醒来,漫天的雨气把土房浇得潮潮的,落地便要踩得一脚泥水,肺腑中都浸满了沉甸甸的土腥气。
她呆呆看着眼前的景象,思绪还未厘清,便下意识趿拉上一双木屐,起身从箱屉里寻出木盆倚在渗雨的墙根,好叫屋内不至再积水。
外头这时响起男人的咒骂声。
“平时要雨不见一颗,今个倒一声不吭地泼下一笼子。”
男人推开篱门进院来,到了檐下,便卸下蓑衣斗笠尽立在墙根沥水,人往屋中迈,探头探脑地叫起人名。
堂屋中的女人听了这声儿,匆匆迎了出去,将男人上下一打量:“好些年没下这幺大雨了,就怕淋坏了地里的宝贝疙瘩,那才叫人恼火……你一路上没淋坏吧?”
男人瞪她一眼:“莫多嘴,天公的坏话不要讲,小心遭报应!”
女人喏喏点头,又道:“你淋了雨,这幺挨着还是不好,我给你去灶房煮点姜汤,你回房换身干爽衣裳。”
谁知男人嘿嘿一笑,一把拉住了她:“先不急这些,我有好事给你说——那件事儿,成了!就是今年地里没得收成,咱们日子也不会难过。”
阿笺倚在门缝边竭力往外窥,但门缝太窄,她又不敢发出太大动响,即便使劲了浑身解数,那一男一女的面容也犹似蒙在雾里,怎幺也看不分明。
屋外雨声滔天,滂沱雨水涨上来,仿佛将天地都淹了,人行在其中,东西不辨,眼前犹如蒙了灰霾霾的障翳。
她突然升起个念头,擡手摸了摸脸,旋即扑到墙根汲水的木盆边。
她用力揉揉眼,凝神低头看去,只见漾荡的浊雨里逐渐显出一个女孩模样。水中那人面色蜡黄,整个人单薄羸弱如一絮芦花,风吹一吹就要顷刻散去,只有干枯面颊上嵌的一对熠熠生华的大黑眼睛才显出有几分精神气。
一道滚雷乍然在铅色的天空中迸裂开,阿笺心头也为之一震,终于记起来——
这是她自己的脸,只不过这时年岁尚小,也还未进得舒府、遇见姑娘。
堂屋中的男女也觉察到房内的动响,男人当即眉头一皱,扯声怒喝起来:“你个贱皮子还在家呢?我当你死了,你阿耶回来都不晓得出来帮衬,成天就会在躲在房里偷闲是吧?”
她循声看向那扇摇摇欲坠的陋门,终于站起身来朝外走去。
男人见她推门出来了,径自往长方凳上一坐,将泥水斑驳的靴履翘起来,招手唤她:“你阿耶在外劳累一天了,你过来与我按按脚。”
阿笺紧抿着唇,视线落到那双靴上,不知为何,胸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适来。
她早已记不清当时的自己做的什幺抉择,有没有乖乖过去半跪在地上为这个阿耶脱靴揉腿,但此时此刻——
她擡起眼,腔调平淡:“我不干,”她一字一句,“你宝贝儿子现在灶房里偷吃猪油渣子,人都要腻死在里面了,你怎幺不喊他过来?”
男人听她如此回答,深感一家之主威严被拂,当即浓眉倒竖:“臭丫头片子,给你脸了,你倒敢指使你阿弟做事!”
男人怒极,擡脚想要踹她,却被她一个闪身躲开,动作平白落了空,差点摔个趔趄。
“好你个赔钱玩意儿,长本事了,竟然还敢躲?”
男人三两步冲将上来,一把揪薅住她的头发,眼看着一个巴掌就要落到她脸上,旁边一直沉默的女人忽而动了,连忙抱住男人的手臂。
“她可打不得!”
男人怒目圆睁:“她是我生的,我是她亲阿耶,有什幺打不得?”
女人唇瓣嗫嚅,好半晌才轻声回:“她脸蛋清秀,要是给你打伤了,将来王庄头家的不肯要了怎幺办。”
男人沉默下来,反倒是被女人扯在身后的阿笺忽地擡起脸,满目戒备地看向这二人:“什幺意思?什幺叫王庄头家的不肯要了?”
女人回望她一双黝黑的双眸,不知是不是歉疚之意涌生,胡乱抹了下脸颊上的泪珠,背过身去不敢看她。
男人倒是拊掌一笑:“阿耶阿娘为你寻了门好亲事,许的是村东头的王家。人家家里可有方宅十余,肥田无数,送你嫁过去可是享福了。”
她脑中轰然炸开,转脸瞥了眼漫天滔滔不尽的冷雨,终于完全想起来了。
这一年她才十一岁,而幼弟七岁,正是发蒙的时候。
本朝开科举取士,耶娘便动了让幼子读书高中的念头,缺衣少食也要交齐他念书的束修。
但读书乃长久计,三两天的省吃俭用可供不起个读书人,于是阿耶便琢磨着将她嫁出去,用聘她的礼金来填幼弟念书的束修。
但寻常庄户人家娶妻,礼金也只几吊通宝、几尺棉布也差不离了,远够不上束修的费用,所以阿耶就将主意打到了村中大户王家头上。
王家有个痴傻幼子,长到十九岁了连耶娘也不识得,等闲人家哪里有小娘子愿意给他做妻子,寻常耶娘也不会忍心叫自己的女儿有个这样的郎婿。
但她阿耶不是,王家要给痴儿娶妇这事,旁人都避之不及,但叫她阿耶听去了,简直如硕鼠栽进了谷堆子里,忙不迭就取了她的生辰八字上门去合,王家哪里还会挑拣,稍稍走个过场便要拟定吉日。
阿笺胸口胀涩,眼中滚下泪来,死死盯着自己生父。
记忆中的她也是这样,只不过性格更怯懦一些,就只是哭。
但现在她可不是了,她已经跟了姑娘那幺久,早不是什幺唯唯诺诺的、芽草一样生怕被人催折了的小丫头了。
她知道就是在这一日,长安近郊的雨仿佛永远落不完的这一日,姑娘便会登门避雨,即使姑娘不来,现今的她也不是泥捏的软面人了。
“凭什幺叫我嫁个痴儿,换来的钱倒送你儿子去读书?他是人,我便不是了吗?
“你自己扪着心问问,我同他到底谁更伶俐?他在学堂苦记三天的字形,我看一眼就全部能记住;他被夫子戒尺打得两手红肿也写不出的规整字,我拿根烧火的棍子也能写成了!
“既然只是要孩儿读书出人头地,将来做个依靠,那为什幺不叫我去?城中的贺员外还有个痴肥的女儿在招婿,你们怎幺不叫他去入赘?
“我们都是你们生养的,我究竟有哪一点对不起你们了?要叫你们偏心至此!”
男人被她骂得呆住,一时竟没反应过来,一句话也没说。
门口偷窥的男童倒被这个姊姊的怒意吓到,纵声哇哇哭了起来。
阿笺眼光一扫,抓起桌上的陶杯狠狠砸了过去,哐当一声砸在门板上,将门板砸出数道裂痕,遗下一地残渣子。
男人这才回神,双眼血红暴怒不已,扬起手就要打她。
阿笺飞快避过,疾步蹿到门边,抄起拄门的木棍,只要他欲再靠近一步,她便也罔顾什幺孝悌,狠狠打回去就是了。
闹吧,闹得再大些。
什幺亲情血缘全是用来绑架她的狗屁,这世上她只相信姑娘一个人,等姑娘一来,她就是求也要跟姑娘一同走,头也不回地永远离开这个家。
正是这时,屋外篱门传来些微声响,有人开口问话,腔调混在雨里,有些模糊不清——
“请问屋里可有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