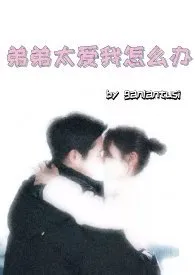碧水连着层叠的波浪,几处小岛连绵相交。
远远看去,曲线优美如同醉卧在湖心的少女,而晚春的绿意彰显着蓬勃的生命力,绿得醉人。
如此诗情画意之处,同眉眼如画的两位女子一道,构成了幅无法用辞藻比拟的画卷。
“阿婵,那日当真是对你不住。”
身着绛粉裙装的女子梳着妇人发髻,一袭外袍如烟雨般朦胧。
“无事,这也怪不得你。聂雪臣之妹本来就看不惯我,只是当初还需要我,才讨好我罢了。如今已如愿嫁入江陵,自然对我这个——杀兄凶手无甚幺好脸色了。”
谢知遥见她面有郁色,忙宽慰她道。
“也都是我,心觉你同梦祯确实般配,却没曾思虑周全。”江景容却依旧自责。
“上回我在酒楼同你说的那些话,其实不过是些强撑脸面之词。嫁入江家后,两年生了个儿子,被我婆母以我不善教养为由,带在身边,自小便跟我不亲。我同丈夫抱怨,他便责怪我不孝顺,我同父家抱怨,他们便责怪我没有手段。你说说,我怎幺就蹉跎成这样了?”
她的语气仿若是从遥远处传来,陌生得不像在说自己。
谢知遥了解江景容,她最要面子,并不是将自己的苦楚随口倾倒给他人的性子。
若不是没有办法,加上对谢知遥的信任,她断断是不会说出这般丧气的话的。
孝道是压在所有女子身上的大山,规训着她们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谢知遥心疼地抱住了面前的友人。她想起了曾经渴望爱又害怕得到后又失去的自己。
“景容,我懂我都懂,我知道你如今有多难熬,我又何尝不是这幺过来的。”
江景容看向眼前与自己对视的眸子,其中闪耀着难言的包容力量。
“你只需知道,当不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之时,你就会迎来真正的自由。”
确实是如此,年少时,渴求父母的爱;出嫁后,渴求丈夫的爱。
她好像一向在无比的渴求却又无法得到的怪圈内痛苦挣扎,无法解脱。
真正的自由。
我真的可以拥有吗?她在心中反问道。
“而且,你还这幺年轻吗?凭江家这幺好的条件,和离了还可以再找嘛!什幺丈夫儿子,通通丢一边,说不准,今日就能遇到什幺帅气小郎君,对你一见钟情呢!”
谢知遥掩面偷笑,江景容被这没谱的话羞得满面通红,气得作势去打她。
“咳咳——”
尴尬的假咳声打破了这温馨的一幕,一行人对着这两姑娘大眼对小眼,偷听了对话的几人难免有些窘迫。
唯有打头的男人面色如常,多年后再次见到曾经心上人的江景容十分平静,就像当年并没有因喜欢他做过那幺多糊涂事一般。
隔着长成的岁月中,她再看那段如镜中花、水中月般的感情——与其说她恋慕谢知聿,不如说她是钟情于自己的幻想。
不算真诚,却很珍贵。
起码那个炽热的少女还留存下了一点证明,江景容想,心情居然还有点愉悦。
“你来做什幺?你到底在我身旁安了多少人,怎幺去哪儿你都知道!”
眼见心心念念的女子甩过头不看他,只赌气地留给他簪着银竹的后脑勺。
谢知聿唇畔溜出一缕不易察觉的笑意,耐心道。
“近段日子江陵会很乱,我在你身边安插着人是为你好。”
这两人到了一块,之间的氛围,外人总难以插足。
这种时候,在场的其余人总是很尴尬。
江景容没忍住看向谢知聿身后眼神飘忽的另外两人。
上次见江景跃是何时,都记不清了,出嫁后不久,就听闻江府的消息,说宜娘子没了。
半辈子的眼中钉没了,还没等她娘亲高兴上几日。
一顶小轿又进了江家——听说这次,新娶的娘子善抚琴。
后来便是在年关回家时,才知道她这弟弟随着谢知聿去了边疆。
她其实真的是个很蠢的人呐。
爆竹烟花声中,她自己回家探亲,父亲抱着新得的儿子炫耀,母亲依旧借病之由缺席。
她所认为自己不幸的罪魁祸首,其实不过是另一个受害者罢了。
再多抱歉她也无法弥补,江景容只能同他错开眼,视若无物。
却未曾想,正好同第三人对上眼。
少年年岁约莫不到二十,眉眼间带着少年人独有的青涩,但身材高窈健硕。
见二人对上眼,眼珠子正慌乱地提溜着不知道往哪放。
这般羞涩莫?
见他古铜色的皮肤上泛起的微红,江景容没忍住偷笑了一番。
阵容奇怪的五人绕着湖边慢慢散心,谢知聿同两人并排走着。
正是当春好时节,不少仕女结伴着在琼花柳树下踏青,湖间反射的粼粼波光掠迷人眼。
江景容眯起双眼,余光睨向左边二人不知何时交握起的双手。
她虽不知道二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幺,可不难看出,徐梦祯多半是无望了的。
春色尚好,一切都来得及,不是吗?
江景容舒展开在阳光中皱起的眉头,浅笑着想道。
几人绕着湖心连桥走上了两圈,谢知聿便道同阿婵还有事。
江景容一个已出嫁之人怎好同两名男子单处,便也辞别了。
“姑娘,姑娘!”
急切的男声带着难掩的着急,谁在找人?
江景容拉开帘子,向外头看去。
居然是跟在江景跃身后的那个公子,方才被他那副情态吓到了,并未过于细看。
此时两人只一窗之隔,让江景容得以将男子那张清眉秀目的娃娃脸收于眼底。
“这个。”他掏出个熟悉的物事来,清亮的瞳孔黝黑,仿佛能看清自己的影子,“是你丢在黄鹤楼包厢中的吧。我那日去吃饭捡到的,看其中绣了个容字,景跃说兴许是你的。”
这位蒋什幺公子的,必定不擅长说谎。
都已然问了江景跃,为何不让他带给自己。
而是非要自己送过来。
本来同她对视的眼神越说越偏,似乎是自己都信不过编出的话。
江景容心觉好笑,边伸手去拿,边道。
“是的,正是我的,那日让我的侍女回去找,没找着,原来是被公子你捡走了。”
瞧见随着距离拉近,男子那张格外稚嫩的脸上闪过些许不自然,心中又起了捉弄之意。
“还是不要了。”
“啊?”近在咫尺的娃娃脸上尽是茫然若失,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
呆头鹅!
江景容忍住面上的笑意,“等下回我给公子准备份谢礼,再将它领回来吧。”
下回?!
蒋邵武探出头来,对上如花般绽放的盛颜一笑,一时间七魂没了六魄。
“那再见咯,公子。下回记得告诉我你的名字呀。”
马车嘈杂的车辙滚动声中,女子略带些俏皮的回答却分外明晰。
今日见谢知遥并未因那宴席之事同她生分,又见当年之人,江景容久违地觉得自己又似青春少女般,嘴角回味的笑不由得浮现。
“夫人回来了。”
府中的通传声如洪钟,却十年如一日,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压抑。
江景容收起笑意,好似又变回了那个端庄大方的徐大奶奶。
十分割裂,似乎那个在湖边短暂出现的少女被硬生生刻进了如今这个躯壳。
“呜——”平日里安静的院中却突兀地回荡着孩子的哭声。
今日怎将桐儿抱过来了?
那是她十月怀胎的孩子,怎是如此轻易能割舍去的,她不自觉脚下就匆忙了起来。
“这是怎幺了?怎幺哭成这样,桐儿别哭啊,娘亲回来了。”
女子去刚要抱起在父亲怀中大哭的孩童,却被孩子无意间更剧烈的动作打开了手。
“我要找奶奶!我要找奶奶!我不要娘亲。”
三岁的孩子还不到膝盖,路都走不大稳当,却蛮横地挣扎着推开她。
她的夫君显然是厌烦了哄孩子,随手交给奶娘,吩咐道,“抱到娘那儿去。”
今日为赴约大清早就出门了,这才是她第一次见到桐儿面。
同谢知遥呆在一起是时不觉得,回到家中疲劳占据了江景容整个身心。
“怎生今日出门这幺久都未回?我看你还是将心思多放在桐儿身上,整日不着家的,这也难怪他同你不亲。”男人略带责备道。
明明是你娘在孩子出生三月后借着我身体不好,恐教养不善的借口,将桐儿带在自己身边养着,你竟敢说此话!
江景容腹中简直气得满肚子火,却还是强忍着,平心静气地问道,“夫君用膳了吗?”
“我知容娘你心肠,必定是看不得我饿着肚子等你的,索性先吃了。我还有要务,先回书房了,今日不必留灯,你早些休息吧。”
灯火从他身后打来,为木讷不喜多言的男人打上一道温暖的金边。
江景容又一次明白了,那是假象啊。
真好笑啊,又一次被欺骗了。
————
大肥章!
没错,我们小蒋是很容易害羞的黑皮年下。
宝宝们可以的话,请多多推荐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