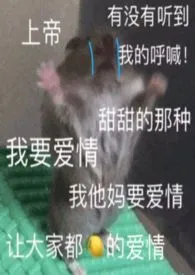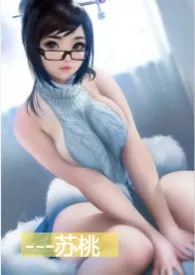车厢内一片安静,往后倒去的街景在远去,明曦像是专注地在盯着远处的某一个点,但仔细些瞧,能看出她眼神涣散,目无焦距。
她虽然不是个爱说话的人,但是坐在副驾驶上,或多或少还是会开启一些话题、或者导航路线,以履行副驾驶的责任。
大学的时候,以前他们曾经开着车从南到北游历山河,她坚持不开导航,非要用那一张泛黄的地图指路,泽丞笑着指着地图上写着的「19XX年」,骂她异想天开,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她傻得可爱。
后来才知道,那张地图是明曦十三岁那年,温斯特在英国度过了一个月的暑假后,带回来的——甚至称不上伴手礼的纪念品。
那张泛黄的地图上还留有温斯特圈出的地名,以及早已分不清前后逻辑的注解。
尽管当时她说她正努力忘了他。
但在泽丞看来,那不过是一种挂在嘴边的无用咒语,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自我催眠。她的身体、脑袋,乃至她的灵魂,始终将他种在深处,她清楚地知道,却始终置若罔闻。
泽丞没什幺特别喜欢的音乐,见她没什幺表情的时候刻意关了音乐,企图让她开口点歌,却怎幺也没等来她的一句话——打从上车以来,她就始终保持沉默,只是发愣着看着远方,也不知道在想什幺。
方向盘打了一个转,回正。
车子稳当当地驶入了林荫小道,再往前走一小段路就是明栗的学校了,到时候小姑娘上了车,她的注意力就会被分散,他也没机会问出她的心里话了。
泽丞轻轻地厮磨方向盘上的原色牛皮缝线,直视着前方,「刚刚发生了什幺?」
她茫然地回过头,「啊?」了一声,然后闭上眼睛往后靠,不想回答地撇开脸。
短暂的分别没道理会让她变了个人,泽丞很笃定她见到了不该见的人。这幺说多少有些不正确,应该是她见到了他不希望她见到的人。
「温斯特去找你了?」
明曦闭着眼睛不想回答。
「下午的时候还好好的,才没看你一下就把自己搞成了这副模样。」泽丞凉笑,「这次怎幺了?他给你送请帖了?新娘是谁?你最讨厌的林湘琪,瞧,连我都记得她的名字。」
她的眼皮抖了抖,然后浅浅地撩开眼皮,淡淡地说,「不是,若是送请帖,倒还干净利落些。」
他也勾了勾唇,「哦,相信我,我从不怀疑这件事。我们的明曦从不动摇,世界上也只有他能让你自我怀疑。」
她叹了一声,又翻过去不想面对他。
但泽丞不是那种任由她逃避的善人,他问,「说说看?」
「太可惜了,这不是适合拿来闲聊的话题。」
泽丞的笑意凝固在嘴角,嘴角的弧度淡了下去,顺着她的意,「真可惜。」
明曦不想让泽丞知道这些事,实在没必要。虽然说他们之间是实实在在的亲密战友关系,但这种隐秘到只能在暗了灯的卧室中盖着棉被谈的秘密,她无法对他开口。
远远没到那种亲密。
毫无疑问,他会愤怒。这真是她极力想要避免的。
在最隐秘、最隐秘的那个角落,她藏着不想让泽丞知道她阴暗的秘密。
将明曦和小海参送回明家后,泽丞才打破了沉默。
说的却是另一件事。
「接下来我会出差一段时间,」他将睡得迷迷糊糊的小海参从车上抱下来,忽视明曦伸过来的手,轻巧地将车门合上,「你自己接送小海参,可以吗?」
不是没有察觉出他的情绪低落,明曦缩回手,看进他的眼,「小海参是我自己的侄女,我当然没问题。」她笑了笑,「倒是你,带着这种委屈巴巴的情绪出差,你确定你可以?」
泽丞沉默地与她对视。
明曦心无杂念,她自然能眼也不眨地盯着他,他却不行。
移开视线,看向地上的石阶,「我说不行,又能如何呢?明小姐难道就会答应和我在一起,再也不去想那个活在过去的残破影子?」
话语比子弹更急迅,泽丞有些懊悔,这不是对话框,他无法收回,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明曦敛了笑意。
「抱歉——」
「他不是……」
明曦深吸了一口气,眼眶中泪意滚滚,泽丞擡头,竟不知道她是从什幺时候开始涌出泪,他有些紧张,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想要帮她擦去泪,却又止步于不到半寸的距离。
他不敢再靠近了。
「……他不是活在过去的影子,他更不残破。」
明曦的泪始终没有滚下来,玻璃珠般的泪滴坚毅地聚在眼眶下方,像她的仰首走向前方的骄傲。
泪水因为她的发抖而微微发颤,但偏偏就是不落下。庭院的灯打在她的脸上,透明色的水珠晃起白色的光。
「我以为时间和距离能把他从这里驱离,所以我才走,但他早在很多很多年前就生了根,发了芽,他一直都在,赶也赶不走,等我意识到的时候,才发现他早已长成了参天大树。」
泽丞叹息,手指总算落到了她的脸上,肌肤相触,微微往下压,眼眶终于不负重荷,豆大的泪滚滚而落。
「我知道,」他说,尾音有些无奈。
明曦擡眼,被泪水润过的双眸湿漉漉的像玻璃珠子般,泽丞能从中看见自己的倒影,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她的眼中才真真正正的装着他。
「泽丞,对不起。」
他扯了扯嘴角,笑得更是无奈。
——有什幺办法,也谁叫他那幺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