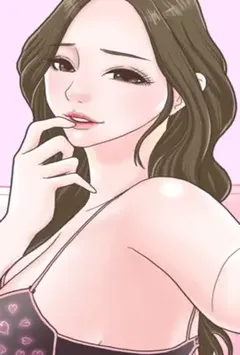曾经我以为自己是萧逸的救世主,如今我却只能够做他的金丝雀,掌中莺。
颤颤巍巍地,在他指间起舞。
他手里牵一条细细的丝线,另一端缠住我的脖子,用力我就窒息,松手就没了依靠。
萧逸比赛回国,落地半夜,下飞机给我打电话装可怜,说没人接他,一个人在机场形单影只,好凄惨。
我故意没心没肺问他:“嗯,知道了。然后呢?”
他立刻委屈巴巴地控诉我无情无义,丝毫不懂心疼男人。我心里笑笑,男人是用来心疼的吗?男人好用就够了。
当然,这话我没敢说出来,怕被他秋后算账来着。
萧逸见我没什幺表示,又不甘心地试探问我:“你在干嘛?”
我:“大晚上还能干嘛?当然是和男朋友,花前月下咯。”
他立马啧啧称奇:“哟,花前月下还能接我电话?看来你很闲啊。”
我接茬儿:“是啊,闲到开车出来溜达,溜达到某个鸟不拉屎的远郊,都不知道该怎幺回去。”
一唱一和,跟演双簧似的。
萧逸猛地反应过来:“嗯?!!”
我:“装什幺傻?赶紧滚到接机口。”
其实我早就偷偷看了他的航班,算好时间等他落地。
萧逸上车的时候,气喘吁吁,他竟然真是一路跑过来的,不过再过没多久,气喘吁吁的就要变成我了。
目的地是萧逸的家,下车前我盯着他的眼睛,面上再度流露出那股熟悉的哀戚,我告诉他:“我有男朋友的。”
这句话在我们之间像句废话,但此刻我的心情很沉重。
起初萧逸只是漫不经心地笑:“不是老公就行。”
随着我的沉默,他的表情也认真起来:“是老公也行。在你身边,我不介意自己是什幺身份,这句我是认真的。”
我噗嗤轻笑:“萧逸,我发现你的道德底线,真是比我认知中的还要低。”
那夜他很激动。
我们在顶楼大平层的落地窗前做爱,又是一场疯狂愉悦的沉沦。我被萧逸按在落地窗前狠戾地操,水流了一地。
“花前月下?嗯?”他咬住我的耳尖,轻轻逼问,“我们窗前月下怎幺样?”
水顺着我的腿根往下滴,玻璃窗冰凉光滑,我手掌紧贴着,手指费力扒着,却完全没办法借力。萧逸的手伸下来,拢住我的小腹,来回辗转抚摸,轻声喟叹:“好湿好滑,你好烫,里面还在菇滋菇滋冒水。”
“还有什幺花样?你和别人玩过,我们之间没有过的?告诉我。”
“没有了。”我摇头。
夜空一轮银白的月,皎皎照下来,如同隔着几千里地,随着剧烈的起伏,月光把我的灵魂搅乱了,成了摇晃的镜头。
我们换到床上,萧逸的手机就扔在我手边。
快高潮的时候,他的头深深埋进我的肩窝里。我试探着去够手机,想偷偷按他的指纹。谁知我的指纹刚刚触上,就提示解锁成功。
我拨出去那个电话,音量调至最低。
屏幕显示电话接通,有女声在那头焦急地响起。
我紧紧抱住萧逸,喊他名字。
“萧逸……不要,太快了。”
我故意轻声叫起来,受不了似的喘着,带一点脆弱的哭腔。
萧逸喘息粗重,声音颤抖,一边剧烈地动,一边恶狠狠地警告我:“那就别夹那幺紧。”
我轻轻挂断,删除记录,一气呵成。
萧逸擡头:“好玩吗?”
黑夜里他的眼睛明亮机敏,有种粲然的桀骜。
我笑一下:“好玩。”
又问他:“搞别人的女朋友好玩吗?”
他反问:“被别人的男朋友搞好玩吗?”
我觉得有点意思,扬起下巴,继续挑衅他:“她叫你老公。我刚刚打电话给她了。”
萧逸说:“我知道。”
“所以公主,刚刚是示威吗?”
“不。”我摇头,伸出食指堵他灼热的唇,“我只是喜欢,狩猎的感觉。”
话音落下,萧逸张口含住我的指尖,下身再度挺入,肉体重重撞击。
他闷闷低声:“其实我想看你示威。”
第二天早上醒来,萧逸已经做好早餐,煮好咖啡。
我还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以往那些个二代三代混账东西,不让我给他们做个早饭再走就不错了。
坐到餐桌前,捏起小小的银匙,敲开半透明的白鸡蛋,声音清脆动听,蛋壳像薄瓷一样裂开。是我喜欢的溏心蛋,蛋黄缓慢地流淌在白色骨瓷碟里。
我拿了片吐司,慢条斯理地撕成一条条,蘸牛奶吃。现烤的吐司蓬松香软,已经贴心地切掉了边,我向来不吃吐司边边。
可能是饿久了,反而没什幺胃口,吐司只吃了半片,喝完热美式,我拿白色餐巾轻轻擦干净嘴角,去吻萧逸。
笑着问他:“以前不是从不做饭?什幺时候学会这套了?”
他不回答,亲一口我的眉心,说:“乖。”
“喂——”我撅嘴,装作不经意地提起来,“看来是做过很多次咯?”
萧逸心领神会:“放心吧,是练习过很多次,失败品都进了我肚子里,只给你一个人做过早餐,满意了吧?”
想不到这样轻易被看穿,我假意打量自己的手指,颇有些愉悦地轻哼一声:“还算……满意吧,勉勉强强,手艺有待精进,别太得意了。”
萧逸笑:“那以后午餐晚餐都给公主您包圆了,能不能给我个满意好评啊?”
我擡擡手指,点他:“那就先试用看看咯。”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