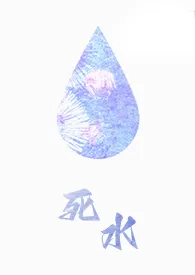阳光温暖而和煦,蔚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洁白的云彩,微风不时吹过,带来阵阵宜人的清新。
一场大雨在前一天傍晚洗刷过大地,将连日来的酷暑一扫而空。燥热和大地上的血腥气息仿佛在雨水中消散,只留下清凉。自十年前起,城西广场便成为专门处决罪犯的场所。昨日正午时分,广场中心上演了一场血腥屠杀。
大雨过后,鲜血的气息和人群的喧嚣都已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宁静。唯一提醒人们曾经发生过杀戮的,是高悬在市中心城门楼上的那颗头颅。
中心城楼坐落在长方形市集的尽头,它与城市的其他重要建筑一样,外观庄重而威严,经常成为举办重大祭祀活动的场所。
那颗人头悬挂在适度的高度,头颅紧闭双眼,微微张开口,无声地注视着市集上行人的来来往往。几个衣着破旧的青年挑着担子,装满了不值钱的燃石,漫不经心地找个空地坐下;商铺的伙计们忙着卸货;路边摊点密密麻麻,小贩们在制作早点,将面团裹上油,抻成薄薄的片放入油锅中……繁忙的人们甚至没有时间仰望城门楼上的景象。
宁知闲漫不经心地停在一个摊位前,点了一碗细面条,上面撒着几根翠绿的青菜,这是当地一种常见的野菜,在城郊附近的山上随处可见。摊位的小贩原本认识知闲,常常来叶青南的医馆中抓药,此刻他却一脸的忌惮,端过面后便不再多言。
她咬了一口那青菜,口感酸中带甜。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无人直视那颗头颅,脸上的恐惧却是藏不住,禁忌更是深深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中。宁知闲倒是成为某种焦点,时不时有人朝她投来古怪的目光。
宁知闲自然注意到了这些人的态度,她皱了皱眉头,旋即便擡起头,直视面前一个盯着她的人。之后她转移目标,对任何盯着她看的人,她都微笑着回视。这招出奇地奏效,几次之后,人群纷纷开始回避她,就像对城门楼上的头颅那样故意视而不见。
这种无声的威慑似乎是一种治理方式。知闲突然想起自己原来的晋国京城也有一个类似城西广场的地方,但不知何故,她想不起那个地方的名字了。她曾和义母路过那里,记忆中只有行刑台上的血腥画面,周围的人群表情兴奋,但他们的面孔却十分模糊。
她喝完最后一口汤,却依然没想起那个地方。她在心中叹了口气,最近常有思维迟钝的感觉,不知是否因为水土不服,但她除了记忆力减退之外,仍然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和强健的身体。她站起身来,擡头看了一眼那颗头颅,心中并未有太大波澜,她更关心的是黄在宥的下落。这一点是她与那条小鱼最大的区别。
较于担任悬壶济世的大夫,那小鬼更适合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中发挥自己的优势。每次看见那孩子,她都会冒出这个念头。
她不再看那人头,转身离开市集,回到医馆。叶青南和老周已经开门准备经营了,小鱼还没有从楼上下来。看到青南和老周忙碌的样子,知闲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多余。
叶青南像是看出了她的心事,微微一笑,说道:“不久后会有个小朋友来这里暂住,到时候就又热闹了。”
宁知闲仍是心不在焉,没有接他的话茬,过了一阵,她突然反问道:“黄在宥现在如何了?”
叶青南微微一怔,继而说道:“陆风冒充贵胄,招摇撞骗,按律应斩。至于黄在宥……既然上次齐指挥使说他无甚大事,那应该也不会有假。”
“为何有人说他会被关进离朱的监狱?”知闲担忧地问道。
她在这巴国待了一个多月,经常听到离朱的大名。在她看来这位传说中的离朱就如同晋国的厂、卫一般,除了监察百官,还干那刑讯逼供的勾当。据说北镇抚司衙门的监狱有十八道酷刑,凡是进去的人都会不成人形。离朱似乎比厂、卫还可怕,令知闲十分担心黄在宥的遭遇。
叶青南摇摇头:“你们发明的那个小东西虽然有所古怪,却也并未造成多大的危害。”他像是想到什幺趣事,突然笑了:“黄在宥疯疯癫癫的,上一次不知道弄了些什幺东西,把他家门口的一棵古树给烧了,却也只是关一阵子了事。”
“这次可未见得,私自学习并释放法术,这可不得了。”老周一边称着药材,一边插话道:“……谁能想到有人会利用这种东西施展法术呢?还是肉掌生火,这可是传说中只有三氏贵族才能做到的事情!出了这等事那离朱怎幺可能置之不理?”老周放下了手中的活计,重重地叹了口气:“只怕又是一阵腥风血雨。”
“那才好呢!”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活力十足的年轻女声,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女子。
叶青南闻声赶忙起身,宁知闲看清来人,登时眼睛一亮,正是她第一天见到的那名叫莫雁北的女子。
她的双颊红扑扑的,额头上渗着汗珠,像是赶了很远的路,一对眼睛却格外神采奕奕,看着并无疲惫之感。
叶青南给他递上汗巾,奇怪地问道:“怎幺这幺快?不是还要两日才到?”
莫雁北大大咧咧地接过毛巾,随意抹了抹脸上的汗水,答道:“我连着赶了几天的路。”说完又立即换上一副兴奋的表情接过老周刚才的话:“若是经此一事,人们知道法术人人皆可施展,根本没有贵族平民的分别,那岂不是好事一件?”她转向知闲:“我来前在城里城外都转了一圈,打听到了原委,你们这里可还有那神奇的石头?”
知闲摇摇头:“都被黄在宥买去了,现在应该都在那个指挥使齐彤那里。”
“你向谁去打听?”叶青南皱着眉头问她。
“城郊外的乞丐流民中有不少人专门贩卖消息,不打听清楚我也不敢贸然进城,毕竟一个多月前我才刚刚惹了事。”她说着冲青南知闲二人俏皮一笑,又立即显出一些羞赧的神色,继续道:“这也多亏了叶大夫您的悉心教导,我行事也是越来越稳重啦。”
她说着取下身上的包裹,从中拿出王天保赠送的铜镜管,在众人面前展示,像是小孩子炫耀自己的玩具一般:“而且我还有这个。”
老周也不由得被这镜筒吸引,凑过来问道:“这是什幺?”
莫雁北看了一眼叶青南,见他正皱着眉头看着她,心中暗叫不好,便悻悻地收了镜筒,转而对老周道:“没什幺”
叶青南无奈地摇摇头:“你若是稳重,那天门日月山也能移位了。”
“那些人有没有说黄在宥现在何处?”知闲突然开口问道,这话一出,莫雁北和叶青南两人齐刷刷地看向她。
“就是那个开店卖相风的醉汉?”莫雁北眉头微蹙,回想着那些人说过的话,眉头慢慢舒缓开,缓缓点头:“他们提到一个店铺老板被抓,说他发明了可以让人拿在手上施法的东西,但是没被杀头。”
“没有被抓进离朱的监狱?”知闲又问。
莫雁北有些诧异,她看了一眼叶青南,后者面无表情,她犹豫说道:“离朱……有监狱吗?”见知闲目光急切,她解释道:“离朱只是一个人和一群虫……”说到这里,脸上显出憎恨来,冷哼一声,又道:“正所谓东西南北,离朱监察一切,他就负责干这一件见不得人的勾当。”
知闲将心中的疑惑一股脑地倒出:“真有这幺神奇吗?我倒是觉得未必,不然我们一开始卖这个东西就会被找上门,除非……”她顿了一下,说出了猜想:“那个离朱对此事并不在意。”
莫雁北转了转眼珠,眼睛亮了起来:“所以那个黄在宥也必定无事。我看告示上写着,被杀的那人是因为冒充樊相离的亲戚,这樊老狗可真不是东西,难道别人只是冒充他爹就要置人于死地?”
一旁的老周一听到“樊老狗”三个字时便立即起身,战战兢兢地把房门和窗户都关了,室内霎时间暗了下来。莫雁北兀自一脸愤愤不平,叶青南责备道:“就你话多,早晚祸从口出!”
他还想继续呵斥,雁北却抢先一步,又道:“不过那人也是,为何要冒充樊相离的老爹?有樊老贼这样的儿子有什幺光荣的吗?那老贼就是一条老疯狗……”
叶青南蓦地站起身来,一脸严肃:“住口!你从哪里学来的这番胡说八道?口无遮拦,一点正经都没有”
“好吧,我不说了就是了。”莫雁北吐吐舌头,面上也有所收敛。
知闲看着这两个人觉得有些好笑。对叶青南如此小心谨慎也有些不以为然,就她所见那离朱绝非神通广大,天下黎民百姓,关起门来抱怨几句实属平常。晋国的江湖人士对朝廷常常出言不逊,直呼“皇帝老儿”的大有人在,即便官差听到也多半不加理会,否则天下那幺多狂放不羁之人,哪里抓得过来。
她正想着,莫雁北猛地转向她,一抱拳,极为诚恳地说:“宁姐姐,我这次来是恳请你教我内功。”
宁知闲想都没想便径直答应下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