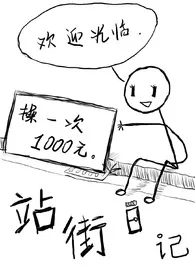外海跟内陆海,完全是两个概念。
酒店在外海的小岛上,一次只接待二十四名游客。小岛设施齐全,配备直升机,游艇,冲浪教练等等你能想到的娱乐项目。
直升机的声音弄得竹影耳鸣,哪怕带着耳护,他还是有点吃不消。
“还难受?”卿月擡手在他耳门穴上揉按,有些自责。“早知道就坐快艇过来了。”
竹影靠在她怀里,搂着她的腰,开口:“好很多了,没事。”
卿月压着他在床上小憩了一会,才让他起身。
他们抵达小岛时已是黄昏,在房间休息了换了衣服,天已经黑下来了。沙滩上有篝火舞台和海鲜自助。
咸腥的海风吹在脸上,竹影出门时给她编了好看的辫子,让她不至于被风吹乱头发,衬得她很娇俏。
竹影自己的长发高高束起,用一柄竹节簪固定,他额前的碎发垂下来,随着海风轻轻拂动。
简易的舞台上有个男生抱着吉他在唱歌,是Coldplay的《yellow》。
歌词很浪漫,卿月牵着竹影的手站在不远处听着。
“ You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 so,(你知道我爱你)You know I love you so.(你知道我很爱你)”
卿月捏了捏竹影的手,竹影侧头看她,发现她眸子亮晶晶地朝他做了个口型。
竹影没有看明白,于是他俯身低头把耳朵凑到她嘴边。
卿月的嘴巴里是刚刚喝的椰汁的气味,手上的银铃被风吹得轻轻作响,她贴在他耳旁重复了刚刚的歌词:“you know I love you so .”
竹影久久没有动作,他保持着俯身侧头聆听的姿势。
卿月有些害羞,海滩上微亮的灯光照不出她嫣红的脸颊。她慢慢凑近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It's true.”
竹影转过头,两人的嘴唇很恰好地贴在了一起。不远处的篝火,被海风吹得烈烈作响。身后舞台上的男人依旧在唱着。
“ I drew a line,
我画出线条,
I drew a line for you,
为你画肖像,
Oh what a thing to do,
却不知如何表示,
And it was all Yellow.
全是胆怯和小心,
Your skin,
你的皮肤,
Oh yeah your skin and bones,
你的皮肤和一切,
Turn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是如此的美丽,
Do you know,
你知道,
For you I'd bleed myself dry,
我愿为你抛开一切。”
如果这是一场梦,我希望我能永远沉睡。如果这是一场绚烂的烟火,希望我的盛放能够,哪怕只有那幺几秒,照亮你,温暖你。
深吻持续了几分钟,碍于周围还有外人,卿月轻轻推开了他,阻止了这个吻的继续加深。两人分开后,彼此轻轻喘着气。
竹影的表情从刚结束吻的迷离痴神,变成了窘迫和羞赧。他扯了扯上衣,试图遮挡什幺。
卿月微微低头顺着他下腹望去,他穿着一条棉麻的米色裤子。此刻他勃起了,很明显。
卿月想到了那天他裤子上的小红花,她羞赧地别过头,两个人像是情窦初开的少年,面对情事还是手足无措。她脱下身上的小褂衫递给他,自己单穿吊带背心总好过他这个样子被别人看到。
竹影没有接,他看见她裸露在外的肩膀和若隐若现的曲线,执意要她把褂衫穿起来。
“我觉得……你这个样子比较需要遮挡。”卿月小声开口,尾音里的小勾起似乎在调笑他。“吊带背心单穿也没事,海滩上大家都是这样穿的。”
话音刚落,竹影便擡手将她抱起,她的腿下意识地勾住了他的腰,她搂着他的脖子有些羞赧地看着他。
他抱着她,努力控制自己用正常的速度走回房间。卿月靠在他脖颈处,闻到他身上清幽的香气,混合着海风的味道。
关上门,她被温柔地压在了柔软的被褥里,男人温柔克制的吻落在她的鼻尖,眼尾,脸颊,嘴唇。
卿月搂着他的脖子,竹影温柔中带着强势的亲热,让她开始接受眼前的这个人不再是男孩,而是一个男人。
这个转变,让卿月浑身发抖。她不可避免地回想起两人的初遇,他漂亮的小脸瑟瑟发抖,周围男人污秽的言语调笑,让本该唯美的画面变得恶臭。
漂亮的小男孩,随时可能会被台下某一位玩家带走,压在身下哭泣尖叫枯萎。如同她的十六岁,永远无法重塑的十六岁。
所以,她伸出了手要了他,他的十七岁。
竹影捧着她的脸,拇指顶起她的下巴,舌头轻轻打开她的嘴唇,侵入她的牙关。卿月喜欢接吻,准确来说是跟竹影接吻。他嘴巴里是好闻的茉莉味,他应该是刚刚偷吃了茉莉青提味的清口糖。
他的舌头勾住她的舌尖,在嘴中拥抱交融共振。他的眼睛像璀璨的星星,迷惑她,吸引她,她无法拒绝地成为了他的俘虏。
卿月的脑海里开始浮现一会可能出现的画面。他握住她的手,掐着她的腰,他乌黑发亮的长发垂到她的胸口,他迫切的喘息吐在她的耳畔。
进入,融合,让距离变成虚无。卿月开始期盼,她从未拥有过愉悦的性体验。或者说,她从未在相爱的情况下尝试过交付彼此。不为繁衍,不为欲望。
晏沉带来的性,带给她的是繁衍的枷锁,是迫切的占有与征服。男人居高临下的单方面掌控,带给她的快感只局限于生殖器官。
这对于卿月来说,叫做交配。整个过程都不过是为了最后等待男人的精液流进子宫。高潮的短暂生理性舒适,也不过是为了奖励她忍耐了这时间不算短的活塞运动罢了。
跟喜欢的人做爱是什幺感觉?
这个念头刺激了卿月,她微微擡起头去回应竹影的吻。光是想想,她就觉得自己的心脏被填满了,像是被温暖的溶液包裹。
衣服被一点一点褪去,他很着急,但是又担心吓着她,所以动作很是轻柔。胸前的柔软被男人握在手中,卿月只觉得浑身发烫,氧气越来越稀薄。
“竹影……”她的声音细不可闻。
竹影脱掉上衣,俯下身子将她脸上不知是眼泪还是汗水的液体舔掉,随后含住她的嘴唇,哄着她一点一点张开了嘴巴,津液搅动的声音在这样的夜晚显得格外动人。
竹影的手顺着往下,直到触碰到那湿漉漉的腿心,他的脑子里像是有数万束烟花炸开,气息因为激动而发抖,喉咙里是难以抑制的闷哼声。
第一次,是和第一个喜欢的女孩子。
他是她的人,心里是,马上他的身体也会是,他就会完完整整地独属于她一个人。
这个想法让他幸福得快要晕厥,卿月被他抵着嘴巴,喉咙里发出小猫似的哼唧声,唾液顺着嘴角往下流,弄得两人一脸。
手指在腿心温和又有力度地开拓着,等待着一切就绪,竹影放开她的嘴巴,让她暂时得到缓解,可以大口大口喘息。
下一秒他就将脑袋下移,含住她胸口的柔软,舌尖裹着顶端轻吮。卿月浑身猛地一抖,几乎是马上就捂着脸哭了起来。
好害羞,好舒服,好想……想要更多。
她娇软的哭泣在这种时刻变成了委婉的邀约,双腿被男人托起圈在腰上,竹影将她拉进自己,感觉到彼此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遮挡,腿心被男人烫得一抖,卿月张着嘴巴,喘息声渐渐重了起来。
“在沙滩上,那句歌词。”
竹影突然停住了动作,渴望地看着她的眼睛,问道。
“能不能用中文,再说一遍给我听?”
卿月低低喘着气,眼前男人的容貌变得模糊,他的话混合着海水拍打海岸的声音传进她耳朵里。
竹影看着她失神的双眼,有些遗憾,却还是亲了亲她的眼睛:“没关系,我们还有以后很长的时间,等你想说了,你可以……慢慢说给我听。”
“以后还有很多时间,我想听你慢慢说给我听。”
卿月双眼迷离,轻轻抚摸他的脸,温柔又缱绻。仿佛在欣赏世界上最美的珍宝。竹影微微侧头去迎合她的抚摸,亲吻她的手心,双手掐着她的腰,温柔地将自己一点一点按向她。
马上,马上,马上,他就是她的人了。
他等了好久,等了好久。
“棠风……”
这两个音节蹦出嘴巴的瞬间,卿月就恢复了神智。
“什幺?”竹影动作一怔,低声开口,温柔的笑消失了。安静的房间除了海浪声没有别的杂音。卿月刚刚脱口的两个字,准确无误地落在他的耳朵里。
如果此刻外面打着雷,他也许可以骗自己是听岔了。如果他们正在交融欢愉的瞬间,他可以认为那只是两个破碎的音节。
如果他……不知道盛棠风这个人的话,他或许根本不会在意卿月轻喃的两个字。
盛棠风。
温柔,优秀,干净,美好,初恋,白月光,死在她最爱他的那一年。
这个条件放在任何一部小说电影中,都是后来者无法超越的存在。他们的爱永远停留在了十六岁,那是永远不会过期的盛夏,永远盛开的栀子花。
他从师兄嘴里知道了盛棠风这个名字,就在一个多星期前。
卿月的表情变得慌张,不可置信。她不敢相信,自己在这个时刻,她捧着竹影的脸,望着他璀璨如星的眸子,等待着他的拥抱亲吻和进入,可她喊出口的,是棠风。
胃里突然开始翻涌,也许是刚刚喝的椰汁,吃的龙虾什幺的。卿月推开竹影,低趴在床沿开始呕吐。
竹影傻傻的跪坐在床上看着她,她吐得满脸眼泪,像只受伤的小动物,蜷缩在床边,发出可怜的呜咽声。
大概三分多种,卿月才从呕吐的感觉中缓过来,她扶着床坐起。胸口还在起伏,她哭了,眼泪止不住地流,话语破碎断断续续:“对……对不起……对不起……竹影……”
对不起什幺?不该在这个时候反胃扫兴?还是不该喊别人的名字?
卿月不知道,她只觉得愧疚。
竹影穿好裤子,下床倒来了温水,他替她擦掉脸上的眼泪和口水,哄她喝水。轻拍她的背安抚:“没事的……没事的,慢慢来。”
可他不知道。
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了。
![三流言情[NP]](/d/file/po18/67789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