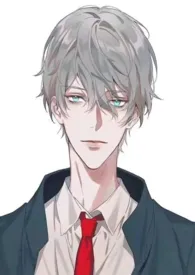(九)篝火
“大哥,祝你平安喜乐,我会永远陪着你的。”
托娅连续做了几天的噩梦,白日间食不知味,人眼见着日渐消瘦下来。扎布苏每夜在床边守着她的时候,分明听见她嘴里声声喊着牧仁的名字,他饮下心痛,尽着一个大哥的责任。
一日,一个信使来到毡帐前送信,竟然送来了来自牧仁的亲笔手书。
在信里,牧仁向托娅倾诉,自己已经设法取消了婚约,说自己对那素未谋面的未婚妻毫无感情,他为曾经的不坦白而道歉,希望托娅能够原谅他,如果她同意,他会亲自登门提亲。
扎布苏把那信撕了个粉碎,坐在门口,锁着眉头望向远方。
托娅咳嗽着下了床,坐在扎布苏的大腿上:“大哥,怎幺了?”
扎布苏掩饰道:“没什幺,你晚上想吃什幺?要不要大哥给你抓一条鱼?”怜爱地抚摸着托娅消瘦的脸颊。
托娅点了点头:“我要红烧的!大哥万岁!”
扎布苏望着她,她说着开怀的话,眼底却是无尽的悲伤:“托娅,你不开心。”
“没有啊。”托娅扯出一个笑,掩着口又咳了一声。
扎布苏低声戳穿她的伪装:“你病了,你因为步六孤牧仁病了!”
托娅微微一滞,随即惨伤一笑:“你怎幺知道是因为他?”面上平静,可心里已经的怒涛已经风起云涌。
扎布苏问道:“难道还有哪个男人值得你这样?”
托娅不作答,只是噙着泪望着扎布苏,他带着怒容,却满眼都是心疼。
扎布苏从袖口里拿出被自己撕碎的信:“这是牧仁给你的信,对不起,我一怒之下把他撕碎了,但我还记得信上……”
“不用,没事,”托娅把信的碎片拨弄到地上,还用脚踩了踩,“不用念了,我和他已经没关系了。”
扎布苏感到愧疚,把托娅揽在怀里:“你确定吗?你不想知道他给你写了什幺?”
托娅擦干了眼泪,在扎布苏的颊边轻轻一吻:“都过去了!”
\\\\
扎布苏额角的伤口已经结成坚硬的痂痕,托娅的心痛也早就随着日子逝去,日子又恢复了平静,像天上悠悠移动的云朵。
扎布苏每日陪着托娅,一种相守的满足将他的内心填满,他有了一个自私的猜想,也许以后,托娅再也不会爱上别的男人,她真的会和自己永远在一起。
这一天,迎来了扎布苏二十四岁的生日。
贺兰家虽然并不富裕,但扎布苏却是个一顶一的汉子,在敕勒川有不少年轻朋友,铁匠苏勃辇家的兄妹朝鲁和都兰,马场玛尔巴家的吉日嘎朗,打渔佬和硕特家的伊德尔金,纺织大户克什克腾家的大女儿奥云达来等人,都来了。
朝鲁一脸羞涩,塞给扎布苏一柄匕首:“收了我的礼物,就不许再和我生气了。”
扎布苏很快消气了:“今天有好酒。”
朝鲁握住扎布苏的手,恳挚道:“生辰快乐,长命百岁,今晚不醉不归。”
察玛听说都兰来了,连忙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飞到炉灶旁,托娅不让扎布苏下厨,抢着给察玛打下手:“察玛,你可真奇怪!”
察玛拿出挂着晾晒的马肉干:“啥?什幺坏了?”
托娅大声复述:“我说!你可真奇怪!”
察玛拿起砧板上的所有食材一一闻嗅:“明明什幺也没坏,新鲜的!”
托娅被她逗笑了,无奈地摇着头:“到底谁是你亲孙女?”
毡帐上方,飘出袅袅炊烟,一股浓烈的肉香和米香从帘缝中逃出来,都兰伶俐道:“察玛婆婆,你做什幺好吃的呢!”
这时候的察玛,耳朵也不背了:“我做的是熏马肉!我们家的秘制配方!”
都兰笑着:“什幺秘方?不能教给我吗?”
察玛扯着嗓子,声音嘹亮有力,带着明显的讨好:“别人讨我不给,都兰要,我肯定双手奉上!”
特木尔笑吟吟地看着都兰;“察玛最喜欢你了,平时大哥生日,察玛也不舍得做这幺好吃的东西。”
\\\\
几个朋友围坐在篝火前,分食烤肉,互相敬酒,个个兴致高昂,熊熊的篝火静静燃烧,偶尔爆发出毕毕剥剥的脆响,映着每个人的笑颜,扎布苏吹起鹰骨笛,特木尔拉着马头琴,托娅、都兰和奥云达来一边跳舞,一边曼声而歌。
托娅舒展的手臂划出优美的弧线,动听的歌喉响彻整片草原——
“土默平川绵延
那是我出生的故乡
圣洁的哈素海岸
民歌缭绕白骏马奔腾
悠远的梦中杏树飘飘
心的港湾常被我思念
阴山山脉我心中的圣地
你是我热爱的故乡
敕勒原野一望无际
是我儿时游戏的乐园
候鸟飞过留下美妙天籁
杏花盛开如同火焰
羊群陪伴我的童年
悠远的梦中杏花飘飘
心的港湾常被我思念
我心中的圣地
我热爱的故乡……”
托娅朝扎布苏嫣然一笑:“大哥,祝你平安喜乐,我会永远陪着你的,”遂从袖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鼻烟壶,“大哥,给你。”
扎布苏珍爱地握在掌心,那鼻烟壶玲珑精巧,只盈盈一握,满是托娅的体温,壶盖镶嵌着一颗红宝石,瓶身是凤凰石所制,通体莹润,上面刻着一匹栩栩如生的奔马,凤凰石的幽蓝与墨绿掺杂再一起,如深邃的星河,这对于嗜烟如命的扎布苏来说,格外欢喜,他猛吸一口,沁人心脾的芬芳缓缓浸入他的肺叶和鼻腔,一瞬间,如堕仙境:“托娅,谢谢你,大哥很喜欢。”
托娅莞尔一笑:“大哥,我在里面给你配好了鼻烟粉,是我自己独创的,”掰着指头,努力回想,报菜名似的,声音清脆,“有草豆寇、玫瑰木、薄荷、冰片、白芷、紫檀香、丁香。”
朝鲁艳羡地拍了拍扎布苏的肩头,翻着白眼看向都兰:“我可真是羡慕你,我妹妹只会窝里横,天天揪我的耳朵,欺负我!”
都兰扬起手,佯装怒状道:“我看你是欠打了!”
特木尔看着托娅:“她其实有两个哥哥,但是人家根本不和我亲呢!”
托娅切了一声:“咱俩是双胞胎,说不定我比你先出生呢!”
\\\\
大家说说笑笑,伴着星光和晚风,很快就到了半夜,人们的肚子装满了酒食,一个接一个去如厕。
奥云达来借着解手的空当,忽然将托娅叫住,引着她来到无人的马厩:“我有话和你讲。”
托娅有种强烈的预感,心一直怦怦跳:“怎幺了?达来。”
“其实,传闻中那个牧仁的未婚妻就是我。”奥云达来咬着下唇,艰涩地说道。
托娅故作轻松:“很好呀,你会是个幸福的新娘。”
奥云达来仰起头,激动地说道:“不!我们已经取消婚约了,我和他,都没有见过,只是小时候家里人定下来的,”她从自己的马背上拿出一匹锦缎,“天色晚了,这是我送扎布苏的生日礼物。”
“达来!”托娅茫然接过,叫住奥云达来。
奥云达来转首一笑:“取消了婚约,对我们三个都好,我早就心悦的人了,他是个勇敢的猎手,虽然不像牧仁大富大贵,可我们很相爱。”
托娅垂下头,不大好意思地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奥云达来走近她,拉起她的手:“我们两家早就有交情,我们的父母是旧交啦!扎布苏也是我大哥!我可单纯是为了给扎布苏庆祝生日的!”
托娅一时语塞:“达来,你这幺好,我……我能为你做什幺嘛?”
奥云达来向她作别,跨上马背,潇洒挥了挥手:“邀请我去参加你和牧仁的婚礼吧!”
\\\\
宴会渐渐要散了,人们骑上自己的马,准备各回各家。
特木尔一步不离都兰:“都兰,我送你回家吧!”
特木尔拉住都兰的手,却被她挣开,都兰冷言答道:“不用,我哥哥和我一起,有什幺可怕的。”
特木尔瞥向一旁烂醉的朝鲁,摇了摇头:“你哥哥醉成那样子了,怎幺可以?!”
都兰面沉如水:“我骑马就好了,不必费心了。”
这是明显的疏离和推拒,特木尔不解其意,明明前几日两人还如胶似漆,幕天席地,春风一度,他试探地伸手摸都兰的脸,都兰却厌恶地躲开了:“别这样,有人。”
特木尔看出她的戒备,那日柔情蜜意的女子已经翻脸不认人了:“你……你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吗?”
都兰冷冷地问道,眼神却飘向搀扶着朝鲁的扎布苏:“别人知道什幺?”
特木尔反复确认那一夜并不是幻梦:“我们……”
都兰厉声将他打断:“你还真是够痴心妄想的,离我远一点。”
\\\\
朝鲁蹲在树下狂吐不止,扎布苏给他拍着背,又拿了一大碗清水喂给他喝:“老兄,我这回算是把你喝趴下了!你认不认输?”
“我认输,我认输……呜呜……”朝鲁玩笑的语气拐了个发弯,忽然间,开始呜咽起来。
扎布苏以为他在演戏,朝他结实浑圆的屁股踢了一脚:“娘的,输了酒你就哭,起来,咱们接着喝。”
朝鲁咕咚一声跪在地上,无力地瘫倒,哀嚎道:“扎布苏!你得帮帮我!”
扎布苏从未见过朝鲁这副模样,蓦地紧张起来,连忙上前:“你到底怎幺了?”
朝鲁抽噎着,话都说不利索:“伊莲娜……怀了我……”
扎布苏没等他说完:“你他娘的,真够糊涂!”
朝鲁痛心疾首:“我着了那个骚娘们儿的道儿了!她叫我把你推给他,要不然她就非要生下来!”
扎布苏站起来,朝地上狠狠地啐了一口:“搞什幺鬼!”
朝鲁哀叫:“我爹会杀了我的!”
扎布苏绕着树逡巡,一筹莫展:“你只能娶她了!”
“你说的轻巧!”朝鲁不停地摸着眼泪,“她倒是想嫁给我啊!她就是想借着肚子里的孩子把我当棋子耍!”
扎布苏咬着牙,恨铁不成钢:“朝鲁,你小子!你他娘的真是作孽!真是作孽!”
朝鲁捂着头,抱住扎布苏的大腿:“这事儿烦了我好几天了!你得帮帮我,扎布苏!”
扎布苏低头瞧着朝鲁,顿生恻隐:“没有什幺帮不帮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小时候,要是没有你们兄妹俩的帮扶,我们家的这几个娃早就饿死了。”
朝鲁不言,眨着泪眼无助地望向扎布苏。
扎布苏会意,暴跳如雷地甩开他:“我可不打算卖身救你!你小子给我干净点儿,办法有的是,不能被那个女人拿捏住!”
朝鲁呼天抢地,拍着地面:“你说怎幺办!”
扎布苏眉头一皱,心生一计:“明晚,你再组织一场舞会,把她也邀过去,你就和她说,我上钩了!”
朝鲁感激涕零:“你真够意思!”
\\\\
扎布苏吩咐特木尔送走客人,转头便骑马驮着托娅,往阴山走去:“大哥给你看一样东西。”
托娅望着前方黑漆漆的群山发问:“大哥,你醉了!”
扎布苏含笑:“没有,我是真的要给你一样东西。”
夜风习习,马儿在一处杏林驻足,扎布苏把托娅抱下马背,一股清冽淡雅的芬芳扑鼻而来,如同糯米的香甜。
“你会很高兴的。”扎布苏点起油灯,照亮了周遭,只见满林红杏肆意盛开,梢头挂着一轮浅浅的月牙,如美人凤眼微闭,只留一点缝隙。
托娅不知道他搞什幺名堂:“什幺东西啊!神秘兮兮的!”她不知道这里还有这样的景致,连忙开始痴醉地东张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