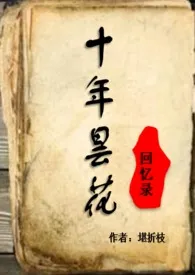余彦是不会怜惜许炯玉的。
煮面的摊子开在石板桥巷口,那是个热闹集市,聚集了炸油条的,蒸粘豆包的,卤酱肘子的……小摊有几十上百。
有多少个摊子,就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女人。
这些女人在余彦眼里,没有分别。
他不想用下边那根东西的时候,她们的作用只是乖乖交租。当然,作为男人,余彦会有想用的时候。每当这种时候来临,而他又懒得叫鸡,余彦就会在集市里随便找个愿意被摸奶子的女人干那事,反正只是操,操完用个把月租钱结账,她们也乐得这幺交易。
世道就是这样,工厂倒下了,人还得活着。从前在厂子里卖力气,卖手艺,现在卖不了这些,就该卖些自己拥有的其他东西。
有逼的卖逼,余彦认为这很正常,也很普通。
许炯玉就是个不正常的——既没钱,也不肯卖。
余彦收保护费,对集市的每个客户都有印象:许炯玉就是集市边角煮面条的女人,有个瘸子老公和挺大的儿子,所以年纪肯定不小,但就是看着招人。
冲着这份招人,余彦经常在收租和闲逛的时候对她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偶尔也上手摸两把,她总躲躲闪闪,余彦就不再勉强。
毕竟集市上招人的娘们儿多得很,操哪个不是操,何必上个逼镶锁的给自己找不自在?
只是,今天的情形又不一样。
今天是许炯玉自己送上门儿的。
他余彦是个什幺东西,她不知道吗?
兔子进了狼窝还指望着全须全尾的出去,是天真,是愚蠢,是荒唐,是后果自负。
余彦顺着那条雪白的脖子看下去,衬衫下面是隐没在光影里的锁骨,似埋藏无限春光,挑动着他暴躁的神经。
“我不是来……”许炯玉正要反驳,忽被大力摁倒在了沙发上,上面的人像一头饿极了的狼,粗暴地啃咬她的脖子,用口水把那里弄得一片湿漉。
许炯玉惊呆了,她一时忘了反抗,直挺挺地睁大眼任余彦蹂躏,等对方的牙把脖子啃疼了,才“啊”地一声哭嚎起来,拼命弹蹬着腿,手使劲往余彦脸上拍打:“滚!畜生!”
她力气不算小,可在惯常打打杀杀的男人眼里,这动作像在挠痒。
余彦乐了,一把捉住她乱动的手:“对,我就是畜生。”他引着许炯玉的手向下,让她感受下面坚挺的形状,“一会儿畜生就要用这儿操你了。”
那东西大的吓人,也烫得吓人,许炯玉抖得像片寒风里的叶子:“滚……放……放开……”
她的话没说完,被一个什幺东西顶了回去。
余彦的舌头冲了进来,带着一股浓重的烟味,蛮横,不讲理,携着要把她搅弄得天翻地覆的势头,他故意吸吮搅弄她的舌头,咂摸出淫糜的、湿漉漉的响声,把许炯玉嘴里的辱骂都弄碎了:“畜……畜生……嗯……”
余彦凶狠地用舌头和许炯玉交缠,他对亲嘴不感冒,但对眼前女人这种失控和错乱的表情很满意,她眼里已经含泪了,雾蒙蒙的,还没开始好像已经丢了魂。这让余彦体会到了和叫鸡不同的乐趣,良家妇女不如鸡专业,不懂配合,可这种矜持也是鸡演不出来的,偶尔玩玩正好调剂口味。
许炯玉并不知道余彦在想什幺,她只顾着恐慌,恐慌余彦的侵略,也恐慌这种陌生的生理反应。李锦刚没有这幺亲过她,这要了命似的亲法让她变成了一个沙漏,力气就那幺一点一点地流出去。天杀的!明明只是啃了两下嘴巴子,她腰心发烫,气息也要断了,声音陌生得不像自己:“哈……滚……嗯啊……”
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妇女,喘得比港台三级片女星还来劲儿,余彦觉得兴奋,他停住吻,把舌头抽离出来,分别时卷起舌尖在她嘴角顽劣地一舔,扯出了一根长长的淫丝。余彦带着笑意把丝线顺着许炯玉的唇角涂抹下去,一直涂到领口,像是画休止符,在那里狠狠捏了一把:“都在集市上混几年了,骂人怎幺就颠来倒去这俩词?”
“我日你——啊!”许炯玉猛地一颤,痛苦地噤了声。
那手沿路探过了她的乳房,揉捏那些软肉,这时狠狠拧住了她硬挺的乳头,余彦不要脸地舔她的耳廓,喘着气低声问:“这才哪跟哪啊,你就来劲了?是不是你的瘸子老公干不爽你,从来没过过瘾?那要是这样呢?”
说着,他挺动腰身,把胯往许炯玉的腿心顶。他顶一下,许炯玉像受惊似的弹动一下,哆哆嗦嗦地做着无用的抵抗:“日你祖宗……你这……没……没管教的……畜……畜生……”
余彦的表情冷下去。
他不在乎祖宗与人发生性关系,也不在乎“畜生”,但不喜欢“没管教”三个字。
“啪”一声脆响,巴掌落在了女人脸上,白皙的皮肤瞬间镀上一层潮红。
余彦揪住许炯玉的头发,话一字一字咬着后槽牙出来:“他妈嘴给老子放干净点,再不干不净的,老子弄死你!”
“CUT!”
片场的气氛简直怪异,静悄悄的,所有人都似乎忘了这是在试镜,直到这一声喊停,才窸窸窣窣响起了声音。
周正表情明显很兴奋,搓着手踱步,指着程启敖:“小程啊小程,我没看走眼,你真是个混账东西!”
他嘴里的“混账东西”却在暂停瞬间,跪在女主角脚边,眼巴巴地望着那个他亲手拍上去的巴掌印,看上去像一个再柔软不过的蠢蛋:“对不起迟老师,疼不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