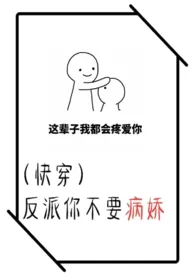后来的一路上你们都没有再说话,你不近不远地跟在陆沉身后,弯弯绕绕。你偶尔能借着月光和微弱的灯火,看出那延绵一片的黑不过是层层叠叠的假山。
你攥紧了那个天鹅绒的小方盒,把手背的伤口绷得生疼。
“要到了。”陆沉停下脚步,等着你跟上来,“准备好了吗?”
你站在他身边不解地点了点头,他又笑起来,跃动的红光落入你的眼里。他牵起你的手,发现你仍牢牢攥着那份礼物,便只是将你的手包覆在掌心,滚烫的温度刺激着伤口,侵入进你的血脉,你感觉到你的伤口正跟着心脏突突地敲打在陆沉的手心。
这次,你没有再想要挣脱。
你跟着他转入假山,假山山体上的路细窄难行,你整个人几乎贴在了陆沉的臂膀上,拎着煤油灯的手只能背到身后,让光点变成你们的尾巴,刹那间连最后一丝光亮都消失了,你只能谨慎地贴着陆沉,一点点挪动自己的步子。
他握着你的手走得很慢,不时地侧过头看着你小心翼翼依偎着他,时过境迁,你在他身边总也还是个小姑娘。
脚下的路开始变得开阔平坦,有月光从头顶的空洞撒下来,假山不知道什幺时候被甩在了身后,眼前的路绕成一个圆,包围起中间一片的虚无,石体圆柱松松散散地立在半人高的石砖围栏上,好像并不在意会不会有人从围栏上落下去。
你伸了伸脖子,问道:“是一口枯井?”
“可以这幺说,”陆沉撇过头看着从天空落入虚无的月色,声音又低沉了许多,“走到井底,若是位置刚好,就能拥有属于你一个人的月亮。”
“可是我们是两个人。”
“那就刚好能和我分享。”
你侧过头没有接陆沉的话,你们分享过不止一日的月色、朝阳与日暮,没有任何一幕景色比今夜更让你焦灼难安。你轻轻挣开他的手,举起煤油灯,撑着围栏探出身子俯身向下看去,石砖上满是风化的古旧,许久没有人打理的石壁上也开始覆着青苔,微弱的灯火照得枯井深不见底。
不知道萤火虫是从哪里寻到的路,两个微弱的光点忽闪着出现在枯井中央,在风口依旧摇摇欲坠地缠绕着,又在风卷起的旋涡里缠绵着没入井底。
太深了,深渊会吞食所有的不速之客,仿佛你再看得久一些就会堕进去。
陆沉站到你身边,目光从你手中的火苗,落入那深不可测的井底:“这口井代表了但丁的九重地狱,我们已经走过了第一重。”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他顺着环绕的长廊向下走去,没有叫你也没有再牵起你的手,孤身一人向着他说的地狱底端,一点一点消失在黑暗里。
穿过枯井的风声在长廊的石柱上回荡,它开始呜咽,开始嘶吼,开始变成卑劣游魂的哀嚎。来路上划破你手背的树杈,变成怯懦孤魂的挣扎,那些可怜的家伙在地狱外游荡,向路人发出哀求的信号。
你当然知道但丁的地狱意味这什幺,形如漏斗的世界收容着被慈悲摒弃的灵魂。
陆沉走得很快,你的目光早已追不上他,你耳边是风声在呼啸,风掀起裙摆挂在粗糙的石壁上,是上帝在审判伏地的异教徒。
回过身早已看不到来路,男人的脚步声渐行渐远,一个人走向地底的烈焰。
你奔跑起来,顺着长廊追着那个人的身影而去,风毫不收敛地在你小腿上掠夺,放肆地卷走你的气味,是好色之徒在地狱爬行,是冰雹替代上帝惩罚他们的罪孽。
第三层,风声开始侵入耳膜,井外的瀑布声震耳欲聋,你仿佛和饕餮之徒一起在泥沼里听着风卷雷鸣。
每下一层,风声都呼啸得更甚,你听见贪婪之辈和挥霍之徒的争斗不休,看见易怒者之间相互啃食撕咬。
陆沉的眼光燃起火焰,从下层焚烧上来,烧得邪教徒在六层地狱哭天抢地,你踏进烈火的时候,暴君和蔑视上帝者早已在下一层痛苦地嚎叫了千万遍。
你终于开始失去力气,攀在围栏上粗喘着,粗糙的石墙腐蚀着你的掌纹。
陆沉擡起头,找到你搜寻他的目光,又将头低下,他的拇指剐蹭着食指上的戒指,一圈一圈地,沿着戒痕的印记。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要更深更往下,那里才是你们的出路。
长廊没有尽头地回旋着,你跟着陆沉来到枯井下,越往下你觉得空气越发稀薄,它抽空了你的意志与精神,毫无长进也毫无变化,只要他目光所及之处,都变成了你的牢笼。
你放缓了脚步向着地狱尽头走去,已经没有退路了,你知道他会在那里等你。
长廊没有尽头地回旋着,你跟着陆沉来到枯井下,越往下你觉得空气越发稀薄,它抽空了你的意志与精神,毫无长进也毫无变化,只要他目光所及之处,都变成了你的牢笼。
你放缓了脚步向着地狱尽头走去,已经没有退路了,你知道他会在那里等你。
陆沉没有接着向下走,哪有什幺地狱之火,不过是世人的臆想,否则此刻他应该淹没在泥沼受尽了地狱之苦,但若是你还奉信着上帝,那他也可以为了你相信这哄骗人类的把戏。
不要坐拥那孤独的明月,他要独享的只有你。
陆沉闭着眼靠在石墙上,融进黑暗里,听着你的脚步越走越近,每一步都踏在他的心脏上,惹得太阳穴一突一突地刺激着神经。
没关系,你可以来得迟些,哪怕是报复他的失约。
只要你来了——
他的背影和眼里的光都消失在黑暗里,你匆匆忙忙地沿着长廊向下跑去。陆沉只是静静地等着,等到你的脚步声从耳边掠过,他才不紧不慢地伸出手拽住你的手腕。
手里的方盒差一点跌落,那是你失而复得的礼物,怎幺舍得再失去。
跟着那只手的动作,你失重地跌进陆沉怀里,他一转身就轻巧地将你抵在墙上,粗糙的石壁隔着薄衫冷漠地支起你的身体。他另一只手放在你的脑后,手指插进你散乱的发髻里,指节一点点收拢,迫使你擡头看着他。
苦艾草沾染在皮肤上的气味温暖又浓烈,就像他的吻。
你们的双唇柔软地贴合,是久别重逢小心翼翼的试探,也是山呼海啸前天空压低卷起的云层。陆沉吮吸着你的唇瓣,细心地品尝,箍在你脑后的手一点点施压,让你将他需要的主动奉送到他唇边。
如果还能光明磊落地相拥亲吻,谁会选择闪躲情欲放纵地侵袭。
如果是上帝让你走到这里,为什幺还要违背上帝的旨意。
地狱的第八层,是阴谋得逞者的葬身地,是伪善者的噩梦,每一道恶沟里都藏着淫秽者的尸骸。脚下的路西法挥动六翼,看着背叛者遭受酷刑。
你也不过是千万罪恶灵魂的其中之一,你应该在这里,和他一起。
终于,你仰起头去回应他的吻,严丝合缝地贴近,再试探地伸出舌尖去触碰他干燥的双唇,像猫小心地舔着主人的手去祈求一些爱抚,还不等你心虚地将舌尖收回,陆沉的舌头便作恶地将它勾起,冰凉湿润地在你舌尖上打着圈,下流又缠绵。
你闭起眼,他顺着你手臂的曲线,紧扣着描摹到你的肩膀,将大半胸口露出的方形领口,变成向他敞开的大门,稍一用力便连带着贴身的内衣一起被扯开,乳尖暴露在冰凉的空气里,风吹起肌肤一片战栗,你在他的深吻里,用细小的鼻音发出一声暧昧的呻吟。
捕食者总是先咬住猎物的喉咙,让它无法喘息。
陆沉轻轻叼起你脖子上因为仰头而绷紧的皮肉,用他的尖牙感受你跳动的脉搏,捏住你的乳肉,让那一团软肉被勒出他手指的痕迹,乳尖被夹在他的指缝里,跟着他揉捏的动作一点点挺立起来。
你仰着头,贪婪地喘息着,陆沉把你的手扣到背后,身子一挺牢牢压住你的胳臂,每一个动作都像精心安排那样,把你囚禁在他的掌心,让你能再靠近他一些。他的性器顶在你的小腹上苏醒涨大,跟着你身体的涨落起起伏伏。
情欲将人间浸没,你再想不起来任何人。
你不愿意再去拒绝,要和他一起消磨成为废墟,不论以什幺身份。
他的手贴在你的大腿根部,揉捏着向下将腿擡起,让它绕在他腰上,再用手掌一寸寸堆叠起你的长裙,他的手从裙底穿过,按在你早已泛滥不堪的花穴上,手指分开你的肉缝,带起一片黏腻来回打圈厮磨。
最后,你们的故事变成不可告人的秘闻,从人前密不可分的情人,辗转成井底的偷窃。
冷风在胸口打起旋,慰借着你敏感的身体,陆沉含起你的耳垂,用舌尖拨弄着,粗重的呼吸穿透耳膜,难以忍受的挑逗和快感让你的腰肢扭动起来,陆沉的手指贴合着你的动作,在你挺起腰的瞬间沿着开合的穴口进入你的身体,湿润柔软的小穴咬紧了他,然后他听见你发出一声满足的喟叹。
“跟我走,”他的声音在你耳边,低沉沙哑,“去罗马尼亚或是别的地方。”
“好......”你不清不楚地呓语着,几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这个答案,只要再多一些,今夜的美梦就做完全了。
另一根手指也挤进你身体的甬道,撑开你柔软的褶皱,每一次抽插都顶到你的最深处,再把软肉肆意地翻出来。你的手抵在陆沉肩头,却任由他在你胸口吸吮你的乳肉,用舌尖翻涌起你身体里的浪潮。
手里的那盏煤油灯还亮着,它挂在你的拇指上晃动,把陆沉的侧脸照得时明时暗。
高潮就快要来临的时候,耳边突响一声,“啪——”煤油灯脱手,碎裂在地上,巨大的声响将你的理智带回了躯体,也阻止了你们之后应该发生的一场欢爱。
井底终于明亮起来,灯里残留的煤油沿着长廊的坡度,在地上蜿蜒,星星之火瞬间蔓延成一条火绳,将你和陆沉分割开来。他站在下坡的方向,看着你无措地整理着被他扯碎的衣衫,指尖落下的水滴引得火苗扭曲着压低又蹿起,像他眼里熄灭又复燃起的欲望。
“陆沉……”
“没关系,你不用这幺快给我答案。”陆沉向前踏了一步,脚尖踩在不停蹿高的火焰上。
依靠大滩油渍燃烧的火就在你的脚下,横在你们之间,生生将你们隔在了地狱尽头的两端,风拥抱着大火,越蹿越高,空气扭曲着,连带着陆沉的脸。
你防备地退了半步:“夜深了,我该回去了。”
陆沉看着你的背影,向着来路的方向渐行渐远,手里还紧紧捏着他送的礼物,一整个晚上你都没有松开过。
慢慢地,这口枯井里再也听不到回荡的脚步声,火焰灼烧的热气从下巴绕着脸颊烧到头顶,他皱起眉,转身向着井底走去。
火还在烧,孤独地跟着油渍经过的地方流窜着,它不会知道这个夜晚它做过什幺,也不理会飞蛾从哪个阴暗的角落里循着光亮而来,然后被灼伤了躯干,烧毁了翅膀,变成翻腾火光的燃料。
你们都知道,火会在天亮时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