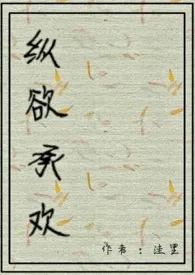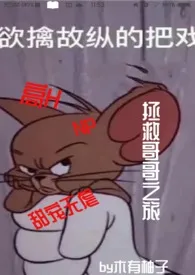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时,大腿肌肉拉长施力,异于平日行走惯使,加上身躯之重,作用于腿脚的劲力反馈,堪堪是上山的两倍;脚力不足者,下行极易磨耗,纵有内功外门护身,仍忌急切为之,稍有不慎,轻则伤筋挫骨,亦不乏劳损过度,坏了膝踝关节的。
耿照唯一学过的轻功,乃出自明姑娘亲炙。明栈雪才智之高自不待言,内外武功都是从实战里淬炼出来,不挟一丝水分。
天罗香的“悬网游墙”虽还构不上“绝学”二字,放眼邪派七玄,也算名声素著了,隐隐成为冷炉谷一脉的号记。行走江湖,但凡遇有容貌绢秀、衣着精致的女子,毋须攀爬纵跃,贴着粉壁即能轻巧游上、始终不坠者,十有八九是天罗香“玉面蟏祖”的座下——这几乎可说是武林常识。
此等为女子量身定作的武功,小巧有余,负着百来斤重的毛族大汉下山却派不上用场。
耿照上山全凭狠劲,无视原本若有若无的盘肠小径,截弯取直,走的是遇阻开路、寻隙破关的硬路子,与对敌无异;只消有一鳞半爪处可供借力,仗着当世无双的“蜗角极争”心法,就这么硬桥硬马地碾压过去。此等暴力硬解的鲁莽之行,还快过了循径奔绕的聂雨色,抢在聂二侠之前赶至战场。
万料不到,此际下山,倚仗的仍是“蜗角极争”,对抗的却非蓁莽蓊郁的大自然,而是自己。每一落足,均须卸去自身与背上韩雪色之重,将筋肉所施加的气力控制在最低幅度,同时运功护住足踝膝关等……不知不觉间,少年摒除杂念,沉入空明之境,全神贯注于协调内外三合,衣袂飘飘、足不沾地,起落间毫无迟滞,如流水行云,才有半山腰上秋、聂二少之叹。
这场自己与自己的对抗,进行得比想像中更加顺利,要不多时,山脚已近在眼前。忽然间,漫天的尘沙挟着擂地蹄声,成片地转过了谷外大道,迳朝沉沙谷内奔去。
沙尘里难辨来人衣着形容,耿照不敢冒险,忙择一矮树掩蔽。才刚藏好,蓦地一骑横里穿出落尘,自队伍前列掉头而来,鞍上的骑士加紧催缰,几乎立于镫上,但见一身皮盔皮甲,腰挎长刀,防尘用的覆面巾迎风猎猎,依稀见得面颊上一道长疤,却不是罗烨是谁?
——是巡检营!
十九娘到底还是传了讯息。耿照精神一振,背着韩雪色自矮树后起身。战马倏忽便至,罗烨“吁”的一声勒缰,未待坐骑全止,已然翻落,扶刀行礼:“属下来迟,大人恕罪。”他目力惊人,大老远便见典卫大人负着一条大汉下山,来不及发号施令,疾行间迳拨马头而来。到说话这时,本将驰入沉沙谷的百人骑队才绕完大圈,转往此间。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耿照将情况概略说了。罗烨让章成——这会儿他已非什长,罗烨拉拔他升了官,统率三支百人队之一,算是自罗、贺以下的第三号人物,营里都喊“章佰”或“章队”——领所部入谷接应老台丞,遇有秋水亭门人或杀手造次,擒先于杀。章成领命而去。
沐云色随后赶至,耿照介绍了罗、沐二人见面。沐云色见这名少年军官眸锐如鹰、气宇轩昂,绝非泛泛,颇有结交之意,碍于战阵倥偬,无暇深谈,微笑着一拱手,自此记住了这个姓字。
巡检营本是谷城大营各部汰下的顽凶难驯之徒,不乏老兵油子,经验丰富,斫了几根杯口粗细的长枝,就着绳网,在两匹马之间架起简易的担架,用以安置韩雪色,另匀了匹坐骑给沐云色,派一支什队护送他俩,先行回城就医。
那自称“翠十九娘”的女子,持典卫大人的关条到巡检营报讯时,恰巧副统领贺新正要率队出城操练。罗烨一听事态紧急,命余人速速整装,除留守休假者,举营赶赴沉沙谷;若非出城时城将刁难,耽搁些个,本应来得更早些。
在谷外要道把守的秋水亭弟子,罗烨难辨忠奸,索性缴了兵刃,连索捆起;一问之下,才知附近几条路上还有人,命贺新率部迂回而进,一一拿下,自己则率领主力长驱直入。是以谷中激斗如斯,非外头负责封锁道路的秋水亭门人浑无所觉,实是撞上一帮先捆再说、毫不讲理的流氓兵,被坚甲明戈一气围上,全成了人肉粽子,便想回谷探查一二,亦不能够。
耿照乍听颇有些哭笑不得:南宫损坐实阴谋家的指控,恶贯满盈,再无疑义,秋水亭自也逃不过“为虎作伥”的罪名,要锁要拿,就是将军一句话。按这位罗大统领全不讲江湖规矩的癖性,这般大张旗鼓地捆人,万一拿错了,此事绝难善了,只能说万幸南宫损非是无辜。
言语之间,秋霜色与聂雨色已至山脚;另一厢,载着萧老台丞及谈大人之尸的马车也出了谷,沿大路去远,只余地平线彼端一抹乌影。章成大队自谷中驰出,与罗烨本队会合,表示里外粗粗搜了一遍,没见其他人。“还是留三个什队下来,看守到谷城或越浦衙门那厢派人来接手罢?”果然当了“章佰”之后就不一样了,处事较往日精细,也算面面俱到。
耿照心中不无感慨,面上不露心思,挥手道:“全撤了罢。明儿再来。”命人备马,冲秋、聂等招手,示意速速起行。
包括罗烨在内,巡检营众人均不知典卫大人葫芦里卖得什么药,怎地脸色铁青若此,倒像鬼在后头追赶似的,忙不迭地只想走。巡检营不计留守,足有两百余骑在此,人人均是全副武装,怕连风火连环坞都闯得,有什么好怕的?
轰隆一声,半山腰上华光迸散,映出一抹屋脊檐影,整个地面仿佛跳了一跳,马匹无不惊得踩起小碎步来,众骑士的吁止声、鞭肃声此起彼落,场面登时大乱。许多人到这时,才发现山腰间似有座破落屋宇,却不知适才那道异光是真有其事,抑或自己眼花。
“呸!他奶奶的……”章成掖着马鞭揪紧缰绳,忍不住啐了一口:
“谁放的烟花炮仗?邪门——”忽见一道极细极白、电蛇般的异芒沿山窜下,快得虬髯军汉来不及喳呼,那异样的冲击仿佛已至面前——
(典……典卫大人!)
这原是谁也躲不过。若非章成福至心灵,猛夹马肚,驭着跳立不休、尚未冷静下来的坐骑一窜一扭,差一点便要将典卫大人横里撞飞,那道异芒便即穿过无数人马,径直贯穿典卫大人,如流星般逸向远方也说不定。他虽貌似鲁莽,实则小心巴结,冲撞上司的事是决计不会做的,更别说只为心上一丝不祥,纵马往大人身上撞去。
正因如此,此一变数谁也无法预料。
耿照着地一滚,起身时见黑影罩头,魁梧的马躯已占据了他原有的位子,恰恰背向山道,挡在自己身前——而下一霎,战马连同鞍上全副武装的军汉,突然绽出无数纵横交错的亮痕,粉碎的脏腑、巨量的鲜血随爆开的腔压四散轰散,将方圆一丈内的人马齐齐推出,在地面留下一枚浓渲深皲的血月亮!
章成瞠目张口的断首,与残肢、脏器、马匹尸块散在“血月”之内,漫天簌簌血雾还未沾地,便与尘沙混成一团,仿佛下起黑雨。
身形毫不起眼的灰袍人就站在血月亮的另一侧,无视周遭人马杂沓,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到来、什么时候来的,明显撕自衣摆的覆面巾掩去面目,只露一双透着残忍笑意的灰眸。
孤倾于血泊中的首级,唤醒了耿照心中的怒火。他甚至忘记要嘲讽老人戴上覆面巾一事。激怒殷横野或许无法扭转结果,毕竟能做的事已不多,总比束手就戮要强。
而除耿照外的其他人,此际才惊见阵中来了不速之客,以及爆成一地乌红狼籍的百人长,呼喝声中马蹄屹蹬,尘翻血溅,屑沫横飞,甲片、长枪、弓刀的铿撞声此起彼落,灰袍客的虚影却穿插在这片致命的戟林刀尖间乍现倏隐,连惊慌人立的战马怒蹄都沾不上衣角,灰影眨眼间越过血月泥潭,掠至耿照身前。
少年颈背汗毛直竖,握住泥血里的刀柄连鞘旋出,迅雷不及掩耳反削身后——他曾见风篁使过类似的招数,但色目刀侯的“驼铃飞斩”毕竟自血战中千锤百炼而得,耿照纵有思见身中之能,也无法凭一眼的印象复制,借的乃是回旋刀法的出其不意。
那刀原是章成挎于腰间,章成连人带马遭“道义光明指”剐碎,因指劲分断的速度太快,体内腔压不及宣泄,竟硬生生炸开;刀柄、刀身,乃至柄鞘上的铜件未损,系刀的炼条耷连着半截腰带、狮面带扣,以及辨不清是布抑或血肉的残碎,一并挥将出去,恍若铜锤流星。
毫无意外,灰袍客的残影消失在视线里,然而杀气的感应犹在。少年乘着旋势起身,刀柄一转,“轰!”催劲震碎了刀鞘,朝迸飞的木鞘、扭碎的铜件之间,猛地扎入刀尖!霜亮的长刀搠如激浪,蓦然顿止,夹入两根枯瘦的指头,动也不动。再度现形的殷横野露出一丝激赏之色,挑眉道:
“这会儿……你连我怎么出手,都猜到了八九成哪!”啧啧称奇,却未痛下杀手,犹如戏鼠之猫。
耿照不理他露骨的挑衅,刀尖倏转,手腕顷刻百转,于方寸间极尽杀着,心法转化自老胡所授的“无双快斩”,招式却与胡彦之的双剑术无一丝相类,而是自心法提炼出更精纯基础之物,直指“无双快斩”背后的不易根本——
殷横野就是要看他拼命挣扎、功败垂成,最后含恨难瞑的痛苦模样,本拟两指一合,连尖带刀绞扭成麻花一般,顺便震碎他的指掌骨轮,再乘旋扭之势,将刀柄硬生生搠入掌心,绞得整条右臂血肉模糊,撕成无数肉条。
岂料一夹之下,刀尖竟自行偏开,旋即反向劲至,顷刻间连转百度,异常刁钻的螺旋劲一霎千变,在最小的幅度内,极尽最大变化,偏偏又紧扣题旨,每一变无不是在追求杀伤力的极致,环环相扣,得理不饶!回过神时,倏忽已拆过千余转;耿照旋势不尽,化入腕间的分不清是刀剑拳脚……殷横野福至心灵,忽想起在何处见过这样的刀法。
——天狐刀!
脱胎自天下三刀之一的《稽神刀法》,天狐刀一直有声闻过实之病。“九尾飞仙”胤纵天创制的这门刀法,并没有使其后代子孙纵横东海、称霸七玄;胤玄最终得以结束狐异门的派阀分裂,使祖宗遗下的基业复归于一,仗的还是智谋权术,直到他生的好女儿,为狐异门带来一名千年难遇的盖世奇才。
殷横野从不觉得天狐刀、乃至狐异门,是一个须得忌惮的问题,毕竟当年他在湖庄来去自如,虽失却价值连城的冰火内丹不无心痛,但那本就不是首要的目标,至多是取信三槐的花红。胤玄及其门人不过守成之辈,在殷横野看来极其平庸,不值一哂。
胤丹书却不同。他所窥之秘,固令殷横野坐立难安,但胤丹书的气度人望,当然还有武功,才是最终成为隐圣目标的原因。这等殊荣当世少有,可惜胤丹书选择了自裁这条路,否则以他多年浸淫天狐刀的心得,假以时日,或能使《稽神刀法》重现江湖亦未可知。
殷横野万万想不到,竟会在此时、在沉沙谷外的荒僻山脚下,再一次亲身领会胤丹书级数的天狐刀法。
耿照所用路数、功法,固与胤丹书不同——考虑到两人毫不相类的际遇,这也是理所当然——除脱胎自天狐刀的理路若合符节,最令殷横野吃惊的,是少年无比娴熟的运刀手法。
功力靠灵丹妙药或能抄得捷径,一部失传既久、与众不同奇功绝艺,也能令初出茅庐的少年英雄比下同侪,加倍衬出凡人年月未及的平庸与悲哀。一旦将时间拉长,丹药造就的功力、奇功慑敌的优势,终会被日积月累的悟练与实战经验追上,此即为“造诣”二字的真义。
耿照际遇是够奇的了,但这些神奇的遇合,不能使他凭空得到一只使刀的手。要把刀使到这等境地,明师、正传、悟性,最重要的是年积月累夙兴夜寐,四者缺一不可,以他的年岁,绝不能有造诣如斯。屈咸亨到底对这小子做了什么,能将他调教至这等境地?
为什么……为什么你总能出我所料,总藏着你不该知晓、不应在手的筹码,总要在关键时刻出来捣乱,为什么……为什么不干脆闭目束手,乖乖接受你惨呼而亡的终局?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你……当真是令人恼火已极啊!”灰袍客咬牙切齿,怒极反笑:
“我看烦了你这些层出不穷的小把戏。死罢,典卫大人!”提劲一震,雄力压倒一切妙着变化,疾旋瞬转的螺旋刀势一霎全溃,两股相反的劲力一拉扯,刀板碎成无数指甲大小的扭曲钢渣,飕飕飕地逆卷而来!
耿照被指劲轰飞,仰头喷出大蓬血箭,碎裂的刀板犹如无数暗器刮过,割得衣衫条条碎碎,裂创披血;人还在半空中,手里光秃秃的刀柄却及时划了个圆,仿佛为此留了三分劲力,堪堪兜住一抹后发先至的细锐指风,撞出“叮!”一声激响。
耿照借力又飞出丈余,落在几匹乱踩乱踏的战马间,总算他忍痛一攀,及时抓着一条飞甩的镫绳翻上马背,没被铁蹄踩成肉泥;便只这么一来一往之间,已然脱出光明指的攻击范畴。
殷横野满以为两道接连而至的指劲能取他性命,不由一怔:“这是……蚕马刀法!这小子适才使的是《蚕马刀法》!”诧异之下,居然忘了追击。
耿照早已认清三五高手之不可敌,料定老贼恣意戏耍之余,必暗出杀着取命,专以一式蚕马刀法等他;饶是如此,也用尽了气力才挡下逼命之危。典卫大人百劫余生,单臂握缰,不忘回头大叫:
“……老贼,敢来一决雌雄!”
他实已无再战之力,欲藉骏马脚力引开煞星,以免众人填命。回见殷横野怔立当场,难得现出影形,周围马上马下几名劲卒回过神,悍不畏死,各执枪刀,正欲掩杀;一条矫健身影穿破尘沙,振臂而下,却是离鞍飞越丈余,直扑殷横野脑顶的罗烨!
(不……不好!)
指气纵横间,人头、断肢如切菜砍瓜般迸飞。殷横野身形微晃,让过了鹰一般乍落复起的少年,“咦”的一声,饶富况味:“《停空诀》、千里秋毫爪……你是‘一生自猎’,还是‘万里寒空’的传人?”罗烨足不沾地,盘旋于马首鞍顶,迅疾如电,仿佛真化成一头真人大小的巨鹰,一击不中,便要飞离。
殷横野眼神狞恶,单臂擎空,虚抓着往下一扯:“我问你话,下来!”凝功锁脉之至,原本矫矢灵动的罗烨顿失平衡,整个人被掼落地面,跌入泥血滩里。
“……罗统领!”
耿照救之不及,抄起一杆长枪射去,使的是兵法上围魏救赵的法子。枪尖发出令人牙酸的破空响,直入灰袍客身前一丈,速度遽降,终凝于三尺之前;地面泥血中,仆倒的罗烨猛然翻正,未及起身,不知从何处摸到一副鲜血淋漓的弓矢,架弦蹬弓,三矢齐放,同样射入一丈方圆,止于来人身前。
蒙面的灰袍怪客单手平举,周身诸物皆凝,恍如魔障,巡检营众人几曾见过这等奇技?俱都看呆了。
泥血里的罗烨不为所动,弓弦离手,对箭矢滞空的奇景仅瞥一眼,抓紧灰袍客尚未进击,一个空心筋斗翻起,攘臂喝道:“并辔连枪……成伍而进!并辔连枪,成伍而进!”清亮的喊叫声挟着精纯内力,响彻战场。
众人为之一震,平日里所受的严苛磨练本能相应,还未回过神来,已然掖枪踢镫、调转马头,寻左右相近者,五骑连辔,拉开距离,形成一道接着一道的小型锋线,枪尖同向一处,一般高低;离鞍坠马的,则不往尘雾里追索坐骑,擎刀引弓,就地数人成团,背靠着背,摆出接敌的阵势。
紊乱的场面转眼趋止,只余马尾扫动,似也被锁限所凝。原本飞扬躁动的黄尘不再翻涌,视线越见清澄,盔甲笼头的轮廓沉静得令人心惊,黑压压的一片,满蕴肃杀之气。
就算是这样的劲旅,在三才五峰等级的高手之前,不过填壑而已,耿照心知肚明。本想高呼“撤退”,唯恐损了士气,徒增死伤,欲唤罗烨,却见几道黄符飞入锁限,尚未全止,突然“轰”的一声,齐齐炸开;锁限为之一动,凝住的长枪、箭矢……等倏忽恢复动能,狞恶的飕飕声落,横七竖八地插了一地,居中哪还有灰袍人的踪影?
枪尖构成的锋阵之间,陡听一阵嚣狂衅笑,极是张扬:“对子狗!吃——”最末一个“屎”字未及开声,人已然弹飞出去。总算聂二侠不只厉害一张嘴,指劲逼命之际,脱手打出一蓬碾成齑粉的火油木灰,凌空沾血,一笔成箓,堪堪张开一个具体而微的消厄阵,殷横野不知由何处发出的指锋与阵同归,反激的冲击力将矮个子的聂二远远送开,恰恰躲过追击。
这手开阵之法,无疑又是稀世天才聂雨色的发明,东胜洲自有术法这门技艺,千百年来没人想过这样居然也能开得了阵,或说以术法之繁复精奥、术者的谨小慎微,没往这种花式作死的路子上发展,毋宁才是合乎情理的。
殷横野施展“分光化影”身法,穿梭于十数道锋线之间,随手杀人,踏着血肉残肢忽现忽隐,犹如鬼魅。耿照与罗烨各自擎刀扑入阵中,却不断错失标的;惨呼惊嚎声里,巡检营的军士连弃甲逃生的念头仿佛都想不起,突如其来的杀戮剥夺了思考的余裕,乃至求生的本能,只能凭借着本能掖枪并辔,眼睁睁看着前后左右的同袍分裂坠倒……
无间地狱若有形象,一定就是眼前的样子。
直到一个激越的弦声响起,仿佛能穿透头颅身体似的,扫过整片杀戮战场。
耿照率先回神,暗叫惭愧,一把扯住身后仓皇四顾的罗烨,低喝道:“别慌!指挥弟兄们离开……以进为退!”浑厚绵和的内劲透臂而入,罗烨激灵灵地打了个寒颤,蓦然省觉,拦了匹无驾之马翻身上鞍,立镫扬刀,大喝:“……跑起来!车悬之阵,车悬之阵!”凌乱的锋线闻声而动,不但重新整伍并辔,更绕圈子奔跑起来,里圈与外圈方向相反,形成数重转向相异的同心圆。
此阵战场罕用,乃谷城大营操演骑兵马术及队形的基本科目。跑起来的战马枪阵,远比静止时更要凶险,果然“车悬”一成,伤亡倏止,便以“隐圣”之神出鬼没,亦毋须甘冒奇险逞凶。
不及寻回战马的军卒,在内圈两两靠背,重新结成防御阵形;扬刀指挥的罗烨则单人一骑,跑在散圈之内,确保全军可见。最中央处,耿照把臂拉起灰头土脸的聂二,耳中听着那不似琴曲、却极具穿透力的异响,举目四眺,欲寻根源:“那是什么声音?是……秋大侠么?”
“人怎能发出这种声音,你道他是水豚?”聂雨色嗤之以鼻,一副“泥马哪来的土包子”的神气,哼笑道:“是老子送他的琴!五道八荒、宇内四海,仅此一把的天下名琴,教你长长见识!”
耿照回头喊:“罗头儿!”罗烨纵马奔近,沉肩伸臂,将典卫大人拉上鞍。耿照望向圈外,赫见山脚之下,秋霜色立于两座相隔约三丈的土垒间,左手负后,右手圈扬,那慑人心魄的异响便这么凭空而出。
(这……这是什么武功,竟能发出这等如磬神音!)
“不,不是凭空而出。”罗烨凝眸望去,沉声道:“有条丝弦般的物事,系于垒间。声音应是拨弦而生。”细瞧些个,果然秋霜色袖间隐有一抹奇异液光,像挽着把潋滟水华也似,并非空无一物。
琴瑟之所以产生音色,盖出自枵空的琴身与丝弦共鸣,并非随意在什么物事上拉引琴弦,便能发生声响,是故制琴一道学问深湛,不能轻易而得。纵于土垒间绑上弦,难不成便能将大地当作琴筝?
“说你土还不服气,胸无点墨!”聂雨色拍去头面衣衫的尘土,难掩得色,冷笑:“我给他找的宝贝,可不是老三玄律琴那样的俗物,连说是‘琴’,都有些对它不起。
“此弦毋须琴身,系上任一物事,即能逼出物中真响,可比世间一切琴筝神奇百倍。当年我在玄律之后弄来了此物,老三足足一个月没跟我说话,就知他有多介意啦。它还有个名目,我以前老嫌土,不怎么喜欢,今儿却觉应景得不得了,简直绝了。”
面色青白的小个子拍拍手,狠狠吸了口气,以手圈口,扯开喉咙:
“这玩意叫‘破野之弦’!对子狗,你的克星来啦,有没觉得脖颈凉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