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篷外面不只是云苍峰,还有武二郎、祁远、吴战威、易彪、谢艺……
差不多整支商队都在。
一个个拼命绷紧脸,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显然都听到了帐篷里的动静,还做了颇多的猜测。
程宗扬干笑道:“各位都在啊。呵呵呵呵。”
云苍峰笑呵呵道:“程小哥身体真是好啊,我这种老家伙是比不得了。呵呵呵呵……”
笑话都被人看完了,脸红有什么用。程宗扬索性厚起脸皮,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云老哥找我有什么事?”
云苍峰咳了一声,“这个……这么早来打扰,是找小哥商量点事。嗯,咱们过去谈。谢兄弟,你也来吧。”
几个人在树后找了片空地坐下。
云氏商会出面的只有云苍峰一个,显然事无大小他都能做主。
白湖商馆一方是程宗扬、祁远和武二郎。
谢艺盘着膝,从容地坐在一旁。
云苍峰快人快语。”昨晚的事就不再多说了。祁老哥也知道,再往前走,十有七八的村寨都听鬼王峒的号令,咱们撞见的事究竟是凶是吉,云某心中也没个底细。眼下咱们两支商队同舟共济,后面会再遇上什么,谁也说不准。大伙儿不妨摊开了说,各位都准备往哪儿去,看路上能不能有个照应。”
众人连连点头。
“我先说吧。”
云苍峰道:“我们云氏商会来南荒,是找一件东西,顺便作些买卖。那件东西是雇主相托,老夫不便透露。买卖倒平常,就是些丝帛绸缎。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白夷族。如果各位也去盘江南,咱们不妨一道走。情形就是这样,程小哥呢?”
祁远看了看程宗扬,说道:“南荒的规矩我祁老四知道。云执事把话说到这里,按理祁老四该给云老哥磕头的。”
程宗扬道:“还有这规矩吗?”
祁远道:“走南荒的规矩,都是不带生人的。商队在路上碰见,顶多说几句客气话就该分手,谁也不能跟着对方。”
程宗扬没想到会是这样,追问道:“为什么呢?”
“南荒的商道都是拿命填出来的,一条商道就是个众宝盆。让外人知道了线路,生意就不好做了。这里是南荒边缘,还好一些,云老哥说的白夷族在盘江以南。谁都知道白夷出产几样稀奇的东西,运到内陆就能赚大钱。但白夷族的路怎么走,知底的只有云氏商会一家。云老哥肯带咱们走这条路,等于是送给咱们白湖商馆一个聚宝盆。磕几个头都是少的。”
程宗扬笑道:“这也算是知识产权了吧,路线保密,垄断经营。”
他随口说出的词,几个人似懂非懂,谢艺眼角却跳了一下,身躯不由自主地挺直,流露出一丝杀伐的气度。
云苍峰道:“祁兄弟客气了。说实话,老夫也不是慷慨,一个是贵商馆有两位好手,一道走老夫也心安些。另一个说出来程小哥、祁兄弟莫气。白湖商馆终究是五原城的商家,就是知道了路线,一年也走不了几遭。”
云苍峰说的委婉,程宗扬已经听出来了。
他们这种小商馆跟云氏商会根本没法比,也不怕他们竞争,抢夺云氏的生意。
云苍峰不故作慷慨,直接挑明其中的利害,倒是商人本色,让大家心里都踏实些。
毕竟大伙都是行商多年,谁也不相信天上员会掉馅饼下来。
“还有一桩,”
云苍峰缓缓道:“这次我们走的是条新路,就算贵商馆知道也没什么要紧的。”
祁远和程宗扬对视一眼。南荒这地方有条能走的路已经谢天谢地了,怎么云氏商会要想着开新路?
“照以往的路线,到白夷族要走上二十多天,这条新路据说能省下一半的时间。那边催得急,我这把老骨头只好来拼命了。”
祁远试探着道:“云老哥……”
程宗扬打断他,“说白了吧。老哥这次带的人都不是你们云氏商会的吧?如果是商会出来的,不会都是一帮没走过南荒的新手──云老哥,易彪他们是不是军方的人?”
云苍峰苦笑着点了点头,“程小哥好眼力。只是此事不便多说,还请小哥见谅。不过老夫可以保证,与各位绝对无害。”
程宗扬通情达理地说道:“为客户保密是商家的天职嘛。不该问的,我们不问。但我不大明白,那条新路你们也没走过,又带了一帮新手,难道我们要一路摸过去?”
“这倒不必。不瞒几位,来南荒之前,我们云氏商会已经请了向导。讲好过了猩猩崖,在山口的熊耳铺会合。”
程宗扬没有在意,祁远却佩服到十分。云氏商会真是手眼通天,连南荒这地方都能找来向导,难怪生意能做得那么大。
云苍峰拂了拂衣袖,“老夫已经絮叨了半天,还不知道程小哥一行到南荒是做什么的?”
祁远立刻变成了锯嘴的葫芦。程宗扬只好干咳一声,“也是找一件东西。”
“哦?是去什么地方?”
在众人目光注视下,程宗扬硬着头皮道:“盘江以南。”
云苍峰点头道:“盘江以南奇珍异宝颇多,小哥要找的东西不妨说说,说不定老夫知道。”
程宗扬嗫嚅道:“霓龙丝。”
“霓龙丝?”
云苍峰眉毛皱了起来,良久摇了摇头,“这个老夫还不清楚。小哥准备去哪里找?”
程宗扬苦涩地想着:如果我知道,那该多好。
忽然一个声音说道:“是传说中霓龙出水时,留下的天丝吗?”
程宗扬扭头看着那个书生打扮的男子,激动之下,连声音都变了,“谢兄知道?”
谢艺笑着摇了摇手,“我只是听说有一种丝与霓龙的天丝很像,究竟是不是霓龙丝我也说不准。那丝七彩纷呈,比最细的蚕丝还细上数倍。思,似乎是在临近海边的碧鲮族那里。”
程宗扬一拍大腿,“没错!就是碧鲮族!”
他声音大得把众人吓了一跳。程宗扬连忙告罪:“失态了,失态了。”
程宗扬正容道:“谢兄既然知道,我就不瞒各位了。我们这次来南荒,就是要去碧鲮族找霓龙丝。与云老哥正好……正好……”
程宗扬后悔自己一时激动,多说了半句,鬼知道那白夷族和碧鲮族是不是同路,如果正好相反,好不容易补上的漏洞就又露出马脚,让人狠踩了。
谢艺插口道:“碧鲮族半海半陆,过了白夷族,再走几日就是。倒是跟云执事同路。”
程宗扬恨不得搂住这个妙人儿狠亲几口,这围解得太及时了。他一副胸有成竹的表情,笑吟吟道:“不错,与云老哥正好同路。”
云苍峰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既然如此,咱们就一道去白夷族。如果这边顺利,老夫就跟程小哥一同往碧鲮族走一趟,见识见识那霓龙天丝。”
他笑呵呵道:“放心,老哥不会跟你抢生意。”
程宗扬打了个哈哈,双方击掌定约,各自满意。
武二郎却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咱们都说好了。这位谢艺兄弟呢?”
谢艺仍带着那种好看的淡淡笑容,温和道:“在下只是想看看南荒的风土人情,回去写一本《南荒风物记》”
程宗扬大出意料,这谢艺竟然是个作家?还是自费旅行写书?
“写书的?”
武二郎哼了一声,“阁下手上的刀茧哪里来的?”
谢艺从容道:“握笔太久磨出茧子,让武兄见笑了。”
一句话把武二郎堵在那里,气哼哼说不出话来。程宗扬也有心探探谢艺的底细,笑道:“谢兄握笔,该不会用虎口吧?”
谢艺手上的刀茧集中在虎口周围,握笔的食指和中指反而平常。
武二郎不是看不出来,多半是不知道握笔跟握刀的差别。
果然,武二郎明白过来,顿时恼羞成怒:“你欺负二爷没写过字!敢睁着眼骗你二爷!”
谢艺拱手笑道:“开个玩笑,武二爷莫怒。”
他笑容并不出奇,却令人如沐春风,武二郎的怒火不自禁地消了,悻悻道:“你们这些写字的,没一个好鸟!”
谢艺拉平膝上的衣摆,淡笑道:“在下出身临安,生平从无大志,只喜游玩山水,寻幽觅胜。学些刀法只为防身之用。此番遇到诸位,幸何如之。”
程宗扬道:“谢兄就别拽文了,我们都是粗人。”
谢艺笑道:“是我的不是。月前我在清江游览十二峰,在江边看到有人贩卖一对白尾翠鸟,说是出自南荒,又谈到南荒种种奇事。谢某一时动念,便孤身上路。如果不是诸位兄弟好心援手,谢某已经是路边的枯骨。”
谢艺眉峰一扬,慨然道:“既然诸位都要往碧鲮族,如果诸位不嫌弃的话,谢某也有意一睹南荒海滨的风光,为拙作添上一抹异域风采。”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云苍峰道:“那好,咱们就一道走。大家都是六朝人,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祁远把酒葫芦递给程宗扬,小声道:“程头儿,碧鲮族我去过一次,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霓龙丝。那谢艺从来没来过南荒,他是怎么知道的?”
程宗扬暗叹,祁远真是个明白人,根本就不提自己的事,只是提醒自己,谢艺说的未必靠谱。
但程宗扬对南荒的见识,还不如那个一次没来过的谢艺。
只好含糊道:“放心,咱们吉人自有天相,肯定能找到霓龙丝。”
他把事情推到老天爷身上,祁远也只能缩了缩脖子,听天由命了。
走了一阵,祁远忽然一拍额头,火烧屁股地跳下马,剥树皮、扎草结、作标记,忙得不亦乐乎。
“要走猩猩崖,马车上不去,后面的不能来了。留个标记,让他们回白龙江口等咱们。”
程宗扬想起来后面留的马车和奴隶,昨晚的火光他们多半也看到了,不知道在后面怎么急呢。
天色依然阴霾,厚厚的云遮蔽了阳光,虽然是白昼,却如同黄昏。
一行人睡到中午才起身,程宗扬又跟凝羽亲热一场,算算时间,这会儿应该是下午三、四点──嗯,也就是他们说的未末申初时候。
路上又过了一条河,到了傍晚,一直令人担心的阴云忽然散开,露出满天云霞。
程宗扬戳了戳祁远,“老祁,晚霞出来了。明天是晴是雨?”
祁远道,。”南荒这鬼天气,作不得数。出着太阳都能下雨。”
武二郎却笃定地说道:“这是胭脂红。黄昏起胭脂,不风就是雨。半夜肯定下雨。”
商队没有武二爷能骑的马,再壮的马匹让二爷一骑,就跟猛张飞骑着条大狗似的。
没有马车,武二爷只好走路,他站在地上跟骑马的程宗扬差不多高,步子一迈开丝毫不比马匹的速度慢。
石刚插口道:“胭脂红那是海边,这里离海还远呢──二爷说的没错!半夜肯定下雨!”
武二郎哼了一声,收回猛虎噬人的目光。忽然他朝左右看了看,鬼鬼祟祟地凑到程宗扬耳边,小声道:“喂,你怎么把她勾上手的?”
“男欢女爱嘛。怎么,武二爷看着不爽?”
武二郎悻悻道:“那丫头冷冰冰的,二爷还以为她是个石女。早知道,二爷就……”
程宗扬一鞭子抽过来,“休想!”
武二郎浑不在意地挨了一鞭,拨眉挤眼地嘀咕道:“那丫头身段还行,皮肤白白的,奶子鼓鼓的……”
程宗扬嘿嘿一笑,“有这闲工夫,不如琢磨琢磨你嫂子。我瞧潘姑娘就不错。”
武三郎立刻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萎了下去。
程宗扬在他腰上捣了捣,“喂。”
武二郎阴着脸迈开大步,撵狗一样直躐出去。
过了一会儿,一个粗砺的声音杀猪一样唱道:“小乖乖来小乖乖!哥来说你来猜!什么长长长上天!什么弯弯照月边!什么开花红艳艳!什么挂果白酥酥!
小乖乖哎小乖乖,哥来唱你来听……”
程宗扬两手捂着耳朵,最后忍不住叫道:“谁给我杀了武二那厮!我出一个铜铢!”
老天爷到底没给武二郎面子,雨一夜都没下,早晨起来反而放了睛。云自如絮,天蓝如洗,竟是半月来难得的好天气,令人心畅神快。
不过程宗扬顾不上去找武二郎谈论“胭脂红”的概念,他一个晚上都跟凝羽缠在一起。
经过白天的尴尬,程宗扬放弃了不够安全的帐篷,带着凝羽溜进丛林。
南荒的毒虫虽然厉害,有凝羽在也不必担心。
倒是武二郎那种无赖不得不防。
那晚程宗扬没有用红色的药片。他很直接地告诉凝羽,那种“巫术“并非好事,长期使用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和程宗扬猜想的一样,停止服药的凝羽出现了戒断反应。
心跳比平常高出一倍,汗水不断涌出,却浑身冰凉。
幸好她服用的量一直很小,才没有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而凝羽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始终一声不吭。
“现在,没有\'巫术\',我也能很开心了。”
凝羽捧着程宗扬的手放在赤裸的胸前。
“你被蛇彝人咬穿脖颈的一刻,我的生命就是你的。”
程宗扬终于知道了凝羽转变的缘由。他说:“每个男人都会那样做吧。”
“但我只遇到一个。”
这也许是凝羽的不幸,却是自己的幸运。程宗扬很想知道凝羽生命中第一个男人是哪个混蛋,让她变得那样讨厌男人,但终于还是没有开口。
后来,凝羽告诉他,在她一生中,都没有像南荒之行那样开心过。
当他开始使用“巫术”的时候,所有的悲伤和痛苦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法言说的喜悦和满足。
在程宗扬的“巫术“中,凝羽感觉自己仿佛获得了飞翔的能力。她可以像每个族人一样展开洁白的双翼,骄傲地在星空下翱翔。月光如水一样从羽翼间淌过,一摇就洒下无数星辉。
两支商队决定同行之后,众人重新整理了行装,把携带的物品平均分摊,减轻马匹的负重。
白湖商馆带的货物不少,药物、盐巴、布匹、器皿还有新酿的美酒,样样俱全。
相比之下,云氏商会就老到得多,只带了上百匹绸缎,既轻便又所值不菲。
那些绸缎都不是最上等的货色,但颜色鲜明艳丽。
南荒人最喜欢大金大红的喜庆颜色,对质地并不在意,六朝最上等的绫罗绸缎,反而不如这些销路好。
祁远看着,一一记在心里,下次再走南荒,也要带些这样的丝绸。
分过货物,众人行进的速度快了许多。
过了蛇彝村之后,道路越来越荒芜。
吴战威举起砍刀,将一株蕨类植物巨大的叶片从柄部砍开,然后抡臂砸断。
栖居在叶片下的爬虫和黄蜂四散飞舞,落在身上的都被吴战威举起巴掌拍死。
易彪跟在他后面,将折断的枝叶扔开,清出狭窄的路面。
在南荒湿热的环境下,许多植物都生长得出奇的高大,芭蕉宽阔的叶片能长到十几米高。
一丛芭蕉提供的荫凉,就能容纳他们整支商队,完全超乎程宗扬的想像。
祁远早已是见怪不怪。”前几年我带着商队从拢水蛮的沼泽经过,十几里的路,都是踩着睡莲叶子过去的。那叶子有一尺多厚,几丈宽,上面连马都能走。
南荒有些地方,几万年都没人走过。那东西都长得邪门极了。”
“就说咱们要走的猩猩崖吧,崖壁平得跟镜子似的,在下面看不到顶。全靠一根老藤上下。武二郎算高的了吧?那藤比他横过来还粗,斜着攀在崖上,天生一道山梯,人马都能通行。这还不算大的,在大山深处,据说还有一棵神木,树冠比山还大,一眼看不到边。”
程宗扬嘀咕道:“这南荒不会是被辐射过吧,听着怎么像变种呢?”
途中又过了条河,地势渐渐升高。身边的植物愈发茂盛,脚下的小路却越走越窄,最后干脆消失在密织的丛林间。足。
在程宗扬的“巫术“中,凝羽感觉自己仿佛获得了飞翔的能力。她可以像每个族人一样展开洁白的双翼,骄傲地在星空下翱翔。月光如水一样从羽翼间淌过,一摇就洒下无数星辉。
两支商队决定同行之后,众人重新整理了行装,把携带的物品平均分摊,减轻马匹的负重。
白湖商馆带的货物不少,药物、盐巴、布匹、器皿还有新酿的美酒,样样俱全。
相比之下,云氏商会就老到得多,只带了上百匹绸缎,既轻便又所值不菲。
那些绸缎都不是最上等的货色,但颜色鲜明艳丽。
南荒人最喜欢大金大红的喜庆颜色,对质地并不在意,六朝最上等的绫罗绸缎,反而不如这些销路好。
祁远看着,一一记在心里,下次再走南荒,也要带些这样的丝绸。
分过货物,众人行进的速度快了许多。
过了蛇彝村之后,道路越来越荒芜。
吴战威举起砍刀,将一株蕨类植物巨大的叶片从柄部砍开,然后抡臂砸断。
栖居在叶片下的爬虫和黄蜂四散飞舞,落在身上的都被吴战威举起巴掌拍死。
易彪跟在他后面,将折断的枝叶扔开,清出狭窄的路面。
在南荒湿热的环境下,许多植物都生长得出奇的高大,芭蕉宽阔的叶片能长到十几米高。
一丛芭蕉提供的荫凉,就能容纳他们整支商队,完全超乎程宗扬的想像。
祁远早已是见怪不怪。”前几年我带着商队从泷水蛮的沼泽经过,十几里的路,都是踩着睡莲叶子过去的。那叶子有一尺多厚,几丈宽,上面连马都能走。
南荒有些地方,几万年都没人走过。那东西都长得邪门极了。”
“就说咱们要走的猩猩崖吧,崖壁平得跟镜子似的,在下面看不到顶。全靠一根老藤上下。武二郎算高的了吧?那藤比他横过来还粗,斜着攀在崖上,天生一道山梯,人马都能通行。这还不算大的,在大山深处,据说还有一棵神木,树冠比山还大,一眼看不到边。”
程宗扬嘀咕道:“这南荒不会是被辐射过吧,听着怎么像变种呢?”
途中又过了条河,地势渐渐升高。身边的植物愈发茂盛,脚下的小路却越走越窄,最后干脆消失在密织的丛林间。
“祁四哥!”
小魏在前面嚷道:“该往哪边走?”
祁远爬上来打量了一下,“那边!那棵大椿树后面!”
那棵椿树直径超过十米,树身不知什么年月被雷劈掉半边,一半已经桔死,犹如炭化的岩石,被雨水冲刷得乌黑发亮。
另一半却枝繁叶茂,只剩一半的庞大树冠巍然挺立,犹如一顶残缺的大伞。
众人在树旁称事休息,武二郎大概是前些日子睡了一路,这会儿毫无疲态。
他三步并两步攀到树上,去扯爬在上面的藤蔓。那藤蔓粗如人臂,上面开着不知名的紫色花朵,每一朵都有脸盆大小,形似金盏。
武二郎伸手一扯,一朵紫色的花盏倾斜过来,泼出一汪清水。
原来前天暴雨如注,这些花盏里都盛满了雨水。
鹅黄色的花蕊在水中浸得膨松,像粉球一样又软又大,散发着淡淡的香味。
南荒天热,气候潮湿,一路走来,每个人都是一身臭汗。
武二郎玩心大起,就那么脱了衣服,赤着虎纹遍布的彪壮躯体,拿花盏里的水浇了一身,一边洗一边大呼痛快。
树下石刚跟几名护卫大声叫好,让武二郎更是爽快。
武二郎披着衣裳跳下来,程宗扬抽了抽鼻子,赞道:“二爷这场好洗,倒像个香喷喷的粉头。”
武二郎嘿嘿笑道,“哪儿有你那小姘头洗得干净。”
程宗扬一怔,接着险些气炸了肺。”武二!你这个不要脸的,敢偷窥!”
“好端端的帐篷不睡,非跑到二爷眼皮底下鬼混。二爷不看还是男人吗?”
武二郎得意洋洋地晃着肩走远,还在背后很贱地比了个手势。
云苍峰咳了一声道:“过了猩猩崖,有一截好路,如果顺利的话,今晚咱们就能赶到熊耳铺。”
祁远道:“都听云老哥安排。”
凝羽面色如常,似乎没听到武三郎的戏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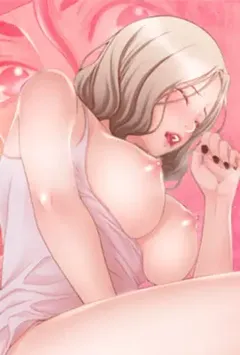





![[刀乱]逆大奥](/d/file/po18/785284.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