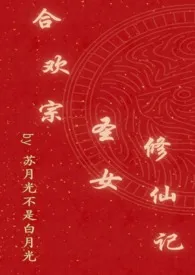连月笑了笑,没有说话,手里慢慢的剥着的橘子。
位置越高,责任越大——她真不想当处长。
勾心斗角太累了吧。
也可能是因为她还没品尝过“权利那令人疯狂的滋味”。
以前她是有一股心气劲儿的。
年少的时候她心里憋着一股气,挣扎着想要逃出那个烂泥坑。后来,是想着怎么也要把妈妈养好了——
命运给了她一个极差的开局,可是她咬着牙也撑着要把它打到最好。
她心很小,没有什么宏图大志,只装的下自己的那一点小心事:
把妈妈那一个月一两万的诊疗费付了,做好自己那个收入还算不错的工作,再有个小小的栖身之地就够了——最好不用还房贷,能多存点钱,那就更完美了。
就连什么爱人孩子,她都不敢想。
生活的重压压在肩上,连基本生活都需要咬牙坚持的时候,道德不过都是扯淡的东西——什么为国为民,宏图大愿,离她太遥远,她没有那个想法。
当年去J国的时候,她的心里虽然惶恐,却尚有一柱支撑。到了妈妈走的那刻,撑了她那么多的心劲儿,似乎也轰然倒塌了。
然后她才后知后觉到领悟到,原来这么多年,自己是那么的疲惫。
那时候她突然明白,其实极大部分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就如浮萍,随机漂流在出身,国运和大势的海面上。
唯有权贵们才能翻天覆地,翻云覆雨,搅动这无边的海。
橘子剥好了,连月伸手,把它递给了自己旁边这个资深权贵家族的代表,男人伸手接过了,又笑嘻嘻的往她那边挪了挪。
两人的距离还隔着有半米,连月懒得理他。
桌面上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她拿起来一看,同事发来的。
问她户口积了多少分了。
S城凭积分入户,连月回国才六年,只有一个本科文凭,证书倒是有几本,加加减减,入户都还差了几分。
“我这两天算过了,都还不够呢,”她回复,“社保要连续交十年,我才六年。”
“唉,真不知道小孩念书要怎么办,”同事回复的言语间颇有些焦虑,“A校倒是很好,第一梯队,就是对口的那两个小区八九万一平,300多万买个30多平的城中村老破小——根本不可能住人。”
连月拿着手机,想起来自己这趟去海边,居然忘了和季念商量这件事——主要是季然太小了。
时代不一样了,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她和季念都不是本市户口,是不是应该喊他拿钱去买老破小了?先把户口落过去?
钱她是没有的,AA制嘛,这个钱该他出。
当时结婚的时候他自己说孩子归他养来着。
这边的权贵代表吃着橘子,又挪了几下,凑过来看她的手机,嘴里一边再说,“和谁发信息这么开心呢?老四?给我看看——”
“户口?”
男人看见她发的信息,难以置信的看了她一眼,又一下子笑了起来,“你想要S市户口?怎么没听你说过?还真老实啊连月——你现在户口哪里的?”
连月皱眉,往旁边挪了挪,“不要你管。”
“怎么也没听老四说?”喻恒还在一边吃橘子一边说,“你拿这个户口来干嘛?我来给你弄。”
连月不理他。
“我现在就问啊,”男人把橘子放桌上,开始掏手机,“简单,你看我的。”
“哎呀你先别问,”连月看他真的就要翻通讯录,伸手去把他手机屏幕按住了,“我先和季念商量下。”
“多大点事儿,还要老四批准才行?”
男人伸手去抓她挡着自己手机的手,又笑,“等他从阿三国回来,这事都办完了。”
“不是问这个,”
手被他的手握住,连月拿起甩开,又要去按他的手机,“我就是先和他商量下季然以后哪里读书——”
“随便读读呗,”男人又去握住她的手,一脸无所谓,“想去哪里读,去哪里读。”
“去。”连月呸了他一声,又把他的手甩开了。
教育很重要。
她的切身经历,切身体会,切身感受。
读书改变命运来着。
“不是什么大事,你们女人就容易焦虑,””男人还在说,“其实都一样。挑好的上就行了。幼儿园呢,随便读读;小学呢,你要是舍得,就送去京城和喻成念一个学校——”
“我舍不得。”连月笑。
喻成读的什么学校,她听妈说过。
根本不对外招生来着。
“那就随便念念,请点家教咯?”男人笑,“你真的不用想太多,老四心里会没数?咱们家一堆哈佛校友,搞个校友分会都够了——到时候高中毕业,写两封推荐信,往哈佛一送,妥妥的,你愁啥?”
“这么简单?”连月笑,“总还是要他努力学习吧?”
“努不努力都无所谓,就是这么简单啊连月,”
喻恒扭头看她,笑得奇怪,“你脑子里都想啥?你还以为季然要走你走过的老路呢?他需要吗?”
“他姓季,享受的是季家的资源,生来就有亿万家产继承——他都含着金钥匙出生在终点了,你还准备着要他和谁比拼起跑线呢?”
女人扭头看他。
“啧啧啧,”男人又在摇头叹气,“怪不得咱们家的孩子都要父亲来教育——女人的眼界好像是不行。唉哟!”
当朝权贵被一个女人当“厅”踢踹殴打,权贵站了起来,一边躲闪一边还说,“连月你够了哈,我是看你是孕妇才让着你——老大叫你不上班果然是对的,你再上都要上傻了,天天和同事嘴碎,连自己家什么情况都不关心来着。”
“别打了,小心动了胎气,老四要打死我。”
“户口你还要不要?你再打我不给你弄了。”
“我说错话了行不行?我们家的女人都聪明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