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槐县城近郊一处村落,一间泥土房内。
屋中燃着炭盆,屋外早春不冷,屋内更是温暖如春,那榻上年轻男子却瑟瑟发抖,不住看向门外。
他面前桌上,摆着刚凉下去的酒菜,杯中残酒已冷,盏中菜肴犹温。
男子站起身来,在地上来回踱步,不时看向门外,夜风阵阵吹拂进来,与屋中火炭热流冲撞,让人又冷又热。
一道清风拂过,院中忽然多了一人,他身形高大结实,身上一袭青色道袍,望之仙风道骨、洒脱超然,不似寻常人物。
“公子!”年轻男子面上神情瞬间生动起来,又是希冀又是畏惧快步冲出门去,冲来人深深一礼,关切问道:“公子终于来了!我姨娘如今可曾还家?”
彭怜笑着摇头,“诸事未定,哪里能轻易让薛夫人还家?高公子在这里住的可还习惯?”
高文垣嘴角抽动,想要发怒却又不敢,良久才道:“这里每日有人伺候,日子倒也算过得去……”
彭怜点头笑道:“小弟照顾不周,倒要委屈高公子多住几日了。”
高文垣眼中闪过一抹恨意,却不敢表现出来,只是低下头来强忍怒意。
彭怜拂过桌面,上面干净至极,竟是纤尘不染,不由暗暗点头,自己租了间农家小院,请了两个仆妇照顾高文垣起居,这屋子收拾得如此干净,这两个仆妇倒是尽责。
此处无人看守,高文垣却根本不跑,明知将来到官府自首便是难逃一死,却仍能挺到现在,如此痴情,实在出乎彭怜意料。
当日练倾城将那薛氏交给教中弟子送到省城交给雪晴严加看管,却对高文垣不闻不问,只说他与妇人痴情,断然不会弃置不顾,如今看来,练倾城识人之明实在过人,这高文垣当真是个痴情种子。
“你那薛姨母每日里锦衣玉食,倒是不需你来惦记,”彭怜随意坐下,“我且问你,高家诸事,你可曾参与其中?”
高文垣茫然摇头,“高家又有什么事了?”
“难道你不知高家强抢民女、霸占良田之事?”彭怜看着眼前男子比自己还要年长几岁,却一副懵懂模样,不由心中暗叹高家教子无方。
“这有什么!”高文垣嗤之以鼻,在榻上坐下,不以为然笑道:“公子看着不似常人,岂不知富贵人家大都如此么?溪槐方寸之地,高家一家独大,倒显得突兀了些,若是在省城,这事不是每天都有么?”
彭怜从樊丽锦处出来,便直奔此处,他心中有些担心高文垣逃了,又确信练倾城眼光,因此过来查看,此刻放下心来,见高文垣如此不以为然,暗笑自己迂腐,此人能为情弑父,可谓几无人性,自己与他说这些无异于对牛弹琴。
他怜高文垣痴情,有心就此放二人一马,如今看来,实在是多此一举。
彭怜站起身来,对高文垣道:“你我约定在先,择日你到县衙自首,我便放薛氏回府,盼你遵守约定,若是不然……”
高文垣连忙起身,恭谨答道:“高某断然不会违约,以致姨娘身陷险境!只盼公子信守然诺,莫要诓骗于我才是!”
彭怜点点头,“如此你便在此安心住着,等我消息便是。”
不理高文垣如何恭谨,彭怜闪身出门,倏忽消失不见。
高文垣揉揉眼睛,心中畏惧之意更加浓郁,整夜辗转难眠,倒是无人知晓。
彭怜离了高文垣住处,连夜回到县城,潜踪匿迹进了高家后院,来到雨荷房中。
子夜已过,窗外漆黑如墨,妇人房中亦是昏黑一片,彭怜轻车熟路,先去封了丫鬟穴道,这才悄悄钻入雨荷床帐之中。
床上妇人穿着雪白中衣,被子盖在腰间,此时斜斜躺着,露出半边白腻胸脯,漆黑夜色中,更显一抹莹白。
彭怜目力极佳,自然看得真切,他刚试过樊丽锦风情,本已心中淡然,一见妇人妖娆,却又不觉情动。
他也不去叫醒雨荷,只是解去身上道袍,随即悄悄掀开被子,将妇人绸裤褪到膝弯,便挺着粗壮阳根,对着雨荷淫穴缓缓推入。
雨荷猛然惊醒,刚要叫喊便觉出不对,随即呓语笑道:“好爹爹,怎么是你来了?”
彭怜一乐,随即笑道:“雨荷为何没有惊叫出声?”
“女儿初时以为是那高文杰突然来了,自然心中惊惧,待到阴中充实胀满,便知是爹爹来了,自然便放下心来……”妇人右腿蜷曲叠在左膝之前,斜斜拧过身来,探手抚摸彭怜手臂,娇吟不已说道:“好爹爹……还是这般粗壮……只这般进来……便让人心里快活……”
彭怜对着妇人饱满肉臀抽送不已,笑着说道:“多日不见,雨荷的淫穴也更加紧窄了呢!”
雨荷自己掰着丰满肉臀,方便自家便宜爹爹抽送,娇羞说道:“这些日子高家大爷来过两次,女儿都说身子不适,没让他沾身……女儿这般为爹爹守贞,还请爹爹怜惜!”
彭怜一愣,练倾城身在风尘,与自己相识之前便已不再接客,与自己结下良缘后更是淡出青楼生意,如今安心做彭家妇,自然而然为自己守贞;至于练倾城几个女儿,本来就是风尘中人,迎来送往、生张熟魏本就情理之中,彭怜从未想过也从未要求谁为自己守贞。
不想今日雨荷竟主动如此,他先是惊讶,随即颇为感触笑道:“雨荷这番心意,却让为父感动莫名,你若果然从此洁身自好,为父说不得要给你个归宿才是!”
雨荷神情娇媚,面上满是奉承之色,一边浪叫一边娇声软语道:“女儿从良日久,早就过不惯那般生张熟魏的日子,只求有情郎长长久久,哪里还肯夜夜笙歌?”
彭怜纵意抽插,点头笑道:“如此也好,到时与你置个宅院,做个彭家外室如何?”
雨荷眼神闪过一抹黯然,嘴上却笑道:“女儿残花败柳之姿,能有如此际遇已是邀天之幸,还要多谢爹爹怜爱……”
彭怜将她神情变化看在眼里,叹息说道:“为父家中境况你并不知晓,便是你娘也只是妾室身份,你若真个入府,最多能有一处房屋一个丫鬟,总归无名无分,何必去寻那寄人篱下烦恼?”
雨荷早听练倾城讲过,彭宅门禁森严、姐妹众多,自家母亲尚且只是小妾,自己若真个过府,只怕更是不堪,心里这才舒缓了些,嫣然笑道:“女儿可不敢要什么名分,真要能得爹爹置办一间外室生活,时常得爹爹母亲勤来看顾,便也不虚此生了!”
彭怜点头笑道:“自该如此!俗语云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到时为父夜里来偷会雨荷,岂不两全其美?”
二人说开心结,自然更加蜜里调油,欢愉几度,雨荷丢了数次,终于哄出彭怜阳精,这才搂着继续说话。
妇人身上一袭抹胸横陈,只遮住半边椒乳,更增一抹魅惑之色,彭怜夜能视物,看在眼里自然心中欢喜,他抱紧雨荷,轻声问道:“年后这几天,你可见过那高文杰?”
“他来女儿房里两次,都是夜里过来,想要求欢都被女儿推拒,只是说了会话……”雨荷拱入少年怀中,只觉昏昏欲睡。
彭怜又问:“他可曾说起,意图刺杀我与你娘?”
雨荷悚然而惊,猛然坐起问道:“还有此事?他却从未说起过!”
彭怜将她搂着躺下,简单说了事情经过,这才又道:“对方手段拙劣,用心却也险恶,如今之计,这高家只怕不能再留了……”
“爹爹可有计较?”
“我已安排你娘去给蒋明聪送信,等他驾临溪槐,便是高家覆灭之时……”
彭怜心中,本来对覆灭高家心有顾虑,谋反乃是不赦之罪,真要坐实,高家便要满门抄斩、鸡犬不留,上天有好生之德,若是因为自己多伤人命,心中总有不忍。
便如蒋明聪所言,为天下生灵,高家人死一死也无不可,于彭怜而言,终究不是如此简单。
只是高家如今倒行逆施,天长日久,莫说地牢中的冷香闻出些变故,便是彭怜自身都要受到殃及,他如今一家老小,却不肯为此甘冒奇险。
父女两个绸缪半夜,彭怜在雨荷房里睡下,临近天明这才悄然离去。
翌日清晨,彭怜召集县学诸位僚属,商议今年招纳生员等事,他无心琐事,一切便沿袭旧制,好在几位僚属极是得力,定了章程便各自散去,省去许多麻烦。
彭怜无事可做,想起昨夜樊丽锦风情,心中便有些难耐,思来想去,便遣人备了些绫罗绸缎各式礼品,觑着吕县令外出,来县衙拜会。
吕锡通不在县衙,下人不敢怠慢,便将彭怜请到衙署后堂,这才进去禀报樊丽锦。
彭怜端坐饮茶,时间不大,只听脚步轻响,却见一位貌美妇人从门后转了出来。
樊丽锦头上梳着圆髻,簪了两枚翡翠簪子,两耳挂着红宝石耳坠,面上脂粉淡抹、腮红两朵,眉眼中满是秋波,一袭淡紫襦裙,脚上一双金丝白绫高底鞋,随着步履若隐若现,竟是好不勾人。
彭怜知道那襦裙之下一双美腿何等风光,眼睛便有些看个不够,若非樊丽锦身边还有丫鬟跟着,只怕当场便要将她推倒亵玩。
樊丽锦眼神火热,神情却是淡然至极,款款走上前来,对彭怜不冷不热淡然说道:“彭大人来的可是不巧,外子有事出去,不知何时方能回来。”
彭怜恭谨行礼,目光灼灼看着美妇笑道:“倒是下官鲁莽,未知大人行止便来叨扰,还请夫人恕罪。”
樊丽锦云淡风轻,仍是冰冰冷冷不假辞色,自然在上位款款坐下,擎起碗盖拨弄盏中舒展茶叶,随意问彭怜道:“彭大人此来,不知所为何事,若非事涉机要,不妨留下话来,由妾身代为转达。”
彭怜抬头看了眼樊丽锦身边丫鬟,心领神会故作为难说道:“倒也不是如何机密之事,不过……”
樊丽锦也不回头,吩咐丫鬟说道:“芝儿且去门外守着,莫要外人进来打扰。”
小丫鬟连忙躬身答应,快步出门而去,只是站在门前廊檐之下,并不远去。
中堂房门大开,光天化日之下,任是谁如何异想天开,也绝难相信,县令夫人会与县学教谕畅叙私情。
彭怜觑着丫鬟远去,这才小声对樊丽锦说道:“昨夜一晤,至今朝思暮想,仍是心潮澎湃,锦儿可曾想我?”
樊丽锦面上仍是云淡风轻神态,两腮却忽然飞起两朵红晕,眼神更加火热滚烫起来,娇羞点头说道:“奴也是如此,只道今夜才能再见郎君,谁料相公大白天的便即来了……”
彭怜笑道:“如今我才算明白,何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只这半日之间,便如经年累月一般!”
“奴昨夜睡得香甜,早饭却没什么胃口,心里只是想着相公何时再来……”说及娇羞处,樊丽锦抬手掩面,偷着看了门外一眼,见丫鬟端正伫立,心中放下心来,“好相公,奴……”
彭怜与她心意相通,哪里不知妇人心意,轻飘飘一跃而起落到樊丽锦身后,将她臻首扳过靠着椅背,随即深深热吻起来。
樊丽锦床笫间风情无限,偏偏面上却又端庄持重,彭怜与她之前见过几次,只道妇人端庄守礼,哪知道她床笫间那般淫媚?
世间男子最喜妇人明里暗里各自不同,所谓“上得厅堂、入得闺房”便是如此,若非樊丽锦如此反差极大,以彭怜这般花丛老手,哪会如此心荡神驰、恋奸情热至此?
若非昨夜他有事在身不得不去,只怕还要多留宿半夜才肯离去,今日冒险前来,更是情难自禁。
樊丽锦身躯火热,任情郎予取予求,不多时已是娇喘吁吁、情难自已。
彭怜知她情动,又怕弄伤她脖颈,亲热片刻便即松开,只是双手探入妇人衣间,握住两团绵软椒乳,细细把玩起来。
樊丽锦恪守妇道,便是心中如何好色,也绝不与人稍假辞色,只因她身为官员内室,深知一步行差踏错便是万劫不复,若非万无一失,断然不会轻易冒险行事。
昔日柳芙蓉正因有此顾虑,才迟迟未能与家仆成奸;那白玉箫不是遇到彭怜这般飞檐走壁如履平地之人,也绝不会轻易失贞定下奸情;这樊丽锦虽不如二妇显贵,心机城府却犹有过之,不是自渎之际被彭怜趁虚而入,实在太过机缘巧合,只怕便是彭怜显露神功,她也不会轻易动心,甘冒如此奇险与丈夫下属勾搭成奸。
自来大户人家妇人勾搭男子,若是私会外边男子,每每墙里墙外搭起梯子,有那胆大包天的,便开了角门请进门来,只是如此大吵大嚷,自然瞒不过旁人耳目,纵如何机密,终有露出马脚的时候。
只因男女恋奸情热,情到浓处便无所顾忌,只求一夕之欢,哪管之后洪水滔天?
便到时如何捶胸顿足、追悔莫及,当时却是心存侥幸、不以为然。
当日便是江涴那般心机深沉之人,对爱妻白玉箫起疑,也只是防着家中小厮不许近前,哪曾知道世间还有彭怜这般飞檐走壁如入无人之境之人?
举凡世间有此修为之辈,又有几人会以此为凭寻芳猎艳?
世间女子遇到彭怜自然便是三生有幸,她那夫婿若是在世,却是遭了劫难。
便如今日樊丽锦一般,明明二人昨夜才勾搭成奸,今日便恋奸情热重聚一处,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便于县衙后院中堂白日宣淫,虽未真个欢好,期间蜜里调油,却胜似寻常男欢女爱。
那妇人樊丽锦非是贪淫好色之辈,只是人近不惑之年,情欲渐生,偏偏丈夫又不堪大用,正是闺怨正浓,偏又阴差阳错遇见彭怜这般花丛高手,骤然识得男欢女爱人间极乐,自然便沉醉其中、不可自拔。
彭怜床上了得,偏又人物风流,樊丽锦得了她,便如久旱逢甘霖一般,情欲醉人,自来如此,尤其男女偷欢,更是引动春心,让人情难自禁。
樊丽锦被彭怜揉的娇躯酸软、娇喘吁吁,只是仰头看着身后年轻俊俏情郎,娇媚哼道:“好相公……这般揉搓人家……着实让人难过……不如……不如……”
她言犹未尽,彭怜却领会于心,转头看了眼门外丫鬟,低声笑道:“春日衣衫繁复,真若欢好,只怕人来时不便处置……”
樊丽锦面色绯红,一双秋水凝眸滴溜溜一转,随即嫣然笑道:“奴有法子,还请相公回去坐着……”
彭怜从善如流,轻飘飘跃回自己座位坐好,却见妇人随手一挥,将那桌案上名贵瓷器打到地上摔得粉碎,借着弯腰捡起一片碎瓷,这才招呼外面丫鬟进来收拾。
丫鬟手脚麻利,很快将地面清扫干净,趁她出去当口,樊丽锦将瓷片递与彭怜,笑着说道:“相公用此划破奴的绸裤,便能随时取用奴的淫穴……”
妇人智计百出,这番布置倒是出乎彭怜预料,他接过瓷片,不由莞尔笑道:“若是仅仅如此,倒是不必这般麻烦……”
樊丽锦有些莫名其妙,只见情郎起身过来将她扳过身子趴在桌上,随即撩开厚重罗裙,妇人回头去看,却见彭怜并不用那锋利瓷片,竟是戟指成剑,随意轻轻一划,便将那裙下绸裤划出一道口子。
妇人早见过彭怜施展轻功,如今见他手掌竟能锋锐如刀,眼中更是异彩连连,情不自禁崇慕说道:“相公文武兼备,竟还有这般手段,倒是奴多此一举了!”
彭怜撩开自己身上道袍露出昂扬下体,对着妇人绸裤破处挺身而入。
樊丽锦骤然快意,情不自禁呻吟一声,随即娇羞说道:“好相公快些弄……一会儿丫鬟要回来送茶的……”
“不妨的,她走进十丈之内我便能听到脚步声,锦儿且安心享受便是……”彭怜得意抽送,动作却是极快,他有心在丫鬟回来之前便让樊丽锦快活一回,自然用尽千般手段、万分力气,将那樊丽锦弄得神魂颠倒、欲仙欲死。
他自己也心中快活,无意中得了樊丽锦这般淫媚妇人,尤其对方还是自己顶头上司的娇妻,亵玩起来自然更加刺激非常。
不过三百余抽,彭怜便觉精关松动,他也丝毫不加控制,抖擞泄出数道阳精,为妇人补益身心。
樊丽锦早被少年情郎这般排山倒海的肏干弄得死去活来,此时被阳精一烫,险些美得昏晕过去,她檀口大张无声呐喊,如是良久,才缓过神来,娇滴滴回头嗔道:“奴都要被相公肏死了……”
“这算……”彭怜满脸得意,忽然神情一紧,低声说道:“不好,大人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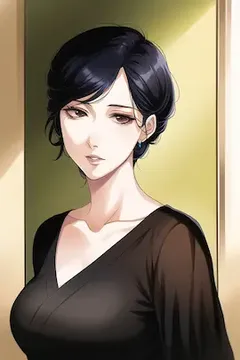

![Blizzard 暴雪 [SD][流花]](/d/file/po18/663649.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