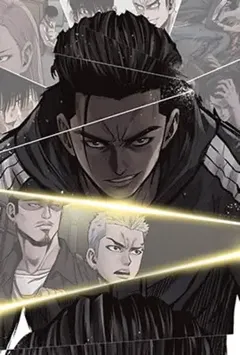东方刚刚露出一点儿鱼肚白,太阳似乎还没睡醒,迟迟的不肯从摇曳浓密的芦苇荡中钻出来。
昨天傍晚终于下了雨,不大,却稀稀拉拉地掉了一夜,直到凌晨时分,才慢慢地停住。空气中仍旧弥漫着浓浓的水汽,把个朦朦胧胧中的杨家洼,衬托得愈发若隐若现,却干净透亮得像刚从画儿里跳出来一样。
吉庆起了个大早,一个人悄悄地提了水桶,水桶里面满满实实地塞了一张网,又扛着铁锨喵悄儿地出了家门。
船都预备下了,是二蛋儿家的。二蛋儿舅舅打过鱼,置办下一条船,头年当兵走了,船却留给了二蛋儿家。平日里也没用,就那么扣在河边。
二蛋儿来得比吉庆还早,见一个人影从雾焯焯中走过来,忙窜起来迎上去。
吉庆把网扔给他,让他背着,然后两个人走到船边,喊着号子把船掀过来,又一起鼓着劲儿推到河里。
他们的目的地是东边苇塘里的一个沟岔子,划船过去要半个小时。那个地方吉庆经常去摸鱼,一个猛子扎到对岸,再沿着泥泞的苇子地走上个把钟头就到了。今天有船,便用不着拐那个弯儿,直直地斜插过去要省事儿得多。
这个沟岔子是吉庆无意中发现的,连着下运河,入河口往里一点儿便越来越窄,慢慢地变成了个小河沟。水也不深,浅的地方才到大腿根儿,深的地方将将够着吉庆的腰。那一回,吉庆本来是在那一片踅摸野鸭的,野鸭没撵着,倒发现了这个好所在,把个吉庆乐得够呛。
好多的鲫鱼,还有大个的胖头。吉庆后来寻思,估计是因为这里密布苇丛,人来的少,鱼的吃食也多,这才把鱼从大河里引了过来。那一次吉庆可过了瘾,扑腾了一会儿就抓到了十几条。
可惜就是太不好走了,还要游回对岸,摸得再多也带不回去。为此,吉庆着实地痛惜了好几天。后来逢年过节或者家里嘴馋了,吉庆都要来这里一次,弄上几条大的,够吃上一两天的。为了这,可把平日里围着吉庆转得那些小子们眼馋坏了,天天央告着吉庆。吉庆却牙关紧闭,绝不吐露一个字,一口咬定是扎猛子摸的。一来二去,大家也就气馁了,只是怪了自己没有吉庆那浪里白条的本事。
本来是不想带着二蛋儿,但思来想去,吉庆觉得还是带个帮手好。再说,船是人家的,往后还要用,给点甜头也说得过去。
“咱这是去哪?”
二蛋儿卖力气地摇着撸,已经有些气喘,却因为兴奋,小脸蛋儿涨得通红。
吉庆指给他看。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像是镶嵌在下运河两岸的一条绿色的花边儿,把个汹涌的大河便衬托出一种柔美和勃勃的生机。二蛋儿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儿,又拼命地摇起来。小船箭一样无声地射过去,雾蒙蒙之间,掩映在苇丛中的一条河汊便豁然可见。
船顺着划进去,吉庆站在船头不时地估摸着水位,觉着差不多了,三下两下脱得就剩了裤头儿,扑通一下跳下了船。
“行了,就这吧。”
吉庆回身招呼着二蛋儿。二蛋儿把船往岸边划了划,扒光了衣裳,跳下河拽着缆绳勾着一把芦苇拴在上面。
两个人分头把船上的家伙什背在身上,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往里淌,越往里水位越浅,慢慢地露出了屁股蛋儿。
二蛋儿等前面的吉庆停住,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看着四周茂密的芦苇,咂着嘴皱着眉说:“庆儿,咋,要在这两头儿堆坝?”
“屁,这么宽这么深,堆两头儿还不得把我俩累死啊。”
吉庆不屑地撇着嘴。
“那咋整?直接下网?”
“听我的,看出水流往哪走了不?”
吉庆指着水面让二蛋儿看。
二蛋儿左看右看了半天,伸了手在水里估摸着,最后肯定了水流的方向。吉庆指挥着二蛋儿在上水的地方筑坝,自己淌到岸上折了些树枝苇杆,然后回来和二蛋儿一起肩挑手抗地干了起来。两个人一起筑得飞快,一会儿功夫一道泥巴堆成的大坝便慢慢地近了水面。吉庆又猫下身,闭着气在水底下扣着扒着,把那些树枝苇杆像喜鹊盖窝一样枝枝杈杈地支撑好,在泥坝的底下掏了个洞,这才招呼着二蛋儿把网拿来。俩人小心翼翼地将网在拢在泥坝靠近下水的一方,两边用绳子在河沟岸边找了小树捆好,这才满意地直起身子。
“这就行了?”
二蛋儿擦着满脸的汗问吉庆。
“行了,去船上把鱼食拿来。”
吉庆说。二蛋儿答应一声,扭头摇晃着身子奔了小船,很快又回来,手里拎了个袋子。袋子里是昨日吉庆拌好的鱼食,棒子面又掺了蚌肉,末了还滴了几滴香油,闻起来喷喷香。
吉庆掏了一把,匀匀地在附近水面上撒了,金黄色的食粒密密麻麻地铺满了碧绿荡漾的河面,稍一停顿,便浸满了水慢慢地沉了下去。觉着差不多了,吉庆背着剩下的鱼食招呼着二蛋儿上了岸,顺着已经变成小溪的沟岔往下游走去。这里的网已经放好,却还要等上一会儿才能收,眼瞅着太阳已经升起,可不能闲着干等。下游是一望无际的湿地,那些成群结队的野鸭最爱纠结在这里的苇子地里,乘着闲工夫,或许能捡上几枚鸭蛋。
火辣辣的太阳眼瞅着就要挂到了头顶,密密的苇丛中越发的闷热,成群的蚊虫聚在一起上上下下地飞舞着。吉庆和二蛋儿一边驱赶着不断撞上来的蚊子,一边兴高采烈地回来,手里面拎着一篓鸭蛋。今天命好,似乎没费什么功夫,竟然看见了成片的鸭群。被他们两个轰着赶着,呼啦啦竞相飞起逃离,空留下四散的鸭蛋,倒好象是故意为他们留得,把个吉庆和二蛋儿乐得几乎雀跃欢呼。
吉庆走到早上下了网的地方,扑通一下跳了下去,手拎着挂在岸边枝杈上的绳子一拽,死沉死沉的,吉庆的笑意更浓,忙招呼二蛋儿下来。二蛋儿也跳了下去,一边往吉庆身边淌,一边兴奋地问:“有么?有么?”
“有嘛?你得把‘嘛’字儿去喽!”
吉庆眉飞色舞地说。
“真得?哈哈!”
二蛋儿兴高采烈地抓住另一头绳子,拎了拎:“我的天爷啊,还真沉!”
“紧着,收网!”
“好嘞!”
二蛋儿答应一声,和吉庆两个人喊着号子把网拽上来。那网越往上收便越发的沉重,里面的鱼还在活蹦乱跳,死命地挣扎,把网拽得颤颤悠悠,好几次几乎要扽脱了手。
吉庆和二蛋儿几乎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终于把满满地一网鱼生拉硬拽地扯上了岸。那些鱼有大有小,却个个壮实肥硕,不时地蹦起来又落下去,此起彼伏,现出一派勃勃的生机。在明媚的阳光映照下,波光鳞鳞的份外耀眼。
吉庆招呼二蛋儿把船上的鱼筐拿过来,两个人一个捡大一个捡小地分别装了,细密的汗珠从两人红润的脸颊上淌下来,却因为收获的喜悦而兴奋地忘了擦拭。
“庆儿,你说,这两筐鱼我们得卖多少钱?”
再回去的路上,二蛋儿摇着撸眼睛还不错神儿地盯着舱里那满满当当地鱼。
吉庆也看了看筐里,舒心地呼出一口长气,躺在甲板上美滋滋地说:“咋也得卖个十几块吧!”
“嗯,我看差不多。”
二蛋儿咧着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顺着下运河往上游二十里,就是俵口镇,因县政府也设在这里,外面的人也把它叫做俵口县。吉庆随着长贵,每个月都来上几次,有时候是上来赶集,有时候买一些农具。平常的日子一般上来都是走旱路,水路这倒是头一次。
小哥俩互相轮换着摇橹,逆水行舟竟也飞快,个把钟头就已经看见了俵口码头熙熙攘攘的人流。马上就要到了,吉庆和二蛋儿却突然忐忑了起来。
“庆儿,你说,咱这鱼有人买么?”
二蛋儿犹犹豫豫地问。
吉庆挠挠头:“有!这么好的鲜货,咋能没人买!”
话虽这么说,其实心里也是没底。
和那次大长脸的交易不算,吉庆和二蛋儿都是头一遭经历这样的过程。当初被宝来的媳妇一说,吉庆立马被勾得蠢蠢欲动,但眼看真得要把抓到的鱼卖了,却咋也不知道怎么个开始怎么个结束。
做生意,那得是多大的事儿哩!就我们两个?别到时候鱼卖不了,还惹上一身腥臊。想到这里,吉庆心里更是像打了鼓一样,把个心敲得七上八下乱七八糟的。
俵口的码头和往日里一样喧闹嘈杂,四里八乡的船只停靠在这里,有装有卸来来往往。码头往上,有一大片空场,有人从水路上过来,就近卸了船也就近卖了。再后来,也就买卖得出了名声,只要有什么可以换成钱的物件,就全都聚拢在了这里,一来二去,就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农贸市场。每日里人声鼎沸,来来往往的人们摩肩接踵,分外热闹。
吉庆和二蛋儿把船小心奕奕地寻了个缝隙靠了码头,找个地界儿拴好,抬着两筐鲜鱼上了岸。让吉庆和二蛋儿想不到的是,还没等小哥俩抬起头,竟开始有三三两两的人聚过来问了:“这鱼卖么?”
“卖啊卖啊。”
吉庆忙迭迭地点头。
“咋卖啊?”
又有人问。
吉庆和二蛋儿互相对视着,心里都没个准谱,一旁的人又开始催了:“紧着紧着,咋卖啊,说个价。”
还是吉庆,想起了宝婶儿说过的话,咬咬牙却还是有些心虚地应了一嘴:“一块钱一斤!”
“一块钱?都这个价?”
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问。
吉庆忙说:“不是,胖头鱼一块,小鲫瓜子便宜,看着给点儿就行!”
胖男人哦了一声儿,猫腰在筐里面翻着,吉庆忙凑过去:“叔,不用看,都是活的,早末晌刚打下来的,没歇着就送来了。”
胖男人点点头,支起身子,随口问了一句:“你们是哪个庄儿的?”
“杨家洼的。”
“杨家洼的?”
胖男人凝神看了看吉庆,扑哧一下乐了:“这孩子,张嘴就来。这里卖鱼的,十个有八个都说是杨家洼的,有几个是真的?”
吉庆倒有些懵了,杨家洼就是杨家洼,咋还蒙你不成?这杨家洼又不是啥大地方,咋还有真的假的?吉庆一时间竟不知怎样说了,张个嘴嗫嚅了半天。
“你看看,撒谎了不是!这孩子,咋也会这个?”
胖男人看着吉庆六神无主的模样,瘪了瘪嘴,摇着头就要走。
“谁撒谎啦,杨家洼就是杨家洼的,儿唬你!”
吉庆见胖男人一副不屑的模样,立时有些急了,脸红脖子粗的大声喊了出来。
胖男人被吉庆的声音吓了一跳,回过身,瞅着吉庆红头涨脸的模样,还是有些不信:“真得?”
“真得!儿唬你!”
吉庆拍着胸脯子信誓旦旦。
胖男人扑哧一下又乐了,一边扒拉着围在鱼筐边的人,一边对吉庆说:“中中,我信,我信。”
一边对聚在身边的人们吆喝着:“别瞅了别瞅了,我要了,包圆儿!”
“包圆儿?”
吉庆的心要跳出了腔子,兴奋地瞅了瞅在一边的二蛋儿一眼。二蛋儿抹着汗,也是一脸的惊喜。
“真得?叔,你都要了?”
“都要了!”
胖男人豪爽地说:“就你说的价儿,大得一块钱一斤,小的给你七毛,咋样,不亏吧?”
“中中!就按叔说得算!”
吉庆和二蛋儿忙不迭地点头应着。
胖男人嘿嘿笑着,走到一旁,变戏法似地抄出一杆秤来。秤杆很长,一头是沉甸甸的秤砣,另一头当啷着绳子,绳子尽头没有秤盘却是个大钩子。胖男人回身又拿出了小盆,盆子上用铁丝吊了个把手,秤钩便钩住了,然后一条条的从筐里把鱼拿出来放上去去,抬头催着吉庆:“来来,帮忙过秤。”
吉庆答应一声儿,蹲下身子帮着,一起把鱼一盆一盆的过了秤,又一盆一盆地转进胖男人自己带来的筐里。
“看好喽啊,大得这筐一共是二十四斤,小的这筐十二斤,记住喽!”
“听叔的,说啥是啥!”
吉庆也认不得那秤,只会点头儿应了。
眼看着所有的鱼都过了秤,胖男人这才松心地直起身子,掏出根儿烟叼嘴里,划火柴点着了,深深地吸了一口:“你们哥俩放心吧,你们可着俵口县打听打听去,我胡胖子从不干缺德的事,不亏你们。”
“信信,哪能不信呢,叔说啥是啥。”
吉庆咧嘴笑着,颤颤巍巍地伸了手,心里通通地跳着,嘴巴张了张。
胖男人看吉庆那一脸为难的样子,突然醒过闷来,呵呵笑了:“忘了忘了,还没给钱呢。”
说完,忙在兜里掏出了一叠皱皱巴巴的票子,一五一十地点给吉庆:“数数,没错吧?一共是三十二块四,给你三十三!”
“没错没错,谢谢叔了。”
吉庆忙接过来,看也不看就塞到兜里,用一只手死命的按着,似乎怕进了裤兜的钱又会从里面飞出来。
“那成,就这样了。记住喽,下回有,还给我留着,甭给别人!只要到这来,随便找个人问,就说是公安局食堂的胡胖子,谁都认识,听着了么?”
“中中,给叔留着!”
吉庆爽快地答应着,抹头拉着二蛋儿就往回跑,跑了几步,突然想起来,船舱里还有一篓子鸭蛋,忙又停住步子。回身见胡胖子正把鱼筐往自己的三轮车上搬,急忙回来帮着一起放好。
“咋又回来了?还不放心?”
胡胖子问。
“不是,叔,我船上还有鸭蛋呢,叔要么?”
胡胖子问:“鸭蛋?啥鸭蛋?”
“野鸭蛋啊,那可是好东西呢!”
“野鸭蛋?真得?”
胡胖子瞪大了眼。
“可不是真的么!一早拾来的,二十多个呢。”
“那赶紧着啊,给我拿过来!”
胡胖子一听是野鸭蛋,立码兴奋了,这玩意当真是好东西,拿钱都买不来。
吉庆忙捅了二蛋儿一下,二蛋儿飞一般的跑回到船上,一会功夫就拎着装满鸭蛋的篓子尥了回来,喘着粗气递给胡胖子。胡胖子高兴地拿出一枚,对着阳光看,看完了又拿出一枚。
“不蒙叔,真是野鸭蛋呢。”
吉庆怕胡胖子不信,忙紧着解释。
胡胖子嘿嘿笑着:“信!哪能不信呢,看你们都是老实孩子,干不了那蒙人的事儿。”
“叔说得对呢,我们都是头一回卖这些,啥都不懂,往后还要求叔多照应着呢。”
吉庆眼巴巴地望着胡胖子,胡胖子瞥了一眼吉庆,却越发觉得吉庆眼神中的那种质朴和真诚竟是那么熟悉。
胡胖子也是从乡下上来的,在市面上混了那么久,这样的质朴却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胡胖子突然地想起了自己在乡下的家,突然地想起了乡下那些儿时的玩伴,也突然地对吉庆有了一种没来由的喜欢。有时候人跟人就是这样,也说不出个啥缘由,很多时候也就是一照面的功夫,就会莫名其妙的有了好感。
胡胖子笑着点头,把鸭蛋放回了篓子里:“照应谈不上,往后来,有啥事儿找你叔就没错了。我这也是看你们对上眼了,啥也不说了,说个价吧。”
“叔说,听叔的!”
“那中,三毛吧。”
“中!”
吉庆爽快地应着,顺手拿起了胡胖子车上的秤。
胡胖子看吉庆拿起秤杆子,扑哧一下又笑了:“你们也就是碰见我了,要是别人,把你们卖了你们还得乐呢。”
吉庆不明白胡胖子的意思,拿着秤愣在了那里。
“这个傻小子哦,我说的三毛,是一个三毛,你拿个秤干啥?按斤要(yāo)啊。再说了,三毛一斤你就卖?鸡蛋还一块五一斤呢。”
“一个三毛啊!”
吉庆这才恍然大悟,不好意思地挠着头。可不么,一个三毛和一斤三毛那得差多少钱呢,幸亏遇到了好人,不然可亏大了。
“紧着数一下,看看多少。”
胡胖子大大方方地掏出钱来,爽快地吆喝着。
吉庆和二蛋儿屁颠屁颠地两个两个的过了数,心里的小算盘扒拉得稀里哗啦,几乎要美出鼻涕泡。
回去的路上,顺风顺水。
初战告捷,小哥俩被满心的欢喜鼓舞得像吞了热豆腐,一刻也不得消停。二蛋儿的撸摇得轻快,吉庆站在船头一脸的昂扬。
卖鱼所得是三十三块,再加上鸭蛋的七块钱,整整四十。
吉庆手心里捧着,一张一张沾了唾沫数了又数,却还是舍不得揣进兜里。长这么大,吉庆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这一摞有零有整脏呼呼的票子,在吉庆眼里,却不亚于一座金山。
吉庆重新又数了一遍,数过了又仔细地平均分成了两份,把自己的那份掖回了兜里,回身把二蛋儿那份递了过去。
“这是给我的?”
二蛋儿停下了摇橹的胳膊,双手在自己的衣服上使劲的蹭了蹭,用了小心地接过来,一张圆呼呼的脸因为兴奋显得红润而又激动,本来不大的小眼儿,看到了钱却陡然瞪成了个铃铛。
“你点点,一共是四十块钱,咋俩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
吉庆洋洋自得地坐在船头,赤裸的脚丫子探进水面,啪嗒啪嗒地踢弄着。
二蛋儿喜悦地“哎”了一声儿,却也没数,直接就揣进了兜,想了想,却又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重新又把钱掏了出来,嘟囔着嘴说:“庆儿,不好吧,咋给我这么多呢?是你带着我弄得,咋说,也得拿大头儿啊。”
“啥大头儿小头儿的,是我俩一起弄的,当然得对半分。”
吉庆说。
“不行不行,”
二蛋儿数了几张捏在手里,凑过来,死活地往吉庆手里边塞:“我就是搭把手儿,谁都能干的活儿!”
吉庆忙往外推:“话咋能这么说呢,再说了,船还是你的呢。”
二蛋儿还是有些不依不饶的,两个人就在这狭小的船上你推我搡地挣扒了起来,把个小船弄得晃晃悠悠左颠右闪。吉庆有些恼了,一把将二蛋儿推了回去:“你咋那么多事儿呢,本来就是两个人搭伙,分个钱还磨磨唧唧的!”
二蛋儿看吉庆真得有些上脸,手里面攥着钱竟有些手足无措,嘴里还嘟嘟囔囔地嘀咕:“不合适,真不合适。”
“行了!就这么的了!”
吉庆大手一挥,扭过脸去继续坐在船头,再也不理会二蛋儿。二蛋儿看吉庆一副坚决的样子,也只好回到船艄,把撸拎起来怏怏地摇着,心里却还是惴惴地。
吉庆表面上生气,其实心里还是有些美滋滋的。人们常说,看一个人得从钱上来看,关键时候这个人不贪,那人品基本上就没跑了。吉庆长这么大没见过也听过,农村人家家都穷,把个钱财看得更重。多少家为了一点财产打个头破血流的,有的亲哥们都反目成了仇。杨家洼里和吉庆好的伙伴们成群结队,但都是一帮孩子,还没在钱财上有过啥牵扯。这是头一回在手里面过了钱财,也就是这头一回,吉庆基本上肯定了二蛋儿是个可以交心的朋友。
经过这一次顺风顺水的经历,吉庆陡然之间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再加上有了二蛋儿做帮手,吉庆一时间更是志得意满。就好像金山银山就摆在眼前,伸伸手就能搂进怀里一样。
想到这些,吉庆心里面被一种燥动鼓弄得有些手舞足蹈,看着波光鳞鳞的河水,恨不得跳进去扎上几个猛子,忍不住张嘴唱了起来。二蛋儿听见吉庆声嘶力竭的嚎叫声儿,嘿嘿地乐了,扯着个破锣嗓子也跟着唱起来。
两个人的歌声在寂静的河面上回荡着,那声调倒像是被风扯着的风筝,忽高忽低此起彼伏直冲云霄。两岸浩浩荡荡连绵不绝的苇丛中,成群结队的水鸟被惊醒,呼啦啦地飞起来,鸣叫着四散盘旋。
小哥俩就这么唱着闹着欢笑着,远远地河道拐弯儿处,杨家洼高高低低的房脊很快便隐隐显现出来。
大脚打早上一起来就没见到吉庆的人影,晌午饭都没回来吃,心里头来气,这时候正摔摔打打地嘀咕着。长贵和往日里一样,眼瞅着大脚的心气不顺,吃过饭便不声不响地溜了出去。
大脚一个人屋里屋外地踅摸,竟是看什么都有气,嗓子眼就好像吃了棒子面的窝头,上不来下不去地堵得难受。好几天了,大脚就像在地里面轰麻雀的那根栓了红绳的麻杆儿,吉庆却似那些猴精猴精的鸟,饶是任大脚围追堵截的,竟愣是没个办法。不是推就是躲,把个大脚闪得七上八下的,气馁之余就觉得自己个真是犯贱。有时候也咬着牙在心里面骂,连带着那院儿的娘俩儿。骂过了就恨恨地和长贵折腾,心里面恍恍惚惚地把长贵当了吉庆,可着劲儿地拽在自己身上再不下来,把个心气十足的长贵也累了个够呛。可那股劲儿松了,气喘吁吁地躺在炕上,那吉庆的影子却又倔强地从心里头冒出来。大脚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的想,想和吉庆在炕上痴痴缠缠地情景,想吉庆伏在自己两腿间汗流浃背的模样儿,越想却越是百爪挠心。
抬头看看早就偏了头顶的日头,大脚嘴里面骂着,把个鸡食盆子“咣当”一下,扔在了当院,弄了个鸡飞狗跳。本以为吉庆又跑到隔壁了,可上午巧姨颠颠地过来串门,竟说也没看见。
屋里头的座钟“铛铛铛”地响了一串,大脚终于再也待不下去,扭身出了院子。
巧姨正出来泼水,扭头正看见大脚怏怏地掩门,站住身问:“庆儿还没回来?”
“鬼知道死哪去了!”
大脚没好气的回了一句。
“那你这是要去哪?”
还真是的,自己这是要去哪呢?大脚被巧姨这么一问,却愣住了,想了想,说:“去找找,没准又下河洗澡呢。”
“洗澡还能洗上一天啊,没准去找同学玩了呢,”
巧姨说,又招呼大脚:“别去瞎找了,一会儿庆儿回来再撞了锁,来,上我这儿待会儿。”
“你那儿有啥好待的。”
大脚嘴里面小声嘀咕着,却还是走了过来。
大巧儿和二巧儿正在院子里的菜园子摘菜,见娘和大叫一起进来,齐齐地叫了一声儿“大脚婶”大脚僵硬的脸这才松弛了下来,硬挤着堆出来一丝笑容。巧姨抄了个马扎递给大脚,大脚坐了,却还是扭头冲着外面张望。
“诶呀行了,咋就那么惦记,一会儿看不着就想了?”
巧姨也坐在大脚身边,笑着调侃她。
大脚心里面有鬼,巧姨无意的一句话,但在大脚耳朵里却格外刺耳。心里面激灵一下,回头看了看巧姨,见巧姨一张笑脸并无异状,这才放心,却还是忍不住回了一嘴:“我的儿当然我惦记,有人却不知道惦记个啥呢。”
巧姨本就是个玲珑剔透的女人,感觉着大脚话锋不对,问:“我咋听你话里有话呢,哦,我不该惦记?咋说也是我未来的姑爷呢。”
“该该,谁敢说你不该呢!”
大脚哼了一下,给了巧姨一个白眼:“就怕不该惦记的地界儿也瞎惦记!”
巧姨心里也是一紧:这大脚的话越发让人难懂了,莫非和吉庆的事情被她知道了?巧姨脑子转得飞快,表面上却仍是波澜不惊的模样,满脸堆着媚笑,竟还往大脚跟前儿凑了凑:“你倒是说说,那啥地界儿该惦记,啥地界儿又不该惦记呢?”
大脚倒一时哑口无言了,暗暗懊恼自己这压不住的性子。难不成把这个脏事儿就此撕破了?别到时候扯出肠子带出了筋!想到这里,竟也无可奈何,只好胡乱地支吾着:“中中,你都该惦记!明个把那兔崽子绑你裤腰上,行了吧?”
巧姨“格格”的倒乐成了一团:“那敢情好,我还白赚了呢,省得到时候疼姑爷还得去你那边现喊。”
大脚更是气恼,也不知道这巧姨是不是在装傻充愣,恨不得上去拧她那咧到后脑勺的嘴。好在老姐俩从小到大也是闹惯了,你来我往的却也没真的上脸,依旧稳稳地坐了,远远看去倒和往日里两人插荤打磕没啥两样儿。
大脚瞥了一眼在那边干活的小姐俩,压低了声音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你个骚货,你就成天的浪笑吧,等哪天把你那窟窿堵上,让你还笑得出来!”
巧姨笑得更是欢畅,一连串银铃似的笑声悠扬顿挫,惹得大巧儿二巧儿止不住地看过来。
“越说你还越来劲了,懒得理你,走了!”
大脚站起身来,甩搭甩搭地就要走,却被巧姨一把拽住:“等会儿等会儿,还没说完呢。”
“有事儿?”
大脚停住,扭头看了一眼巧姨。
“你坐下,坐好喽,”
巧姨一把将大脚扥下,按在马扎上坐好,诡异的一笑,小声问:“我觉着你这些日子不对劲呢?是不是有啥好事儿?”
大脚诧异地低头看自己,疑惑地问:“啥不对劲?你看我哪像是有好事儿?”
“天天耷拉着一张脸,倒是看不出有啥好事儿。”
巧姨抿嘴笑着,脸上越发的神秘兮兮:“不过,看你这神态,咋瞅咋像是犯了桃花呢。”
大脚“呸”地一声儿,啐了口吐沫:“你个骚嘴,天天的就是这个!桃花咋长也长不到我这来,倒是你吧,赶紧摘摘自个,快被桃花埋起来了!”
巧姨格格一笑,凑近了大脚:“真得真得,说真格的呢,你自己不知道,旁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看看你,这屁股也圆了,奶子也鼓了,这老脸都跟抹了蜜似地,天天带着红润呢!”
说完,闪了身子上下打量着大脚,越瞅脸上的戏谑嬉笑却是越浓。
大脚被她看得糊涂,也自己扭着身子上下地看,终于惴惴不安地问:“这真能看出来?”
巧姨“嘎嘎”地笑弯了腰,指着大脚:“你看你看,不打自招了吧……”
大脚立时醒过闷来,这是被巧姨调理了,一脸的羞臊,“诶呀”一声儿,站起身来就要撕扯巧姨。巧姨笑着去躲,姐俩个倒像是一对没出门的闺女,嘻嘻笑着扯成了一团。一边的大巧儿二巧儿不知道这边是为了啥,却也被两人的无忌感染了,呵呵地跟着笑。
两个人闹了一会儿,总算消停了下来,巧姨搂着大脚,凑在她耳边问:“说说,咋回事?”
“滚犊子,啥咋回事?”
大脚摩挲着胸脯,喘个不停。
“还装!跟我你还没个实话呢。”
大脚一时语噎,不知道跟她说是不说。想了想,却觉得这些日子吉庆被她独占了,无论如何地心有不甘,陡然而生一阵子嫉妒。索性说了,好歹也是个让她羡慕的缘由。眼睛悄悄地往菜园子方向抽了一眼,掩了口凑在巧姨耳边:“长贵好了!”
“真得?”
巧姨一脸的惊奇,装模作样的竟好像是头一回听到。
“可不真的,这事我蒙你干啥!”
大脚洋洋自得地坐下,下巴颏扬起老高,到好似对巧姨示威一样。
“说说,说说!”
巧姨拽着自己的马扎凑得更近:“说说他是咋好的!”
“谁知道咋好的,冷不丁就好了呗。”
大脚闪烁其词,却再不敢把长贵治病的偏方说了出来。
“蒙鬼去吧!说好就好了?”
巧姨撇着嘴,满脸的不信。大脚一副爱信不信的模样,却再不敢接茬,忙扭脸去瞅门口。门外的街道依旧是静悄悄的,远处高高低低地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尖利的声音此起彼伏。树叶好像是被毒辣辣的日头晒得焦了,有气无力地低垂着,风也没有一丝儿,越发显得燥热。
老姐俩依旧是默默地坐着,一个是打破沙锅要问到底的神态,另一个却倔强个脖子任你大刀片砍来,依旧是是岿然不动。一时间倒有些僵了。
吉庆就在这时,恰如其分地跑了进来,满脸的汗水,气喘吁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