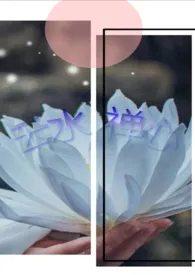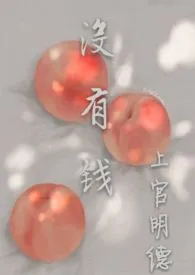哈哈。紧裹着的丝被缓缓打开,玉骨冰肌的我如同出水的芙蓉,亦真亦幻地出现在何安东面前。
“果然是你”
“这话该我说……”何安东毫无邪念地牵起我的手,眼神也变得迷离起来,“我少年时就做过这样的梦,梦到自已披着黎明把一个看不清面容的女子从黑暗中拉了出来,没想到,这个女人会是你。”
“这么说,我们做过同一个梦。”我不相信地看着何安东。要不就是,现在的我又在做梦。
“我做过四次这样的梦,少年时,我感觉梦里的女人很亲切,而后就有了第一次遗精。结婚前又做一次,因为这两个梦离奇的相同,所以,就算新婚妻子很漂亮,我也感觉很陌生,陌生到连正常的夫妻生活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我惶惶地抽回被何安东抓着的手,发烫的脸如同染上了桃花色。
“难怪啊!难怪第一眼看到你时我的心会骡然一跳。柳烟儿,为什么十年前遇到你的那个人不是我。”
何安东再次抓起我的手,如同沉浸在某个不愿意醒来的梦中。
“为了梦中的那个女人,我三十二岁那一年才在母亲的逼迫中结了婚。呵呵,你可知道我第三次做这个梦的时候是哪一天吗?”
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越来越感觉不可思议。
“你第一次自杀时,是我陪着你的公爹进到了你的家中,就是那个晚上,我第三次做了那个梦。到你第二次自杀时,总共做了四次。”
“第二次自杀。”我睡目结舌地盯着何安东。难不成,我们才是最有缘的一对。
“我就是第二次自杀时做的这个梦。那一次,医生都放弃了,如果不是你把我拉回来,怕是我不想信,又不得不信。”
“烟儿,你愿意为了我离开姓程的吗?”
我像被蝎子堑到似地抽回了手,如果没有程杰,我一定会为他放弃程弘博。就是因为不想放弃程杰,所以,我必需和他保持距离。
“柳烟儿,你还没回答我呢!”何安东固执地抓着我的手。
身体又开始发烫,脑海里反复交替的居然是那种让人耳热心跳的画面。
不好,被凉水勉强压下去的药性又开始发作了。
“饿不?”
想回答何安东,也不想在失态的情形中被他看扁了。
因而,我不顾一切地逃进了浴室,把被催情药撩出的臆想绕绕地挠杀在冰冷的凉水中。
浴室的?悄然开了,换上睡服的何安东健步走了进来。
“你……出去”
“那个汪八蛋告诉我,这种药必需夫妻相合才能解。烟儿,从你打电话叫我的那刻起,你就该想到这个结果。你已经成了我放不下的女人,我不希望你委屈了自已。”
是的,从打电话叫他来的那刻起,我的确想到了这个结果。
老天真会捉弄人,如果程弘博或程杰能痛痛快快地接听我的电话,或许,我与何安东的缘分就不会如此的顺理成章。
我把自已当成了何安东的女人。一个下午的缠锦后,我舒服了,何安东也痛快了。
我以为这一页又将在我立志与何安东划清关系的状态中结束。不曾想,未等我说出绝偷的话,程杰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又是他的电话。”何安东敏感地盯着我。
何安东是个自负而又自傲的男人,看到程杰的电话后,我灵机一动,按下了免提键。
“烟儿。”程杰的呼唤既温馨又亲切,一瞬间,我动容了。
“我以为你死了。”因为委屈,我喽喽地哭了。
电话那头一滞,何安东的目光俗然冷了。
“烟儿,今天在市里开会,刚看到你的电话,你是不是有事找我?”
“原来程区长是去开会了,呵呵,你的会比我的人重要,我已经没事了,再见吧!”
我故作轻松地挂了手机时,何安东一直在用幽冷的眼神打量着我。
“柳烟儿,你什么时候给程区长打的电话?”
“给你打电话之前!”
“呵呵,原来我是第二人选!”何安东自嘲地笑着。
“错!你是第三人选!”
“什么意思?”何安东有种被激怒了的感觉。
“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程弘博的,他是我丈夫,去吴德成那里解救我是他的责任与义务。可惜,他在陪教委来的领导,没时间听我说话。没办法,我只好打程区长的电话。呵呵,打给你是因为没招了。”
“柳烟儿,你把我当什么?”何安东腾地火了。
“你自已嫁磨吧,何主任,我想回家了,麻烦你送我下山。”
我从未想到何安东的眼神会如此的阴蛰,就在我以为他也会像程杰那样甩手而去时,何安东却大笑着走出了别墅的?
心里一阵失落,当何安东一口一个柳女士地把我诸到他的后车座上时,我感觉,我们已经成了两个完全陌生的人。
何安东痛痛快快地把我送到小区门口,我手脚发软地下了他的车,刚想说声谢谢,他却一踩油门,汽车就是离弦的箭,飞一样地驶离了我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