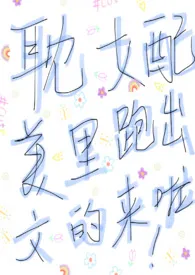洪武十一年,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十五子植为卫王,二十六年改封辽王。
起初辽王府在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
建文年间,辽王渡海南归,改封荆州,这是辽王府在荆州的由来。
张居正五岁入学读书,十岁通晓六经大义,时人称为神童,在荆州府很有一些声名。
十二岁去荆州府投考,被湖广学政田顼和荆州府知府李士翱看中,破例提为补府学生。
嘉靖十六年,年仅十三岁的居正去省城武昌参加乡试,在湖广学政、按察金事、监试御史和主考官中间引发了一场要不要让他中举的大讨论,最后在湖广巡抚顾璘的坚持下终于没有录取。
顾璘是当时有名的才子,和上元县的陈沂、王韦称为“金陵三俊”,其后又加宝应的朱应登,称为四大家(见《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传四》)。
他对当时监考的御史说道:“张居正是一个大才,早些发达,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等到才具老练了,将来的发展更加没有限量。”
他对张居正器重有加,曾将自己的犀牛皮腰带赠送给他,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
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昔张燕公识李邺侯于童稚,吾庶几云云。”顾璘的眼光还是有的。
嘉靖十九年,张居正中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入京会试,中二甲进士,选庶吉士。
三年期满,称为散馆,凡是二甲进士及第的,照例升为翰林院编修。
张居正的祖父张镇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见明王世贞《首辅传》)。
第六代辽王致格生来柔弱多病,王府的实际权力全由王妃毛氏管理。
毛妃有主张,有办法,把王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当地很有声望。
嘉靖十六年,致格病逝,第七代辽王宪X和张居正同年同月出生,要守孝三年才能袭封爵位,所以大权还在嫡母毛妃手里。
毛妃看到宪X资质平庸,只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少年,便不时招张居正入府赐食,让宪X坐在下首,教导道:“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要给居正牵着鼻子走呀!”
宪X满脸通红,心中充满了惭愤,但是没有当场发作。
他和居正从此相识,成为时常来往的朋友,但是在友谊的后面,埋藏着深深的嫉恨。
嘉靖十九年,十六岁的宪X三年丧服已满,照例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
张居正也于这一年考中举人。
辽王宪X就在居正中举的这一天,把护卫张镇召进辽王府,赐他喝酒,实在喝不下就叫家人强灌,最后将他活活醉死了。
张居正和辽王就这样结下了难解的大仇,虽然在表面上,他们还是朋友,还是非常的亲近。
嘉靖二十六年,一个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一个顺应时代崇奉起了道教,被嘉靖皇帝封为清微忠教真人。
明代的宗藩在政治上是被剥夺所有权力的,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宗禄。
朱姓繁衍,王室和外戚男子世袭各类郡王、各类将军、各类中尉,女子世袭的公主、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公主的丈夫是驸马,郡主以至乡君的丈夫是仪宾。
明朝发展到嘉靖这一朝,这些皇室的直系、旁系亲戚已发展到数以万计,每人都有岁禄,从郡王的一万石到乡君及仪宾的二百石,中央财政有一半消耗在这上面。
宗藩在政治上没有进取之心,便在地方上大量兼并土地,积聚个人财富,辽王府便是这样。
毛妃一死,辽王大权到手,立时抖擞起来,豢养一帮如狼似虎的手下,打砸抢骗,强买强卖,无所不用其极,美女、土地和房屋滚滚卷入他的囊中,成为彻头彻尾的荆州一霸。
地方官员看见当今圣上御赐他的“清微忠教真人”牌匾,如何敢来哼上一句?
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的元配顾氏病逝,他心伤爱妻之死,告假回到江陵,过起了长达六年的半隐居生活(见《文忠公行实》)。
在休假期间,两个从小的好友重新走动起来,好像有一条无形的绳子,他们的命运仿佛总能纠结在一处。
《大明律》规定:宗室藩王没有皇帝的恩准,是不得离开封地半步的,违者削为庶民。
辽王有“清微忠教真人”这块护身符,经常打着求仙访道的旗帜,到数百里外的地方去游山玩水、寻花问柳。
这次他拉着张居正出来游玩,便是借口去道教圣地龙虎山拜访张天师,却不料在南昌城撞到了方学渐一行,被初荷清纯脱俗的美貌所吸引,一路跟了上来。
那道士转过头来,只见眼前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男子,身量中等,面目清秀,衣冠楚楚,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好奇地望向自己,瞧不出什么来历,问道:“你是谁?问这个干嘛?”
方学渐见他四十上下年纪,道袍破旧,模样有几分滑稽,一双深褐色的眸子里却隐隐发出金子一般的黄光,仿佛能洞穿世间所有的人心一般,心中凛然,恭敬地道:“在下方学渐,末学后进,微不足道,不敢请教道长的法号?”
道士“噢”了一声,用衣袖抹去桌上的八个大字,淡淡地道:“贫道姓蓝,别人都叫我道行,其实我的道行是很低的,这几个字是我心血来潮,随意涂抹上去玩的。”
方学渐知他故意推脱,笑了笑道:“道长的午饭不小心撒了,不如由在下做东,弄两壶老酒、几样小菜,小酌一番?”回头吩咐伙计收拾桌子,整上酒菜。
蓝道行天生异秉,少年时出家学道,艺成之后周游四方,靠给人看风水选墓穴赚钱过日。
他给人请吃请喝惯了,这次也不怎么在意,拉开凳子,毫不客气地坐了,仔细端详他的面容,点头道:“好好,小伙子有点善心,看你的面相,也算少有的福泽深厚之人,难得,难得。”
一个小女孩突然跑过来,双手一伸,把一块杏黄色的干净手绢递给他,道:“这位大叔,你的脸好脏,别人都在偷偷笑你,快用它擦擦吧。”正是和山庄众人一起吃饭的小素。
蓝道行呵呵一笑,接过手绢,和气地望了她一眼,笑道:“小姑娘的良心倒好……”才说到一半,移动的手臂突然在空中顿住,道士脸上所有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僵硬,两只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手指微颤,薄薄的绸绢从他的掌上轻轻飘落,一大一小,四眼相对。
蓝道行突然大叫一声,见了鬼似的,从座位上直窜起来,口中哈哈大笑道:“不得了,了不得,今天全都碰到一起了……”几步抢到楼梯口,也不知在哪里绊了一下,身子打横,骨碌碌滚了下去。
他的笑声突兀之极,偏又良久不歇,笑声中夹着“哎哟、哎哟”的呻吟,酒店伙计的惊呼,和众人的哄堂大笑,声势颇为可观,撼得整个酒楼都似在轻轻摇晃。
方学渐望望一脸愕然的小素,又望望空荡荡的楼梯,摇了摇头,心想:世人都说修道之人都带有几分呆头和轻狂,现在看来果有一定道理。
拉了小素的手,回去原来的桌子。
方学渐装作没看见那只苍蝇,在席上劝酒劝菜,谈笑风生,心中却盘算着如何教训他一下。
菜好酒好,主人又十分客气,大家吃的都十分开心,这一顿饭吃了半个时辰才完。
酒楼的隔壁就是杏花客栈,闵总管过去订了客房,众人酒足饭饱,过去安置行李。
下午自由活动,四个马夫要了一辆马车,出去寻找乐子;闵总管带小素上街,买些衣物、玩具和零食;童管家留下来照看受伤的解明道;方学渐、初荷和小昭要去滕王阁玩,老麻熟门熟路,只得再当一回马夫。
方学渐靴子里藏一柄锋利匕首,衣带上挂一把七星宝剑,虎腰里缠一根盘龙长鞭,左臂挽着闭月羞花的初荷,右手拉着沉鱼落雁的小昭,雄赳赳、气昂昂地上了马车。
老麻喝叫一声,一抖缰绳,马车转出客栈,按照方学渐的吩咐,往城外一个荒僻的地方跑去。
出了东城门,马车沿着官道一路向东,拐过几个弯,道上行人便渐渐稀了,后面急促的马蹄声却越发地响亮。
方学渐从窗口探出半个脑袋,只见车子后面紧跟着五匹骏马,“乌蹄玉兔”当头,那只肥猪色胆包天,果然追了上来。
中年书生心情不好,在席上喝醉了酒,没有跟来。
嗖的一声,一道迅捷无匹的银光从他耳边一闪而过,方学渐脑袋一缩,心中暗叫一声“妈呀”,差点吓得魂都没了,对方居然还随身带着如此犀利的弓箭。
瞧不出来那四个傻子一样的王府护卫,看上去木头木脑,杀人的手段却一点都不含糊。
马车一口气跑出十余里地,官道突然一分为二,老麻缰绳一拉,车子转弯往南跑,又奔行数里,远远望见一个茂密的杂木丛林,路径荒僻,人迹罕至,正是杀人灭口的绝佳所在。
方学渐心中叫苦不迭,没有其他办法可想,只一个劲地催促老麻把车赶得快些,再快些。
到了人烟稠密的市镇,这些人的胆子再大,也不敢当街杀人。
辽王府的坐骑都是百里挑一的良驹,不紧不慢地跟着,马车一入林子,登时从后面包抄上来。
“嗖嗖”声中,拉车的骏马几乎同时中箭,四声凄厉的哀号连在一起,短促又漫长,听上去分外惊心动魄。
疾驰的骏马像被闪电击中一般,骤然间失去了控制,无意识地向前奔出二十余步,蓦地轰然倒下,庞大的尸身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差点把整辆马车掀翻过来。
四根银色的箭簇穿透马的脑颅,只露出短短的一截箭头,在温暖阳光下闪着夺目的寒光,犹如开着四朵妖艳的百合,殷红的鲜血沿着箭杆汩汩而出,顷刻流了一地。
蹄声“得得”,一匹快马自车后跑了上来,那胖子哈哈大笑,道:“车里的小子听了,乖乖把两个美人献上,本王爷就饶你一命,说不定还送你几两银子做安家费。”
车子颠簸得厉害,车厢里的三个人更是颠三倒四,惊叫着滚成一团,四处碰壁,鼻青脸肿。
方学渐尽量护着两个老婆,咬牙切齿,痛恨自己居然如此轻敌,不但教训不了这只猪头,还要丢掉自己的小命和两个如花似玉的老婆,真是“方郎妙计平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命”。
一想到初荷和小昭冰雪一样光洁白嫩的躯体,将被一头肥猪似的家伙压在身下,疲塌滚圆的肚皮,黑黢黢的丑陋棒子,两个老婆在床榻上辗转哀号,痛不欲生,惨不忍睹的情形,方学渐几乎气晕过去,眼睛充血,提起手掌啪啪打了自己两个耳光,从靴子里拔出那柄雪亮的匕首,沉声道:“荷儿、小昭,今天是相公害了你们,我现在出去和这几个跳梁小丑较量一番,你们有机会赶快逃走吧。”
不等两人回答,他伸手掀开帘子,正要钻出车去,咚的一声,脑袋上一阵剧痛,和进来的老麻撞了一个正着。
方学渐吃了一惊,手中的匕首来不及收回,“哧”地刺入老麻的大腿。
帘子一开即合,两人面面相觑,突然同时叫喊起来。
真是出师不利,不伤敌,先伤己。
幸好刺得不深,拔出匕首,敷上随身携带的金创药,小昭撕下一幅衣襟,替他包好伤口。
老麻眼睛半闭,靠在板壁上哼哼唧唧,也不知在念叨什么。
方学渐满脸尽是尴尬之色,握着那把匕首,不知道先跳出去砍人呢,还是留下来先道歉。
“嗤”的一声,一柄钢刀刺破车帘,刀锋转向往左,正要将帘子割成两半。
方学渐暗暗叫苦,没有这块棉布做掩护,自己这方赤裸裸地暴露在敌人的箭石之下,那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急忙去抽腰上的长鞭,仓促之间却又如何来得及?
“啪”的一声脆响,一条细长的黑影在眼前一闪而过,从那道被刀锋割开的缺口准确地飞出去,车外马上响起了一声惊呼,钢刀凌空坠落,在车子上一磕,翻滚出去,“呛啷”落地。
鞭子抖动,车外的一条汉子扑了过来,方学渐想也不想就挺出匕首,身子扑到,锋利的匕首轻轻刺入那人的心脏,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有粘稠的血液喷上淡青色的帘子,像开了一朵鲜艳的月季。
那人来不及哼出一声便一命呜呼,趴在车辕上,把一面帘子压在身下,绷得死紧。
从割开的缺口望出去,那胖子一脸的得意洋洋,骑着那匹“乌蹄玉兔”,在两丈外观看好戏。
方学渐回头一望,鞭子的主人居然是老麻。
头上“格”的一声轻响,有人已然跳上车顶,方学渐愣了一愣,猛地清醒过来,身子向前扑出,后脑上蓦地爬过一抹阴森森的寒意,“哧”的一声,冰一样的钢刀穿过薄薄的木板,贴着头颈割下他的一缕黑发。
他惊出一身冷汗,扑到地板上,又和先前的死人顶了一下脑袋,疼痛入骨,还没等他哼出一声,又是一柄钢刀刺破帘子,刀锋笔直向下,布帛碎裂的声音呼啸而来,只需眨动一下眼睛的工夫,他的脑袋就将被锋利的刀锋一分而二。
初荷和小昭齐声惊呼起来,方学渐心中一痛,知道自己再难活命,脑中电光火石般闪过一双幽怨的眼睛。
是龙红灵,还是小昭、初荷,他已经分不清了,右臂机械般地伸出,掌中的匕首割破帘子,准确地刺入那人的手腕。
长发飞舞,头顶上急遽的风声骤然停顿,雪白刺目的锋刃离他的后脑还有半寸的地方,被老麻用长鞭硬生生地拉住。
方学渐的魂魄在鬼门关前溜达了一圈,总算平安回来。
长鞭一甩,钢刀飞入老麻的手中,向上轻轻送出,车顶上立时响起了一声凄厉的惨叫,砰地一响,一个重物砸在车厢上,老麻手中的钢刀一收一送,大颗大颗的血泪从头顶割开的缝隙间“滴滴答答”落下来,惨叫声嘎然停止。
方学渐的手掌在地板上用力一拍,身子从帘子的破洞口扑了出去,匕首的寒光在那个护卫惊恐的眸子里绽开一抹动人的惊悸,嚓的一响,洞穿了他的咽喉。
他的左手在尸身的肩头上撑了一下,右手已拔出腰带上的七星宝剑,一个敏捷的凌空翻身,一招“横看秦岭”,青色的长剑平平掠过,火一般的鲜血顿时狂飙而出,一颗人头高高飞起,跌在马路正中,骨碌碌地滚出老远。
无头的尸身在马上前后摇晃,终于缓缓倒下。
胖子尽管作恶多端,平时欺负的全是武力弱小的良善,何时见过如此血腥惨烈的场面,一时张口结舌,看傻了眼,直到一条鞭子悄无声息地缠上他的脖颈,身子腾云驾雾般斜斜飞出,咚的一声,一个倒栽葱,头下脚上摔在地上,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已被赤裸裸地挂在树林子里,身上的一万二千多两银子,还有那些为博取佳人欢心而准备的珠宝玉石首饰,都和衣衫一起不翼而飞。
唯一贴身收藏的是那条特大号的丝绸内裤,不是穿在身上,而是塞在嘴里。
方学渐原本想给胖子来个“斩草除根”,割下他为害不浅的小弟弟,念在那一笔小财的份上,只剃光了他全身的毛发,暂时不下辣手。
回到原地,老麻已经用两匹马套好车子,初荷和小昭一同骑在马上,面孔有些发白。
方学渐向她们笑了笑,和老麻合力把人和马的尸身搬上车子,又在上面放了七、八块几十斤重的大石头。
一切收拾妥当,老麻上车赶路,方学渐、初荷和小昭骑马,继续向前行去。
树林的尽头是方圆数十里的平山湖。
老麻用长剑刺中了两匹马的眼睛,瞎眼的马匹疯狂地奔跑起来,拉着马车驰入平山湖,割开的水面像被一把巨大的犁耕过,渐渐行远,整辆马车很快消失在视野之中,沉入湖底的淤泥。
水波荡漾,金色的阳光撒在上面,像鱼鳞一样轻轻跳跃。
湖面上还不时吐出一串串血色的气泡,慢慢稀少、寥落,仿佛日出前的天幕,群星渐渐退隐,最后归于空白、平静。
没有风,没有波,除了来路上零星的红色血花,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初荷和小昭同骑在那匹“乌蹄玉兔”上,四人三马沿着岸边行了两里多路,才下马到湖边洗净身上的血迹。
经过这一场惊心动魄的遭遇,几人都没有了游览滕王阁的兴致,再加老麻的大腿受了伤,径直回去杏花客栈。
方学渐为感谢老麻的救命之恩,偷偷塞了两千两银子给他。
老麻银子入袋,只朝他笑了笑,不说一句话,闷声大发财。
跨进客栈门槛,时辰尚早,闵总管和小素还没有回来,四个马夫更是跑得不见踪影。
方学渐摸出五钱银子给店小二,吩咐他去请城里最好的医生,给老麻看病开方,价钱多贵在所不惜。
老麻说声感谢,一高一低地回房休息。
杏花客栈没有单门独户的小院,方学渐的住处是一间上房,内外两个房间,用薄薄的板壁隔着,价钱比普通的客房要贵上一倍。
窗前正对着一个精致写意的小院,一棵银杏古树参天而立,树高五丈余,干围二丈八尺,形如山丘,冠似华盖,叶色已经转黄,龙盘虎踞,气势磅礴。
房中陈设还算雅致,尤其是家具桌椅,居然全是用比较珍贵的花梨木做的,也算十分难得,更难得的是屏风后面的一只大木桶,规格几乎能与灵昭学苑里,方学渐花了一百五十两银子订做的楠木浴桶相媲美,只是材料上差了些。
两个客栈的伙计轮流提水进来,不多时便已积蓄起大半桶水,点燃下面的炭火,小昭自行囊里取出数种香草和晒干的花瓣,酌量放入少许,随水温的提高,房间里很快弥漫开湿润而暧昧的芳香。
方学渐怀抱温香软玉,侧着脑袋温柔地亲吻初荷冰玉一般的脖颈,灼热的舌尖灵巧地上面滑动,带起她一声声娇弱的呢喃,两只手掌在她高低起伏的山川丘壑之间来回游走,敏感的鼻端萦绕着一股熟悉又陌生的幽香,有少女的清雅,又带着些少妇的甜蜜,熏人欲醉。
初荷妩媚羞涩的眼睛上蒙了一层朦胧的水气,柔软的身子微微颤抖,两只无力的小手抓着他的手背,不知道是在引导还是在阻拦?
鲜润的嘴唇张开来,仿佛两片娇嫩的玫瑰花瓣,带着晨露在黎明的风中轻轻摇曳,芬芳的呼吸阵阵地喷在男子的脸上,是世上最厉害的一种催情春药。
方学渐右手抄到她的腿弯里,将她横着抱起,“啧”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笑道:“相公服侍亲亲荷儿洗澡。”几步走到屏风后面,脱去她身上的衣裙,把她白花花的身子抱进木桶,水波荡漾,更显得肌肤胜雪,美人如玉。
美色当前他如何忍受得住,探手下去握住一对雪白硕大的奶子,滑腻如酥,饱满欲裂,摸上去极其受用。
方学渐正要好好享受一番,只听正在关窗关门的小昭说道:“这位先生,你找谁?”
只听一个中年男子清朗的声音道:“我想找你家公子,不知道他在不在?”
方学渐探头出去,只见门口站着个三十上下年纪的书生,丝绸长袍,面容清俊,正是和胖子在一起的那个翰林院编修。
方学渐心中一惊,知道他久不见朋友回来,却看到那三匹同伴的好马被自己骑回来,生了疑心,前来询问原由。
他是当官的,自己可要小心应付,千万别露了马脚,当下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拱手道:“尊驾贵姓,可是找晚生么?”
张居正面色恒定如常,还施一礼,道:“鄙人姓张,刚才看到你和几个伴当骑了我同伴的马匹回来,不知是怎么回事,特意来问一问。”
方学渐夸张地“哦”了一声,扭头望了小昭一眼,眨眨眼睛,笑道:“张大人,这件事情说来话长,这里谈话不太方便,不如我们到隔壁的杏花酒楼,找个位子坐下来,好好地叙一叙?”
张居正沉吟片刻,听见屏风后面隐约有水声传出,知道有人在洗澡,脸上微微一红,点头道:“这样也好,只是麻烦公子移步。”
两人谦逊一番,张居正毕竟年长许多,走在前头带路。
方学渐离他大约两个身子的距离,凝视他消瘦挺拔的后背,心中盘算着如何把这件事情糊弄过去。
俗话说无官不贪,这位翰林大人多半也是贪的,只是编修是个没有权力的虚职,没有门路贪,结果两袖清风,穷得连老婆生病都买不起药。
两人下楼穿过下面的小院,沿着楼道拐了几个弯,从一座平台上的一个架空木梯过去,便是杏花酒楼。
此时是下午时分,客人稀少,两人要了几样精致细点和一壶西湖龙井,在二楼一个靠窗的桌子相对坐了。
方学渐以茶代酒,笑盈盈地与他互敬了一杯茶水,通过自己的姓名,从怀中摸出那枚汉白玉扳指,递给他,道:“张大人,你见多识广,不知道认不认识这枚白玉扳指?”
张居正皱了皱眉头,接过扳指,正反端详一遍,道:“这扳指有些眼熟,好像是辽王殿下……”
方学渐微笑着点了点头,揭开盖子喝口茶,道:“不瞒张大人,这位辽王殿下举止不够检点啊,我和贱内去鄱阳湖欣赏山水风光,青天白日的,他竟然带着几个手下追赶上来,要将我的两个老婆强抢过去,张大人是翰林院编修,不知道大明律法可允许皇亲国戚可以为所欲为么?”
张居正素来清楚辽王的为人,只不料他到了外乡也如此胡作非为,不知道收敛一点,不但丢了坐骑,连扳指也被别人收缴,这下吃的苦头肯定不小,心中快意,面上却不动声色,缓缓说道:“辽王殿下做事任性了些,公子和两个夫人都安然无事,没有酿成大错,也算幸事一件,却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形怎样,方公子可否相告么?”
方学渐眯起眼睛,盯着他的面孔,居然连一丝异样的颤动都看不出来,心中暗暗佩服他的修养功夫,精华内敛,让人猜不透他心中在想什么。
而喜怒不形于色,有体无质,忍他人所不能忍,正是一个人做大官、成大事的必备条件。
此人城府如此之深,生平仅见,连神龙山庄号称第一老狐狸的老麻看上去都似有些不及。
方学渐脑子飞转,突然想起那个道士在桌上写的八个大字来,“国家栋梁,中兴民臣”,难道就是指的这个人?
他打了个哈哈,道:“我只是一个手无搏鸡之力的普通人,如何斗得过辽王的那些如狼似虎的手下,我的一个下人被他们在腿上砍了一刀,差点小命不保。
我现在能在这里陪张大人喝茶聊天,那是全靠几个路过的大侠拔刀相助,才平安地全身而退。“
张居正淡然一笑,目光深处却有精光隐隐闪动,道:“那是辽王殿下不够走运,赔了夫人又折兵,却不知那几位大侠是什么来历?”
“关东五侠,不知张大人有没有听说过?这些可是好人啊,大大的好人。”
张居正“哦”了一声,脸上的笑意更浓,道:“这倒没听说过,既是侠客,有机会倒要好好结识一番。方公子,不管怎样,还请你指点一条明路,辽王殿下毕竟是我的同伴,半路走失,回去难以交代。”
方学渐转了转眼珠子,看着他的面孔,笑道:“不敢欺瞒张大人,辽王殿下至今平安无事,那关东五侠却是往西方去了。”心想:“关东五侠”确实是往西方极乐世界去的,这倒没有骗你。
张居正喝干杯中茶水,把那枚白玉扳指放回桌上,站起来拱手道:“多谢方公子见告,鄙人急着去寻辽王殿下的下落,这就告辞,后会有期。”转身下楼而去。
方学渐不料他如此干脆,说走就走,等他反应过来,张居正已走到楼梯口,还想出声招呼,把这枚白玉扳指送给他,手伸到一半,终于没有出口,脚步声“咚咚”响,渐渐变轻,很快听不见了。
他无心喝茶,付过钱钞,回转自己的客房,路过解明道的房间时,房门紧紧关着,里面水声“哗哗”,大概是在洗澡。
方学渐摇了摇头,心想这位解大哥满身泥垢,浸过的洗澡水营养丰富,大致可以拿去肥田了。
正想走开,突然听见一个女子的声音透过窗纸传出来:“你说你的老婆跟人跑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语速快捷却不乏女子的温婉,却是童管家。
解道明叹了口气道:“这事说来话长,还要从我小时候说起,我父亲是…”
方学渐暗暗称奇,听了好一会,却听不出半句风言风语,老老实实地,就像一对久违的老友在回忆以前的往事,兴趣缺乏,便急步跑回自己的房间,几下扒去身上的衣衫,在初荷和小昭的惊呼声中,“扑通”跳进大水桶,张开双臂,把两个美女左右抱住,嬉笑道:“相公做公证人,这一次来比比你们的屁股哪个更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