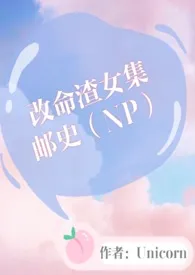忙活一下午,又累又脏,拉着刘海儿去澡堂子洗了洗。
别看我这脸饱经沧桑,晒得又黑,在煤窑干活又看不出来脏净,可是身上的皮肤不会骗人。
刘海儿给我搓澡直夸我这身上的皮肤像是十七八的大姑娘。
相比于这些打工仔,我是一路上学没干过粗活,身上细皮嫩肉是当然的。
这刘海儿越搓越上瘾,别他妈是犯了色心想女人了。
妈了个屄的,骂了这小子几句,洗完了匆匆离开。
这几天我都是在四队宿舍睡,因为四队没住满,床铺宽敞,但是今晚没暖气,我又洗的白白的,不想去三队跟那帮一身臭汗的挤。
妈的,还是去李婶儿床上吧。
趁着工人没还都没回,赶紧去厨房吃几口热乎的,又趁着打手们没回,早早躲到李婶儿床上。
李婶儿晚饭前后还要忙活一阵,入冬了,猪圈也挂了塑料布,猪食太凉了弄不碎,还得烧水沏豆饼,挺忙的。
李婶儿留我一个人在她床铺先睡一觉,准备晚上再大战。
把帘子放下来,打手们都是当兵的出身,比较守规矩,不乱翻。
这一觉就睡到晚上八点多了,这时候还是三队自由活动的时间,当然已经不允许出宿舍了,李婶儿还没忙完。
王哥这个时间不回来基本上晚上就不回来睡了。
这王哥其实晚上经常不回来睡,据说这小子在屯子里有个姘头,经常去鬼混。
但是如果他晚上不回来,第二天早上是一定要回来看看的,他自己有摩托车,一回来就能听到声音。
今天打手们回来的挺早的,我一个人躲在李婶儿床上,无聊又不敢出声,这个时间正是打手们来回巡视的时间,所以宿舍里比较热闹。
这帮打手,平时也不喜欢待在院里,谁他妈的愿意待在监狱里。
这个小院密不透风,白天除了我和老齐父子还有李婶儿,基本上没什么人,根本不用看着。
只有三队四队的休息日才会留下一半的打手看院。
平时,这帮打手分为两组,一组跟着工人到矿井,在井边守着(井边都有工棚),以防突发事件,其实也就是跟机械班的人打牌,然后帮助运煤车司机清点和上称。
另一组就轮休。
轮休的一组,都是下屯子里玩去,据说,据说啊,我是还没见识到,屯子里有女人玩,当然他们的主要休闲活动还是网吧、台球厅和老祖家的小吃铺。
咱们这个三道沟屯子,距离鸡西市里很近,不过20多公里,所以基本不受乡里管,现在交通发达,大客车小客车方便,屯子里的人赶集也是直接都去市里。
但是屯子就是屯子,没有正经的饭店,只有几个小吃铺,卖早餐为主,也能弄个溜炒小菜,七队的打手们基本上都是来这些地方打牙祭。
王哥比较抠,打手们的工资也不高,来老祖家的小吃铺的原因是因为他家有个大电视,兵哥哥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再要一两瓶啤酒,能过一天。
书归正传,今天这王哥不在,这帮打手们又放飞自我了,在宿舍里打牌,聊天,到十二点多还他妈的不睡。
李婶儿忙完了回来,也只能跟我躲在床上不说话,想像上次一样,借着打手们的呼噜声打炮是没机会。
妈的,挺到了一点多,我看李婶儿都他妈睡着了,我也放弃了,搂着李婶儿也睡了。
……
第二天一大早,迷迷糊糊中,听到外面的嘈杂,先后听到胡老大和王哥的摩托声。
这帮兵哥哥早就起来出去忙活去了。
一看表才7点多,工人们已经吃完饭,准备下井。
这天是一队休息的时间,但是看到二队三队四队也都还在院里没出去,有点奇怪,我赶紧从李婶儿身上爬起来,叫她掩护我出去。
此时宿舍里没有打手,李婶儿出去开门,见没人往这边看,才叫我出来。
院里并没有太多人,各队工人基本都在宿舍,小院的大铁门意外的开着,王哥带着大部分的打手在门外守着,似乎是在准备迎接什么重要人物。
平时大铁门上面的小门都是锁着的,上一次开大门,还是四队的人刚来的时候。
不过看今天这架势不像是迎接新人。
我赶快回到三队,问了一下刘海儿,也不知道,只是打手们通知晚一会儿再出工。
不多时,门外来了一辆吉普车,下车的人和胡老大亲切拥抱,热情叙旧,胡老大把这人引到办公室,坐了也就十几分钟,然后胡老大亲自带着人来各个宿舍瞅了瞅,最后一个到三队。
大伙议论纷纷,都猜疑这人是不是董老板。
等到我们三队这屋的时候,这人驻足多时,对每个人都仔细打量了一番。
当然也没对谁过多观察,只是我看到胡老大反复看了我好几眼。
还好我留了个心眼,我这洗的白白的,又几天没下井,穿的衣服都是干净的太惹眼,他们进屋前,我特意抹了两把煤灰在脸上,又穿了小驴子的脏衣服。
那人看了一圈,胡老大陪笑到:“咋样,有没有啊?”
“啊,呵呵,走吧。”那人同样笑脸回应。
两人互让走出宿舍。
来的这人似乎有点眼熟,感觉似乎是见过,刚才一说话,更让我觉得似曾相识,这人是谁呢?
出去后这人又跟胡老大寒暄了几句,就出门上车走了,接着,打手们进屋通知上工。
今天胡老大和王哥都在,我也不好明目张胆地偷懒,于是跟着三队下井去了。
“这人是谁呢?”在井下想了一天也没想起来。
中午吃着久违的工作午餐,着实玩不下去,不行上去后还得给小驴子提意见,想办法提升午餐的质量。
晚上王哥在,不方便再去钻李婶儿裤裆。
不过躺在床铺上,还是想不起来这人是谁。
要是平时,路上见到一个眼熟的人,想不起来也就想不起来了,可是在这里,如果是和自己有过交情或者认识的人可就不简单了。
他能救我出去?
还是我到这来跟他有关?
……
“六子,把衣服收了……”
晚上熄灯前听到姜波在管四队的人,这一声呼叫唤起了我的记忆。
六子,六子?陆子?!对,是陆子!!!
还记得第一次去见严六爷,他的那个马仔,六爷喊他陆子那个,对,就是他,因为只有那一面之缘,所以记得不深,不过越想越回忆越清晰,没错,就是他。
可是他他来这里做什么?
来找我?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夜。
没睡好,第二天还被冻醒了。
昨天被这个陆子“逼”得下了井,忘了给四队修水暖气管的事,结果冻了自己一夜。
今天两位老大又不在院里,上午老齐准备骑他那个破倒骑驴下屯子进菜,我顺道蹭他车。